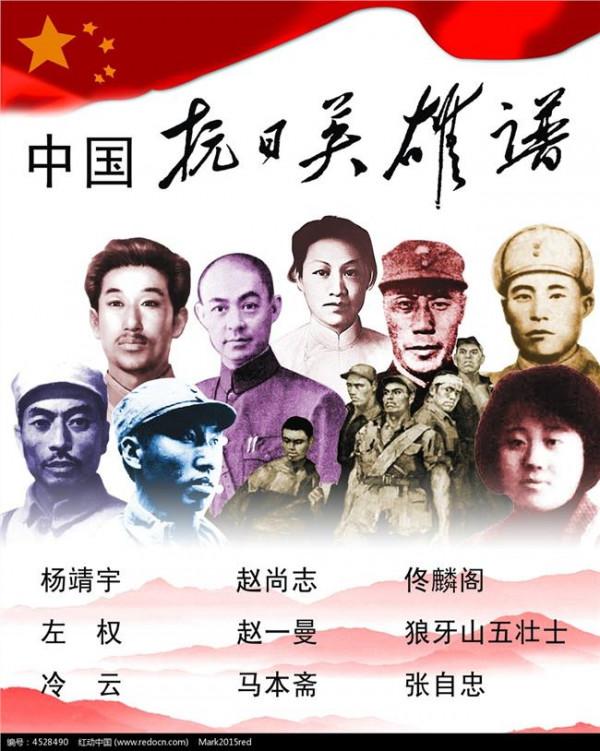王光美谈陈少敏后人 王光美谈文革期间的刘少奇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
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这一天是将少奇和我放在一个会场上批斗的,我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批斗会结束后,还和原来一样,将我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
我和少奇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我被勒令干这干那。有一段时间老叫我背砖头。要我把砖头装在筐里,从这院背到那院,从那院背到这院。有时我实在背不动,就站着将砖筐靠在墙上,托一托力。有一次一个看守的战士小张,见我背得吃力,冲我大声说:“你背不动不会少背一点吗!”其实他是同情我,要我少背一点。后来在往筐里装砖时,我就真的少放了一点。可没多久,就见不到这个战士了,听说因为这件事被调走了。
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居的前后院之间搭起了一堵高墙,把我和少奇完全隔开。
9月13日凌晨大约三四点钟,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门口增加了岗哨。
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刚进去那会儿,押我的小战士揪着我的领子往前推搡。我受不了这个,说:“你别推我行不行?要我往哪走你说话,你让往哪走我就往哪走。”这一反抗还真有用,后来他们再也没有碰我。
我被关在二层楼的一间单人牢房,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的窗口。牢房内有一个小厕所。最令我不习惯的是厕所门上也有监视窗口。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牢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窗户,开饭时就打开这个小窗,把碗递出去,外面给装上饭菜后再拿进来吃。
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或小米稀饭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给的饭菜没谱,有时很少,吃不饱;有时又特多,吃不完还不行。平时每天就是在床上干坐着,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规定“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着东西。
有时我坐着没事,就捻头发玩,消磨时光。有次被哨兵从门外看见了,马上喊:“你手上是什么东西?”12年的铁窗生活,每天面对这个铁门,使我至今不喜欢防盗门。
刚开始的半年,不放风,也不给报纸看,外面情况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日子。后来给放风、看报纸了。放风是一个人一个人轮流放,放完一个人回到牢房,再让另一个人出去,互相之间不照面。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传着看。从这个房间传到那个房间之前,监管人员都要仔细察看,检查上面写了字没有?扎眼或者做了什么记号没有?就怕犯人之间传递消息。
中间有一段让我出牢房打扫卫生。这是我最高兴的,因为可以趁机活动活动身体。
没事老盼望提审,因为可以有机会说话
同后来相比,二楼这间牢房的条件还算是好的,比较干净,床上的被褥是白色的。那时过年过节还能吃到带肉馅的包子。估计在这里住了大约有一年半。有一天突然将我转到一楼的一间破旧牢房。各方面条件明显降低,牢房阴暗潮湿,墙壁的下半截全是大片的霉湿斑,伙食之差就不用说了。
有一阵子忽然要我洗床单,有时一天洗十几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凉水洗。给我洗床单用的木盆很大,厕所的小门进不去,洗的时候只好用一个小盆在厕所里接水,一点一点地舀到大盆里,洗好了再一点一点地倒回去,来回折腾。尽管洗床单很累,我还是高兴,总比老在床上坐着好,可以利用出门晒床单的机会活动一下,等于延长了放风时间。
后来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把我转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没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监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监狱里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院子,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那阵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积水,两脚就经常泡在水里。那时正是盛夏,天一晴,烈日暴晒,帐篷里像蒸笼。一到晚上,又到处是蚊子。我常常用报纸捂在脸上,以阻挡蚊子的袭击。
我在秦城监狱12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有时我老猜左右房间关的是什么人,有几次零星听到一点声音,觉得好像旁边关的是严慰冰,也不知到底是不是?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少奇同志最后留给我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成丧失立场。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
那段时间少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
胡耀邦听说我仍被限制自由,安排我搬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央组织部接收专案工作的当天,就果断地将我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并安排孩子们和我住在一起。我终于结束了将近12年的囚禁生活。
刘源(刘少奇儿子):妈妈刚放出来那会儿,住在厂桥的中办招待所,就是现在金台饭店的前身。那时“四人帮”的残余势力还存在,“文革”中的“三种人”还没有得到清理。有人就来交代我妈妈说:“你现在虽然放出来了,但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恨你。你不要随便外出,否则安全不保。”这样一来,弄得招待所很紧张,很难办。我们一听很生气:这算什么呀!人都放出来了怎么还限制自由?
我就去找胡耀邦同志的女儿胡曼丽,请她向耀邦同志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要求给我妈妈换个地方住。胡曼丽一听也很生气,回去就跟她爸爸说了。耀邦同志听后说,马上请光美同志搬到翠明庄去住。翠明庄是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耀邦同志那时兼中组部部长。这样,妈妈很快搬到了翠明庄。
耀邦同志家那时在离翠明庄不远的富强胡同。我陪妈妈去过他家一次。谈话中耀邦同志说: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况下,通过少奇同志审查报告的会上大家都举手了,只有陈少敏同志一个人没有举手,所以你们见到有些同志时不要有情绪。
那时陈云同志家在北长街,也离翠明庄不远。有一天我陪妈妈散步,一路到了陈云同志家门口,也没有事先通报,就对门卫说,如果陈云同志方便的话我们去看望他。陈云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话中他说:少奇同志是一定要平反的,但现在还不到时候,“四人帮”搞了那么多诬蔑不实之词,他们随意定案,但我们就不能像他们那样草率,要非常严谨。
陈云同志还说:“你们家的孩子,这么多年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一封也没有丢,都在这个抽屉里。”
1979年的春节,我和孩子们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会。此后,为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各项工作按部就班地展开。5月13日上午,中央派出专机去河南郑州迎取少奇同志的骨灰,要我和孩子们前往。当天下午,我们在省里同志的陪同下,从郑州到开封。
我们来到少奇同志逝世的地方。一进那小屋,我一眼就见到了少奇用的枕头,急忙跑过去,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睹物思情,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对枕头,是1963年我们访问柬埔寨时西哈努克亲王送的,没想到它伴着少奇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致悼词。追悼会进行过程中,会场上不时传来抽泣声,好多人都哭了。我看到徐帅徐向前同志胸前衣服上被泪水湿了一大片。散会时,小平同志过来,握着我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
在治丧活动过程中,不少人提出,鉴于少奇同志逝世的特殊情况,应该保存他的骨灰。中国革命博物馆来人要求说:毛主席进了纪念堂,朱老总进了八宝山,周总理撒向了江河大地,少奇同志的骨灰交给我们革命博物馆保存收藏。我没有同意。
少奇同志生前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死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早在1956年4月,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一起,第一批在提倡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名。当天回家后,少奇就向我讲了这件事,并进一步提出不保留骨灰,像恩格斯那样把骨灰撒在大海里。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险的时刻,他又一次向我和孩子们作了这一遗嘱。因此,我郑重地向中央和治丧委员会提出,尊重少奇同志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5月19日上午,在治丧委员会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们护送少奇同志的骨灰,由北京乘专机抵达青岛海军军港。海军派出了一艘驱逐舰、四艘护卫炮舰,执行散撒少奇同志骨灰的任务。中午,五艘军舰编队驶向黄海海域。午后1时许,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我们满含热泪,取出少奇同志的骨灰,撒向滔滔奔流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