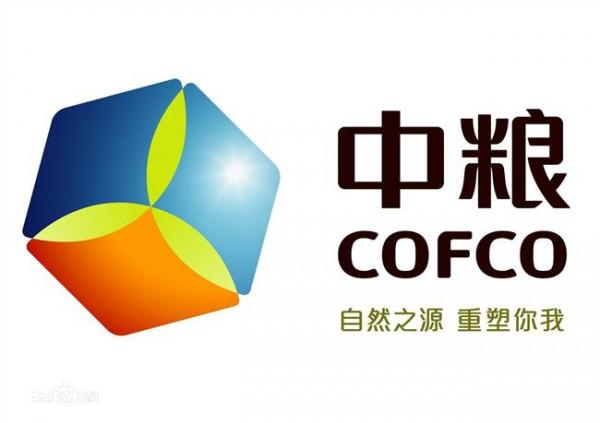余静赣被抓起来了 章文岳:重新被抓起来了
象山之行,毫无收获,倒带回一身的失落。回家时老娘无甚话语,连去何处也不问;反正她已按约作了汇报,送“客”的日子临近了。我自然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觉得反常而已。次日,我即去柴场打柴。砍倒了一些青柴,把几日前砍倒晒干的捆缚,装成一担,提早挑回陶公山来,以便沿途出卖。我确实在准备再度外逃的路费了。
象山之行不是毫无意义,它是一次远行的尝试。要不是对手不在师院东大楼操场边拦截我;要不是突然中止我的保外就医期,十天半月之后,我也不会呆在家乡了。最可能是先去上海,在上海碰运气;然而收拾了干柴,乘便船,我从曹家山头上岸,没人要买。便挑上环山路回家,快到师院操场,迎面来了一位白无常--民兵队长许二海。
“文岳!”他拦住我的柴担,下达命令:
“大队叫你办公室去一趟。”
我没有啃声,在他面前停顿一下后,继续我的行程。可是他一直尾随着,我自知不妙,心沉沉如坠。争相对毛泽东表忠的公安局的造反派们,绝不会放弃将我逮捕以图表功的机会的。然而我这书呆子还存在着此去也许把我安排在劳教部门的幻想。
我将柴担挑到我的住舍门边放下,说:“你将子华叫来,我要取洗换的衣物。”
“不行!现在就走!”许二海恶狠狠的。但他只动口不动手。精神上他自知低下。
正在争吵不休的当儿,邻家的大妈说她家女儿已将黑炭(子华)叫来了。他这黑炭绰号是他皮肤黑黝黝之故。工友们也叫他《七侠五义》中的黑侠狐智化(子华)。我朝下面小梯石阶路望去,只见我的屋主人飞跃的上来了。一把将我与许二海隔开,他气虎虎地站到民兵队长面前。无常瘦小,退后一步说:“你干什么?”
“让他吃饱了再走!”我的患难朋友斩钉截铁的口气,似乎不容讨价还价。
“不行!”无常仗着鬼王之命在身,不想妥协。
黑侠狐立即扬起拳头,我连忙一把拉开了他。说:
“他是奉命的。我不饿。你保重。后会有期。我的衣物你交给我家里吧。”我转身对许二海命令似的:“走!”
我被带进南安桥畔的大队办公室,那是一幢带小阁楼的三层建筑。我就被关进了小阁楼里。
狭小的阁楼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四旧”扫来的战利品。那是一些谈不上有什么文物价值的,诸如陈旧的黄缎马褂、绣花鞋、锡质烛台、铁制香炉、撕碎一角的祖宗神像以及断臂缺腿的泥木菩萨。据说大岭墩上的尼庵等处被农民红卫兵洗劫一空,而有价值的东西已无影无踪。
王家(建国前夕工运领袖王孝和出身地)大岙底的安仁尼姑因阻挠农民的革命行动,而被拉到大街游斗。我村大队会计朱居士的家也被抄,本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我大队在四清后已并入马阿来的红卫大队。
建国以来,与历次政治运动配合的大抄,与个别镇压结合的小抄,已经胜不胜数。大陆民间的财宝已被搜括一空。这些财宝是不会少于大陆三、五年的国民收入的。都到哪里去了呢?除去一部分被埋入地下,或藏匿不知去向,打着革命照牌的假洋鬼子们(如康生之流)早将最值钱的国宝或古玩,顺手牵羊而去。
据一份《林彪集团成员到文物库房拿走文物的记录》的材料透露:“林、叶(群)的秘书竟来了文管处三百多次,陈伯达及秘书来了139次”,而且如入无人之境。
仅林、叶就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唱片1083张……,价值343万多元,而实际付款七百六十六元五角五分!其后江青人又窃夺了一阵,她选的一块18K的法国怀表,表上镶嵌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7元钱。江青是毛泽东家里的内当家,窃夺更是“打江山、坐江山”支票的一点兑现。那些不会理财的败家子们又将一些稀世珍宝当成废纸或废物投入熔熔燃烧的高炉……
也有几个名家如曾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林风眠,在红卫兵抄家前,抱定“与其被抄,不如毁之”的理念,将一千多幅作品,泡成纸浆,倒入马桶,用水冲走,演出了艺术大师悲壮的一幕。
我进大队办公室时,所有大队干部都没有出面,都不愿以恶人亮相。那个许二海把我小阁楼的门关锁了。要撬开是很容易的。但下面不会没有人,我未作蓄意的潜逃,因为不知道劳改队已成了人间地狱;有幻想,把我安置在劳教部门自食其力吧。
我没有话说,也不提什么抗议,说大队无权这样做。我知道这是公安局的指令。即使我忍不住大吵大闹,马阿来他们必然好说歹说一阵,最多叫公安人员立刻从宁波赶来,我的人身一样失去自由。
我席地而坐,痴痴地。许二海又上来看一下,这小板门是经不起猛力推撞的,他不放心。说实在,身无分文,想逃与逃不出宁波范围。他说:
“我明天带你去宁波。这是命令……”
他带着“我也是奉命行事的呀”的口气,别说他六亲不认呀。只是我不理他,从小就对他地痞型一家保持距离。对我做豆腐谋生的外来户常耍无赖,要敲竹杠的,小时的记忆尚未抹去。
带我到宁波去!宁波就是公安局了。对我“越境嫌疑”下一个结论,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必要程序,但我万万想不到此一去就是一十二年,要是知道这长期非人的炼狱,饥饿、拷打、脚镣及犯人霸头的欺凌和侮辱,我无论如何要作一下冲刺,在市内街巷中逃跑的。
刚才上来经过二楼办公室时,书记马阿来他们静听着我上楼的脚步声,坐在里面。许二海催促我往三层阁楼走。我在三楼楼梯口停下,转过身去,对着这位老一辈的象山老乡,也对着乡亲干部们,大声重申:
“我是相信社会主义的!”愤懑,抗议,不平的心潮中跳出这句话来。
“是的!是的!”马阿来站起来应酬。他是真诚的,又象玩世不恭地点点头。众干部则默无一言。老马应该记得:52年暑期,我带领几个回乡同学,前去祝贺他所创办的陶公山第一个互助组的成立。我还送了一本《苏联画报》,喻示着中国农民的美好将来。这画报虽从旧书摊廉价购得,也足以说明我十六岁那年就钟情于社会主义了。
然而,谁理解我内心的不平和不幸呢?我“相信社会主义的”呐喊又打动了谁的心呢?被混世魔王搞乱了的天下,还有什么是非曲直!此时此刻谁也救助不了我。一切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即派性和个人利益的需要,难道毛泽东和林彪不相信刘少奇、彭德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吗?
夜来临了。九妹送来了一碗冷了的蛋炒饭。胃口全无;饥饿感不知去哪里了。干巴巴的,我说不要吃。这位从小受到:大哥是白虎星和讨债鬼投胎误导的13岁的小姑娘,见面也不叫我一声哥哥。她看我坐在地板上一副发呆的样子,老起嘴脸,语气中带着教训的口吻,但也不无亲情地说:
“你为什么要去象山呢?关照过是不能乱跑的。”
意思是祸水自招,咎由自取,怪不得家里啊!
其实,造反派主宰的鄞县公检法,并不真放我,一旦认为我身体能正常活动,就将我这个明文批毛的书毒头,成为本县忠字台上的唯一祭品。
老娘有一次当街扬言:
“劳改有什么(可怕)呀!王家那个叫翠香的地主婆,在劳改队烧饭,五年期满回来,反使白胖了起来。丹城济民姑丈,让白虎星检举,改造出来,也是好好的。什么自由!在现今年代,有口饭吃就好。街上要饭的,好多跑进去了。”
所以老娘把我推到劳改队还是理直气壮的。无知和刚愎自用如果与自私相胶合,便可以将亲生儿子置于死地,即使儿子的天分很高,有口皆碑。
天气还不冷,我就这样坐着坐着,天全黑了,也不管下面民兵看管得怎么样,和着身上的一件单衣躺了下来。由于白天打柴挑担的劳累,兼之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身心都感疲乏,不久就睡着了。
有什么办法?撬开容易脱卸的板门,没有钱,能往哪里逃?鱼儿搁在三层楼,还能游么?惟一的只好束手就擒,争取一个宽大处理,无可奈何地劳教三年。最好留在看守所干胡子所干的活。只是我一定让他们吃得卫生,尽可能让他们吃饱,如果发到手中的口粮不够最低限度,我就首先考虑政治犯的需要。
死是不想的,因为毛泽东会比我早死。他死后,我坚信便可生存发展,不是么,中央内部也有这么强大的反毛力量,连第二号人物都是敌人,这位异想天开的超级大帝不断地制造着自己的对立面。我想我至多再熬上五年至七年吧。
第二天一早,家里没有来人。意味着昨天那顿冷炒饭是“最后的晚餐”了,把自己亲生的儿子,小时当成自己命根子的儿子送上了祭台。这祭台是鄞县公安局内造反派和投机干部们为献忠于毛泽东所建筑的。本县范围内就只这样一个书毒头,岂能错过。
许二海来解押我起程了。路经许家祠堂。正在乡下小住的上海亲家婆就站在早已停业的药房“杏春堂”后门的阶沿上。她是在乡下老家避暑小住的。见了她,我以为她是为我送行的,但她把脸侧了转去。我也就免了叫一声“亲家娘”。显然她是想证实一下“文岳又被抓走了”的纷纷传扬。
她的表情说不上难过,但也不是高兴,多少有点不安感,基调是与已无关。在我打成右派后几次去上海她家讨扰,还保持了礼数周到。孩子的大娘舅么,老话说:娘舅大来头。为了大姐常受婆、夫的礼教束缚,我曾在二姊催促下,对她们母子讲了大道理,写过夫妻平等,反对专横的去信。
想不到一过她的身边,许二海就老着嘴脸对我说:
“你亲家婆向我告过状,说你骂她!”
这使我很吃一惊。虽没有答理这位尖嘴民兵,但我心里纳闷:我从来不骂长我一辈的人呀?说不定把我讲道理当成骂人了。”
前面就是碾子弄口。右侧那家妇女正在骂街,说昨夜有人纵火,将火把投进了她家的后窗。幸而未点燃灶前干柴。她是在骂我那个与她积冤很深的二姐。二姐是否在为我制造混乱场面,在干部救火的纷乱中让我脱逃呢?
约在一个月前,这个妇女伙同她的邻居赶到二姐家,揪住二姐头发,狠命的乱拉,我刚路过闻声赶去,将二姐解脱出来。头发已被扯断了好些。很可能这位同情弱势常有仗义表现的二姐,是想趁村干部忙于救火的混乱时刻,让我逃生。
二姐此时却未露面,我也从未想得到她的资助,因为我这书呆还没有燃眉之急。不知道此时的劳改场已成了法西斯暴政的实验场,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我没有火烧眉睫,因而也没有千方百计凑路费逃生。二姐是同情被压迫者的,她直筒子,有侠义心肠。如果我恳求她,她会背着丈夫解囊相助的。只是她性格外向,多嘴多舌、乍乍呼呼,常招惹村里一些强悍妇女,摈弃了忍让低调的家风。
在我父亲长期工作和经营过的饮食合作商店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竟有个从师院大楼上跑下来的学生。这群人预先得到风声,在这里候着。出于好奇心,还是看热闹?还是记下这历史的瞬间?他们的脸色是凝重的,都避开了我顺着过去的目光,垂下了脸面。那个年轻学生还有点惊惶神色,见了我生离死别的目光,也垂下了脸儿。无疑这位北京学生界57探花,建国后陶公乡首位大学生、社会主义冒死探索者,此去凶多吉少,似都心头沉重。
我没有止步,一步步地,沉重地,缓缓地,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微笑,一种尴尬的笑,向他们说道:
“(乡亲们)我(不过)是想到苏联去(生存发展)。”我并没有停住脚步,回过头去继续说道:“我会回来的(乡亲们)!”(可惜当时无人录音,原话一字不差。)
这时候,我又突然觉得自己正在扮演类似关云长单刀赴宴,正气凛然的角色,我并非刻意追求这一英雄的角色。也想不到一大早就在饮食店门口聚集着这么多的一群人,其中有我所喜欢看到的年轻大学生。说实在,我这是临场发挥,即兴表现。似有神灵指点一样。那时候,由于我身后跟着一个无常爷吧,谁都没有吭声,谁都沉默着,看我离去,走向人人都想竭力规避的炼狱之门。
后庙湾摆了渡,在摇摇摆摆的湖面上,遥对家乡山岗上两幢自我打成右派回乡后,与我交往了七、八年的师院大楼,想起了在阅览室里与闵文的一场冲突。
有一天,我正在浏览《越华报》,我想从中获得越南对中苏论战的看法。胡志明当时采取两方面友好的态度,但或许在他国内出版的报刊中能有一些独立的见解。渴求知识的天性必定这样那样地去消化品味,按需要去吸收、批判地选择合意的东西。那时候如能发现微妙的差别,也有助于对中国党由于极左的主宰犯了路线错误的判断。老百姓对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现象已经厌恶了,不愿看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