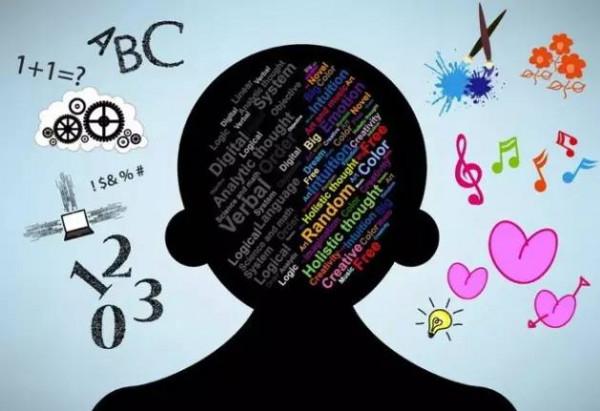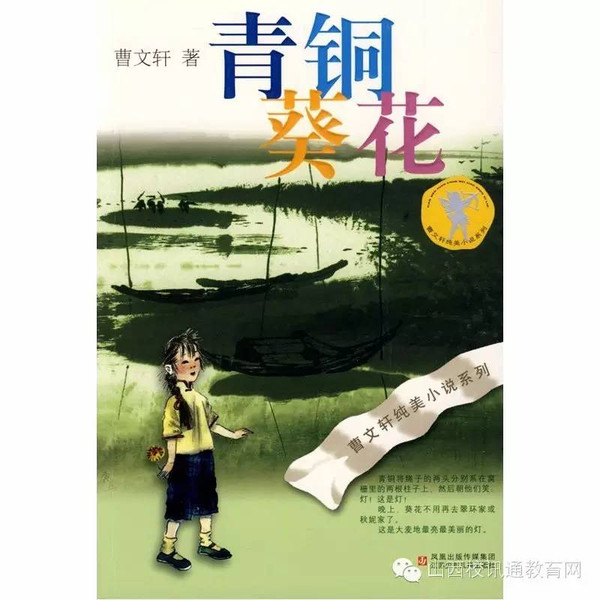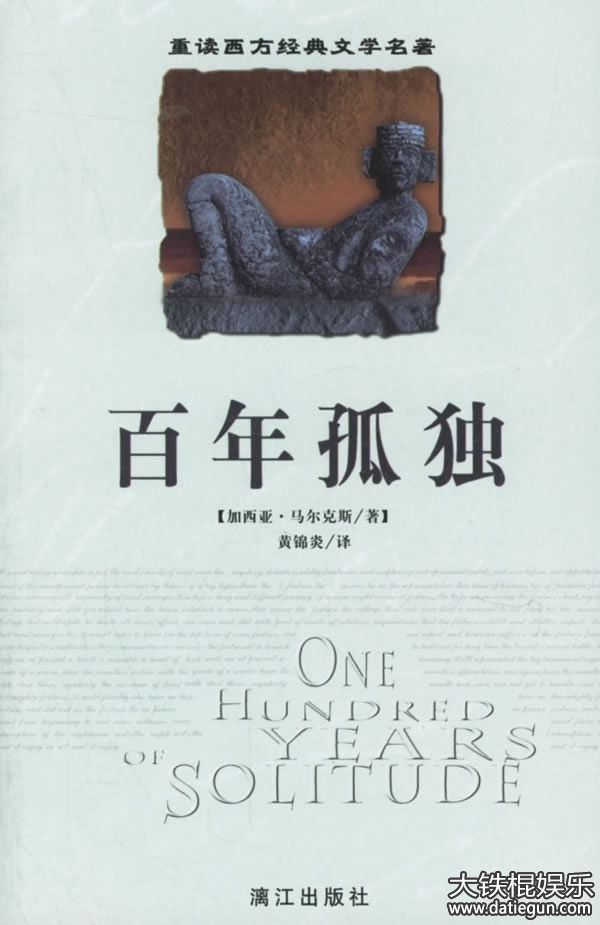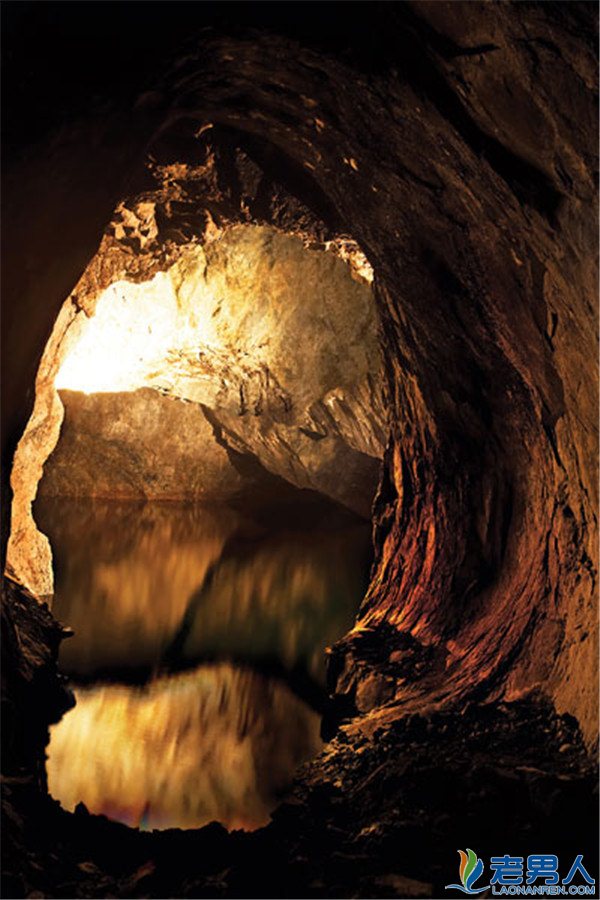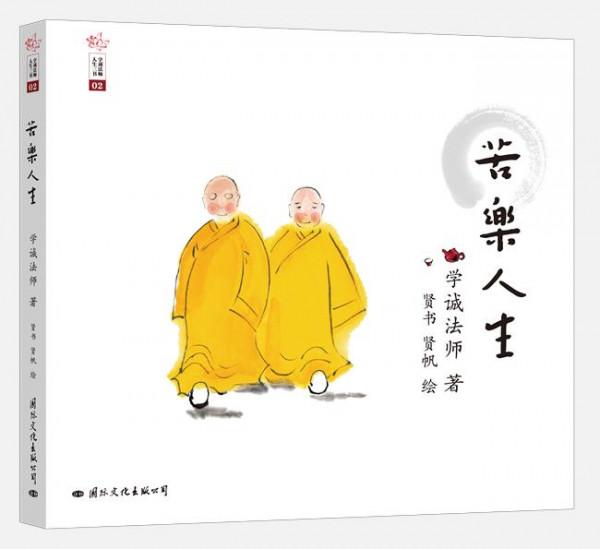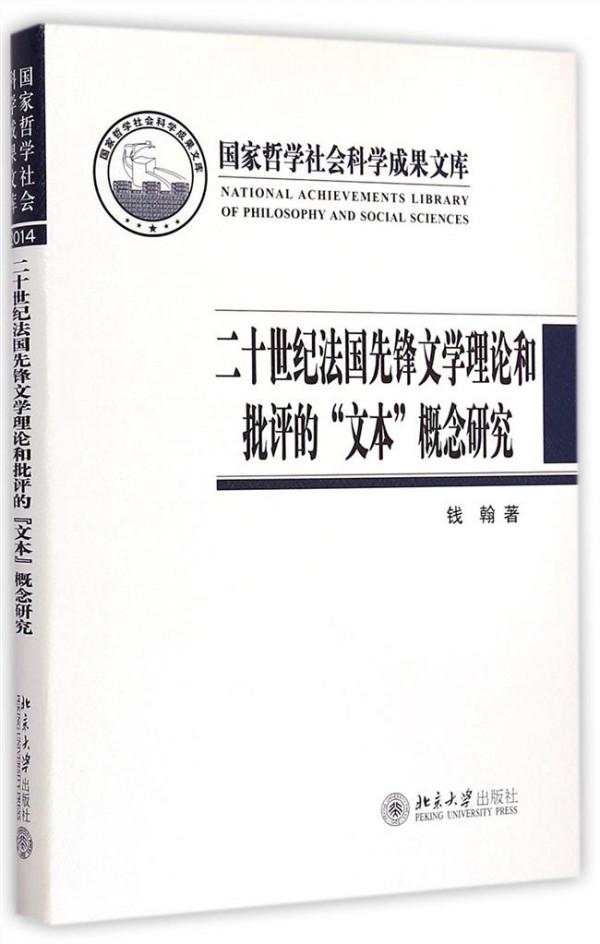谢有顺恐惧折磨着我们 心怀恐惧的写作者——读谢有顺《我们并不孤单》
心怀恐惧的写作者——读谢有顺《我们并不孤单》 ■丁国强 我们正在陷入一种精神麻木之中,虽然也有王朔那样的放言无忌者大声叫嚷:“无知者无畏”,但是,毕竟只是一种虚晃的姿态。那种“无畏”是硬着头皮说出来的,掩饰着心底莫大的空虚。
近读青年评论家谢有顺的文集《我们并不孤单》,有一个陌生而又真实的字眼刺痛了我——恐惧。在听够了“我是流氓我怕谁”叫嚷之后,我们终于听到了一个细微而坚硬的声音。 这个声音在当下秩序混乱的文坛是不占上风的,在这个文字泛滥的时代,对写作怀有恐惧的人极为稀有。
因为写作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表达自我思想,而仅仅是为了占有某种资源或者是寻求一种量的复加。写作者越来越疯狂,他们漠视写作的意义,逃避现实,拒绝沉重,他们下笔万言而言不及义,干瘪的思想与枯燥的语言霸占着媒体,无休止地折磨着读者的神经。
写作已不再需要理由,复制者的乐趣在于发表,“不发表就死亡”这是互联网时代的逻辑,只要有人扫上一眼、点击一下,就足够了。
写作的危机,不仅是话语的危机,也是价值的危机。在取消了意义设定之后,写作就成了一种盲目的游戏。所谓的“大众”是一个无底洞,也是一个垃圾箱,纯正的写作者被看做是患了洁癖,反而吃不开了,那些粗制滥造的写作者格外风光,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他们所从事的也是一种掠夺性经营,文学的土壤变得越来越贫瘠。谢有顺如此发问:“图书馆的书已经汗牛充栋了,我是否有必要再写几本?”失去内在的精神标准控制的写作是缺乏自省的写作,这种写作是不计后果的。
无论是媚俗还是自娱,我们看见,那些文化泡沫的制造者已变得肆无忌惮了,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可在乎的了,语言的纯净、良心的维护、真实的存留等等,似乎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
谢有顺提出:“我们没有义务为粗俗而无关紧要的事物卖命。”是啊,把生命耗费在这种无根蒂的写作上面,真可谓是文化自残。 《我们并不孤单》一书的首篇就是《人为什么恐惧》,我相信,谢有顺的恐惧是发自内心的,唯有承认并遵循规范的人才会拥有这种精神伤痛。
只有正视人自身的有限性的人才能够真正克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对“不存在”、对“死亡”的恐惧,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用狂妄姿态来掩饰内心恐惧的人不但虚假而且也背逆了人类的本性,“无畏者”注定不可能成为思想者,他们只不过是些跳梁小丑而已。
心怀恐惧的写作者会时时提防自己内心的黑暗,用理性来审视自己的生存处境,鲁迅先生就是一位清醒的思想者,他之所以“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正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只是一个“过客”,他并不想去终结什么,更不想把持什么,他的反叛来自内在的精神需要,为了摆脱奴隶的身份,为了获得做人的资格。
鲁迅从来都没有夸大自己的力量。
那些利用鲁迅来为自己壮胆企图借机上台阶的人是最大的亵渎者,他们把鲁迅当成了文攻武卫的工具,这不但是时代的悲剧,也体现了人性的缺陷。谢有顺发现,恐惧感的沦落导致了政治社会和消费社会的精神贫血。批判需要分析和辨别,不加节制地攻击一切,最终连自己也会粉身碎骨。
对当下境遇的隔膜和疏远也会造成“无畏”,凌空蹈虚的文字是空虚的。谢有顺的追问是一针见血的:“诗歌到底与什么相关?”如果把诗歌封闭在一个抽成真空的玻璃容器里面,诗人岂不成了按规程操作的技术人员?诗人如不确立“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精神基点,那么,他的写作就很难牵动心灵。
谢有顺强调:“诗性守护的不是知识或技术”,以“伪生活”为依托的写作是可耻的,因为它所制造的幻觉麻痹了我们的感官和神经,使我们不再习惯真实和纯洁。
关怀人的生存是诗人的责任,对于这一点,谢有顺的态度十分坚决,他主张抛弃所谓的“复杂诗艺”而让心灵在场,只有这样,与“我”相关的存在以及存在的细节才会去贴近颤动的词语。
关切存在的诗人是诚实的,他们向灵魂交待了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写作的质量在于直面现实境遇和内心冲突而不在于逍遥和超脱。被欲望所支配的快乐是不真实的,唯有精神困境中的紧张才是心灵的真相。 在心灵的真相面前,谎言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