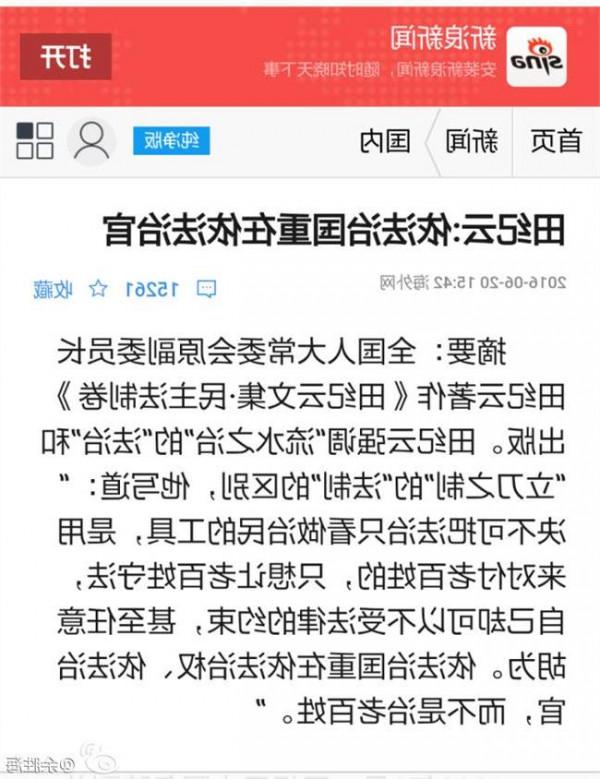许纪霖美国自由主义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随着东欧与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自由主义在整个世 界又重新大放异彩。它在90年代的中国也重新起步,成为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可能性选择。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潮,基本形成了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种思潮互动的格局。
自由主义思潮及其运动尽管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压制,但在知识份子阶层之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究竟如何,不仅取决于一系列社会政治因素,同时也有赖于自由主义自身的成熟。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两种可供借鉴的资源。第一种资源是众所周知的,即外来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历史经验。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有另一种本土的资源,这就是本世纪上半叶那一度相当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多少年过去了,它们沉淀在岁月的尘埃之中,几乎被民族的集体记忆所忘却。这些本土的经验与历史一旦发掘出来,重新加以反思,对于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来说,恰恰是一份独特的、富有启迪性的历史遗产。
毕竟,中国也有自己的自由主义传统,我们应该加以珍惜。
一 修正的自由主义思潮
如果要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在此之前,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严格说起来,严、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只能算作自由主义的先驱。只是到了五四时代,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份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不过,有了自由主义者,不一定就意味着有了纯正的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可谓生不逢时,时运不济。因为到了本世纪初,不说中国,就是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欧美诸国,自由主义也已经乱了套,产生了各种杂交和变种。欧美的自由主义,从十七世纪的苏格兰学派的古典自由主义,经十九世纪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自由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初,由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暴露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在宏观经济控制和伦理道德上的种种弊病,开始与其他思想流派(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杂交,呈现出各种各样的修正趋势:有美国杜威式的民主 自由主义,也有英国费边社式的社会 自由主义。
从整个世界大潮流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正是各色各样社会主义风头十足的时候,相形之下,自由主义倒是风雨飘摇,步步后退,不断地修正自己,弄得态度暧昧,面目不清。
殷海光曾经说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按照殷先生的意思,先天不足,乃指自由主义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层意思:即使是舶来品,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份子所进口的自由主义,也多是修正型的,而对自由主义的原典,如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等人的思想知之甚浅,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个人自由的至上意义以及“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自然也体会不深。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先天不足,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出生伊始就缺乏纯正的性质,而只是杂交的产物。再者,同样是杂交,西方的修正型自由主义毕竟是从古典的一脉脱胎而来,对自由主义的那些最基本元素如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纵然千变万化,还是守得住;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或面临错综局面,就会有人背离,不是鼓吹“新式独裁”,成为“新保守主义者”,就是放弃理性的立场,倒向激进的革命民粹主义。
张东荪是一个深受基尔特社会主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这种“先天不足”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就人类言,最理想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的个人主义的陶养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中国没有经过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养而遽然来 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主要是从英美来的,一般被笼统地称为英美的自由主义。实际上,从美国进口的自由主义与从英国进口的有很大的差别。来自美国的主要是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 自由主义。杜威曾经在中国呆过二年,留下了著名的五大讲演,其中就有社会政治哲学十六讲。
经过其忠实信徒胡适的宣传和发挥,杜威的影响更是如虎添翼。他给中国自由主义留下的精神礼物计有三项∶一是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使胡适等人相信可以像知识研究那样,科学地、分门别类地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具体问题 ;二是渐进的、点滴的社会改造策略,鼓舞一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耐心地坚守文化教育阵地,从文化与社会的最基本改造做起;三是将民主的含义大大地泛化,推广到所有的领域,使得这一本来在古典自由主义辞典中纯粹的政治概念,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属性,因而也获得了普遍的、崇高的神圣性质。
二 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主流
不过,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舶来品中,最有影响的还不是美式的,而是英制的;不是大名鼎鼎的杜威,而是一个现在已经被我们忘得差不多的英国人,他就是拉斯(Harold Laski)。拉斯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著名的费边主义思想家,他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后来成为英国工党主要的理论家,1945年出任工党的主席。
尽管拉斯基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在中国的信徒却甚众,而且都是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中坚人物,如罗隆 基、王造时、储安平、张君劢等。
他们将拉斯基的政治思想于中国广泛传播,其影响之大,几乎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之主流。20年代末是拉斯基在中国最走红的时候。当时胡适、罗隆基、张君劢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云集上海,以《新月》杂志为中心,组织了一个费边社式的小团体“平社”,翻译拉斯基的著作,研讨费边主义的理论,并以此为借鉴,探求改造中国的自由主义方案。
30年代以后,拉斯基在中国的风头虽然有所减弱,但其理论已经渗透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深处,无论是他们的政治思想,还是其社会改造方案,随处可见费边主义的深刻痕迹。
拉斯基的费边主义,是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理论,他在保留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力图将它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调和起来,从而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发展出一变种,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试图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盼望已久的福音。
因为当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起步的时候,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在西方已经遭到了各种各样社会主义的严厉批判,已经部分地(至少在伦理层面)失去了其合法性。
西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几乎是同时输入中国的。古典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替资本主义庄严辩护的学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是找不到任何对应的精神资源的,而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苏俄式的,还是费边式或基尔特式的,都有可能在中国历史内部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抑制地对社会主义怀有偏好,这一折磨人的思想困境,在处于20年代初社会主义论战中的张东荪身上,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
尽管无可奈何的张东荪最后是以一种笨拙的时间性分段策略(即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暂时安顿了内心的困惑,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毕其功于一役”的努力。
在空间的层面上,拉斯基的费边主义巧妙地调和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使之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改造方案。它的出现,自然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欢欣鼓舞,也难怪社会民主主义会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潮了。
关于这种费边社的自由主义思潮,留英回来的萧乾曾经为它作过一个恰当的解释:
“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外也不支持作为资 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见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
在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无论是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王造 时的主张与批评派观点?还是当时产生了极大政治影响的罗隆基起草的民盟一大纲领,都可以看到社会民主主义的鲜明标记。用张君劢的话说,在政治领域是一种“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多党合作替代多党竞争;在经济领域则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即私人经济与国家经济、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混合体。
这种在自由主义架构内部的“国家社会主义”,无非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而已。
不过,资本主义自引进中国伊始,虽然被认为是国家富强必经之途,但总是暗含某种道德上的贬义;相反地,社会主义在现代中国则天生地大受欢迎,被想像为具有某种终极意义的社会乌托邦。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很少有人公开自称拥护资本主义,哪怕主张国家资本主义,也要以“社会主义”自命。
甚至连胡适,在20年代也一度对社会主义大有好感,他途经莫斯科三天,参观了几处地方,就激动得连夜给国内朋友写信,为苏俄“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大唱赞歌,并设想以“社会化”的方式建立一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
至于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更是深得中国知识份子的青睐,成为自由主义思潮中一道最耀眼的风景线。
三 观念的和行动的自由主义者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五四时代还处于朦胧的混沌阶段,与激进的革命民粹主义的界限模糊不清。到20、30年代,在杜威、拉斯基思想的催化下,渐渐分化出几种自由 主义的思潮。不过,无论是胡适的实验主义,还是张君劢、罗隆基的社会民主主义,都仅仅是思潮而已,而远远没有成为拥有深厚学理资源的理论。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对自由主义发生兴趣,决非学理的因素,而是由于现实的社会问题所刺激。他们对自由主义学理的关切,要远逊于对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设计。
因此,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在 学理层面上并没有多少研究的价值,真正有意义的,倒是思潮驱使下的运动??那种进 入政治操作层面的自由主义运动。不过,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运动(如好政府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制宪救国运动、人权运动、宪政运动等)尽管在20、30年代就层出不穷,但真正形成规模、具有全社会影响的,还要等到40年代。
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之所以到40年代才风起云涌,从自由主义者本身来说,是由 于组织化的因素。殷海光曾经将运动中的活跃份子分为“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他认为,在运动初始的宣传阶段,由“观念人物”占主导地位,到进一步的组织阶段,“行动人物”就脱颖而出。
我们也可以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划分为两类人∶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与行动的自由主义者。所谓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大都是知识体制里面的学院派人物,有著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通常曾留学英美或在国内清华、燕京、圣约瀚等大学接受英美文化的熏陶。
他们关心政治,却是一种胡适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即不离开自己的专业岗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资源,通过大学讲坛、同人社团 和公共传媒等公共领域,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精神领袖,在20、30年代聚集在《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等刊物周围,发挥著较大的舆论作用。这些文人书生,个人主义气息极浓,各自有各自的信仰和观念;又有着文人相轻的传统毛病,基本上是一盘散沙。
尽管其中的一些活跃份子如胡适,有时候会以一种费边社的方式,以个人的身分游说和影响政府中的高官,以推行自己的自由主义主张,但大部分人仍然坚守“君子群而不党”的信念,极其自觉地保持著个人精神和身分的独立性,拒绝直接参政,拒绝成为“组织人”,哪怕是组织反对党。
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作为一种社会道义和公共良知的存在,在自由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相当巨大,尤其在起初的宣传阶段更是功不可抹。
然而正如储安平所评论的:“政治活动不能没有领导人物,但是因为相轻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份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份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的,不是权力的,所以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是自由份子根本上的弱点。”
有鉴于此,一些自由主义者不甘心仅仅停留在观念和言论上,他们要进一步付诸行动,尤其是组织反对党,以组织化的方式和权力化的运作推进自由主义运动。这些行动的自由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