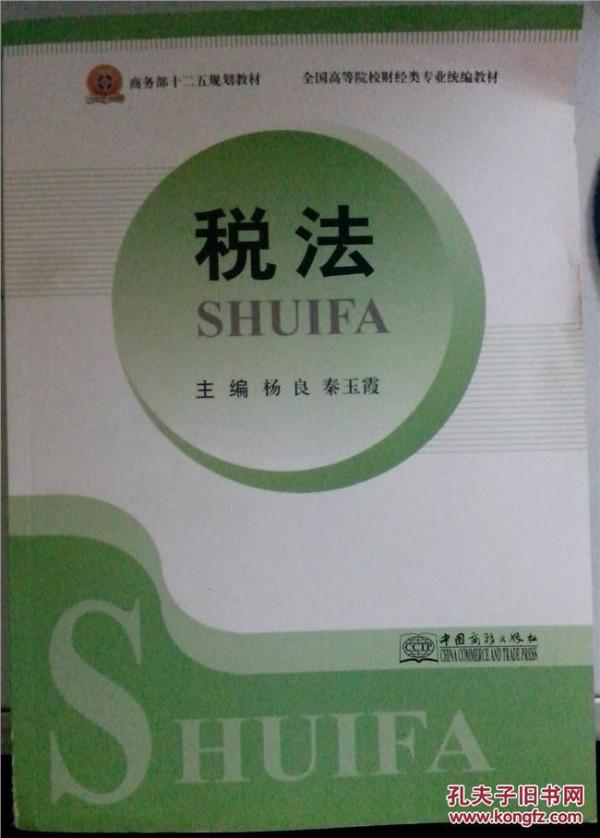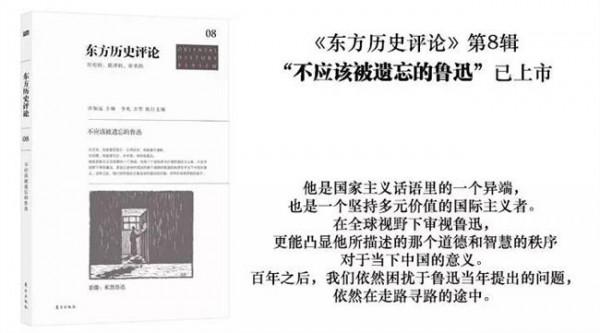许纪霖外公 许纪霖:新天下主义:重建中国的内外秩序
影响21世纪世界最大的事件,可能是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扩大,中国的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却出现了日趋严峻的紧张局势。在国内,国家的强大没有吸引边疆各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反而在西藏、新疆不断发生民族与宗教冲突,甚至出现了极端的分离主义和恐怖活动。
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的崛起让周边国家惴惴不安,东海、南海的海岛之争令东亚上空战争的乌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危险。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都空气高涨,呈相互刺激之势。犹如19世纪的欧洲,局部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危机的脚步临近家门,我们有化解危机的方案吗?治标的国策固然可以开列一张清单,但重要的乃是根除危机之本。这一本源不是别的,而是自19世纪末引入中国的民族国家至上意识,这一意识如今已经成为从官方到民间的宰制性思维。民族主义本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然而一旦成为君临天下的最高价值,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就像曾经在欧洲发生过的世界大战一样。
真正的治本之方,需要一种与民族国家意识对冲的思维。这一思维,我称之为新天下主义,一种来自于古代传统、又重新加以现代性解释的轴心文明智慧。
一,天下主义的普世性价值
何谓天下主义?在中国传统之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文明秩序,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国,“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1]作为价值体的天下,乃是一套文明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国不过是王朝的权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秩序,不仅适用于一朝一国,而且是永恒的、绝对的和普世的,国家可亡,但天下不能亡,否则将人人相食,成为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
当今中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如此高涨,背后乃是一种“中国特殊论”的价值观。似乎西方有西方的价值,中国有中国的价值,所以中国不能走西方的邪路,要走中国特殊的现代化道路。这种论调,看起来很爱国,很民族本位,却是最不“中国”,最反传统的。
因为中国的文明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天下的价值是普世的,人类主义的,而不是特殊的,某个具体的民族或国家的。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古代世界的轴心文明,就像基督教、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也是以全人类的普世关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以人类的价值来自我衡量。
当近代之后中国从欧洲引入民族主义之后,中国人的胸怀从此狭隘了许多,文明也因此而萎缩,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天下气魄,矮化为“那是西方的、这是中国的”小家子气。
毛泽东当年还讲“中国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民族主义的背后有国际主义的大视野。而如今的中国梦,只剩下一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
固然,古代中国人除了讲天下,还讲“夷夏之辨”,然而,古代的夷夏,与今天挂在极端民族主义者嘴边的中国/西方、我们/他们的二分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今人的二分思维受到近代种族主义、族群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影响,夷夏之间、他者与我们之间是绝对的敌我关系,毫无通约、融合之余地;而古代中国人的夷夏之辩不是固态化的种族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可打通、可转化的文化概念。
夷夏之间,所区别的只是与天下价值相联系的文明之有无。天下是绝对的,夷夏却是相对的,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但文明却可以学习和模仿。
诚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在中国文化之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2]历史上有许多以夏变夷,同化蛮族的例子,同样也有以夷变夏、化胡为华的反向过程。
汉人本身是农耕民族,而胡人多为草原民族,农耕中国和草原中国经过六朝、隋唐和元清的双向融合,华夏文化已经渗透进许多胡人的文化,比如佛教原来就是胡人的宗教,汉族的血统里面也掺杂了众多蛮夷的成分,从服饰到起居,中原的汉族无不受到北方胡人的影响,比如汉人最初的习惯是席地而坐,后来喜欢上了胡人的马扎,从马扎发展为椅子,最后改变了自己的习惯。
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不衰,不是因为其封闭、狭窄,而是得益其开放和包容,不断将外来的文明化为自身的传统,以天下主义的普世胸怀,只关心其价值之好坏,不问种族意义上的“我的”、“你的”,只要是“好的”,通通拿来将你我打通,融为一体,化为“我们的”文明。
然而,今日极端之民族主义者,视中国与西方为绝对的天敌,以种族和民族的绝对分野抗拒外来的文明,甚至连学术界里面,也流行着一种“西学原罪论”,只要是洋人的东西,就一概拒绝。不必讨论。他们判断是非、善恶和美丑的标准,不再有古人的普世尺度,只剩下“我的”狭隘立场,似乎只要是“我的”,就必定是“好的”,只要是“中国的”,就是无须证明的绝对之善。
这种“政治正确”的民族主义,看起来在弘扬中华文明,实质是将普世的中华文明贬低为一国一族之特殊文化。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只关注“什么是我们的”? 文化是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解决自我的文化认同,而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一国一族的普遍视野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中国的目标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而是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中国的主权,不容别人来说三道四”这类惯常语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在今天要实现的不仅是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梦想,而且是民族精神的世界转向。
中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到普遍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中华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
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是黑格尔所说的负有“世界精神”的世界民族,理应对世界承担责任,对传承“世界精神”承认责任,这个“世界精神”,就是在普世价值形态出现的新天下主义。
二,去中心、去等级化的新普遍性
谈到天下主义,周边国家的总会谈虎色变,担心随着中国的崛起,昔日那个骄傲自大、威震四方的中华帝国会起死回生,卷土重来。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缘由的。传统的天下主义除了普世性价值之外,还有地理空间的含义,即以中原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天下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第一个是内圈,是皇帝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第二个是中圈,是帝国通过册封、羁縻和土司制度间接加以控制的边疆,第三个是由朝贡制度所形成的万邦来朝的国际等级秩序。从中心到边缘,从化内到化外,传统的天下主义想象和建构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蛮夷臣服于中央的三个同心圆世界。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唐宋明的中原汉族王朝,还是蒙元满清的边疆民族王朝,在其空间扩张的过程之中,既给周边地域和国家带来了高级的宗教和文明,同时也充满了暴力、征服和柔性奴役。在今日这个尊重民族平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时代,如果有谁还试图重新回到以华夏为中心的等级性天下秩序,不仅意味着对历史的反动,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梦呓而已。
因此,天下主义需要在现代性的脉络之中予以扬弃和更新,发展为天下主义的2.0新版。
新天下主义新在何处?与传统天下主义相比,新天下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去中心、去等级化,二是创造一个新的普遍性之天下。
传统的天下主义,乃是以华夏为核心的同心圆等级性权力/文明秩序,新天下主义首先要割弃的,是这一中心和等级化秩序。新天下主义的所谓“新”,乃是加入了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在新天下秩序之中,没有中心,只有相互尊重独立和平等的民族与国家,也不再是支配与被奴役、保护与臣服的等级性权力安排,而是去权力、去宰制的平等相处的和平秩序。
更重要的乃是新天下秩序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没有华夏与蛮夷之分,不再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别,诚如古人所云:“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在新天下主义的内部秩序之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法律和身份上相互平等,尊重和保护不同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与多样性;而在国际的外部秩序之中,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国不分大国、小国,相互承认与尊重独立的主权,平等对待,和平共处。
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乃是一种“承认的政治”,相互承认彼此的自主性与独特性,承认各自民族的本真性。以‘承认的政治”为基础的新天下主义与传统的天下主义不同,传统的天下主义之所以有中心,乃是相信处于中心的华夏民族秉承天命,其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来自超越的天之意志,因此有中心与边缘之分。
在今天这个世俗化的时代,每个民族与国家的合法性源头不再来自那个普世的超越世界(无论是“神”还是“天”),而是自身的本真性。
各民族国家的本真性各有其独特的价值,一个良善的国际秩序首先需要各国相互尊重与承认。如果说传统天下主义是建立在天命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的等级性关系基础上的话,那么,新天下主义就是世俗化时代以“承认的政治”为原则的各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与相互尊重。
新天下主义,是传统天下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超克。一方面,超克传统天下主义的中心观,保持其普遍主义的属性;另一方面,吸取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原则,但克服其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狭隘立场,以普世主义平衡特殊主义。民族国家的本真性与主权并非绝对的,而是有外在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新天下主义的普世文明原则。去中心、去等级化只是新天下主义消极面,从积极面而言,乃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天下之普遍性,这就是共享的普遍性。
传统的天下主义虽然是一种全人类的普世文明,然而就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古希腊-罗马等其他轴心文明一样,其文明的普遍性格乃是通过轴心时期某个特定民族,以“天将大任于斯人也”的神圣使命感,出来拯救堕落的世界,从而将民族的特殊文化上升为普世性的人类文明。
古代文明的普世性来源于特殊的民族与地域,又高于各种特殊性,其与超越世界的神圣之源(神或者天)相通,形成一种超越的、形而上的普世性。古代中国天下主义所体现的普遍性价值,其源头乃是超越世界中普世性的天命、天道与天理,只是中国文明与西洋不同,神圣与世俗、超越与现实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神圣的天下普遍性在现实世界之中通过世俗的民意呈现出来。
即便如此,中国的天下主义与其他轴心文明一样,皆是以某个天赋民族为中心,然后完成民族精神的世界化转向,向周边和更大的领域扩张,从而建立起天下的普遍性。
而被艾森斯塔特所称之为“第二次轴心文明”的现代性文明,最初发生在西欧,然后向全世界扩张,同样具有由中心向边缘、由核心民族推向全球各个角落的轴心文明性格。
然而,新天下主义要消解的,正是传统天下主义与各种轴心文明的这种从核心民族向全球、从中心向边缘、从单一特殊性上升为同质普遍性的文明构成。新天下主义所追求的普遍价值,乃是一种新的普世文明。这种普世文明,不是从某个特殊的文明变异而来,而是各种不同文明所共同分享的普世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