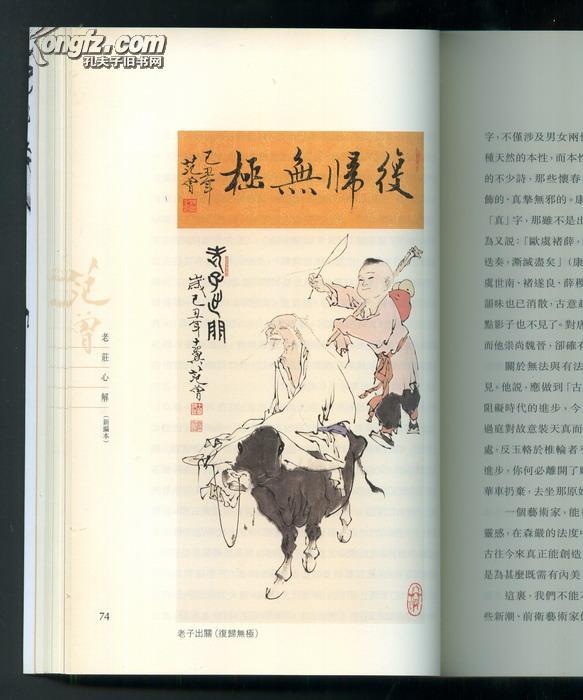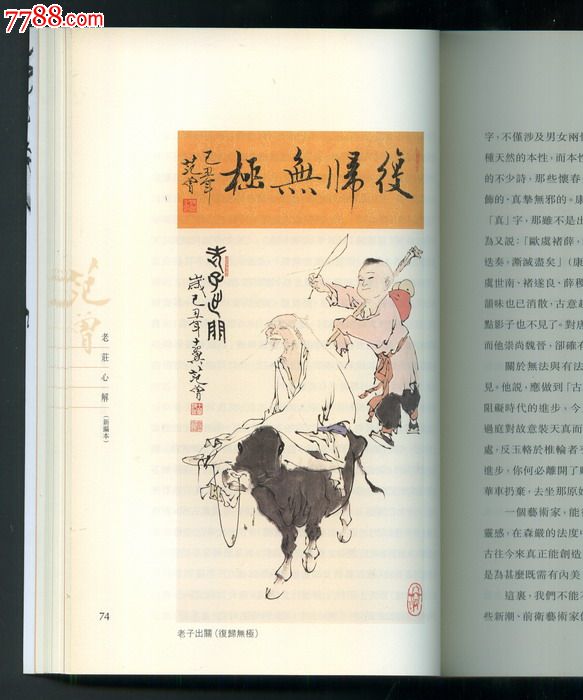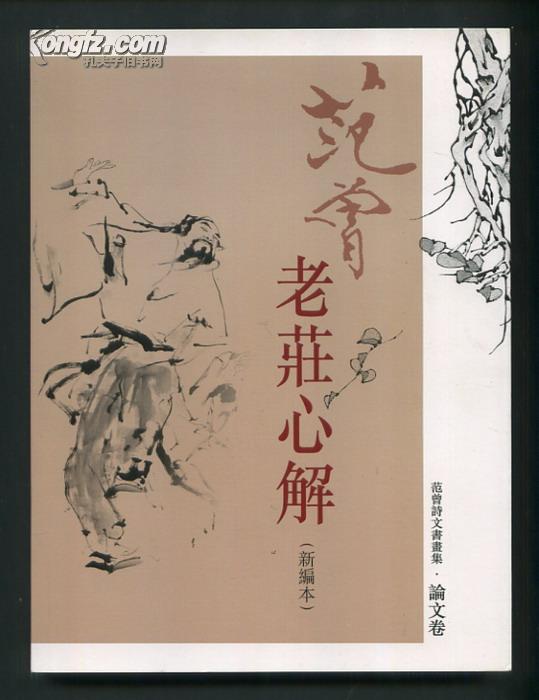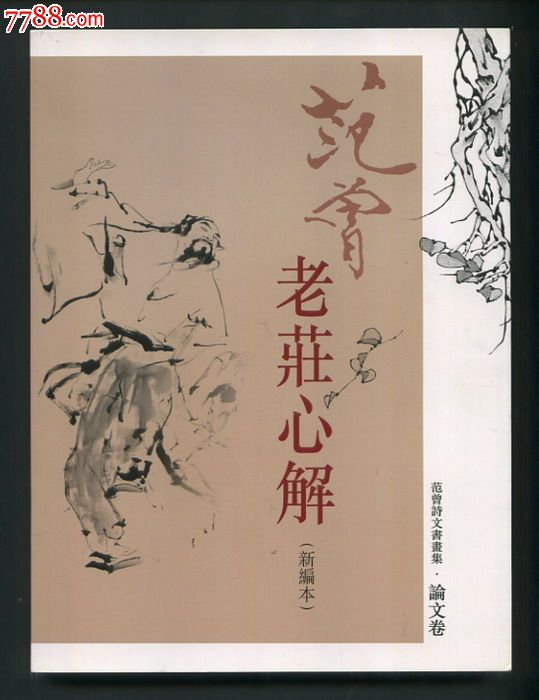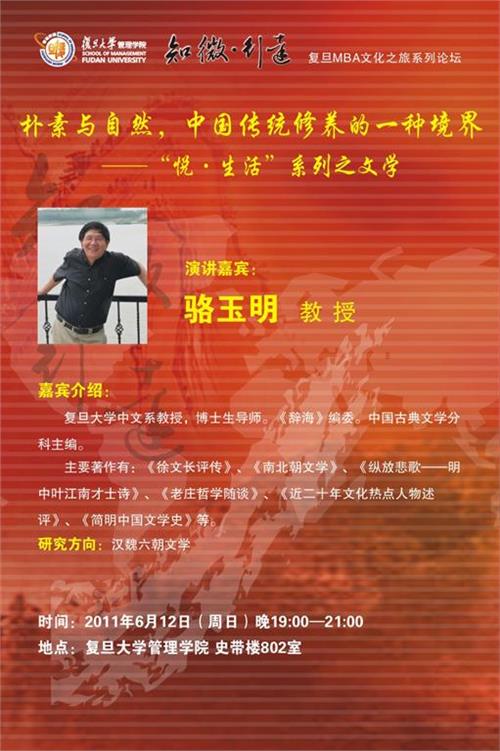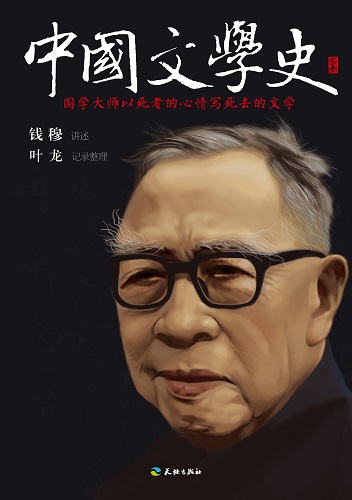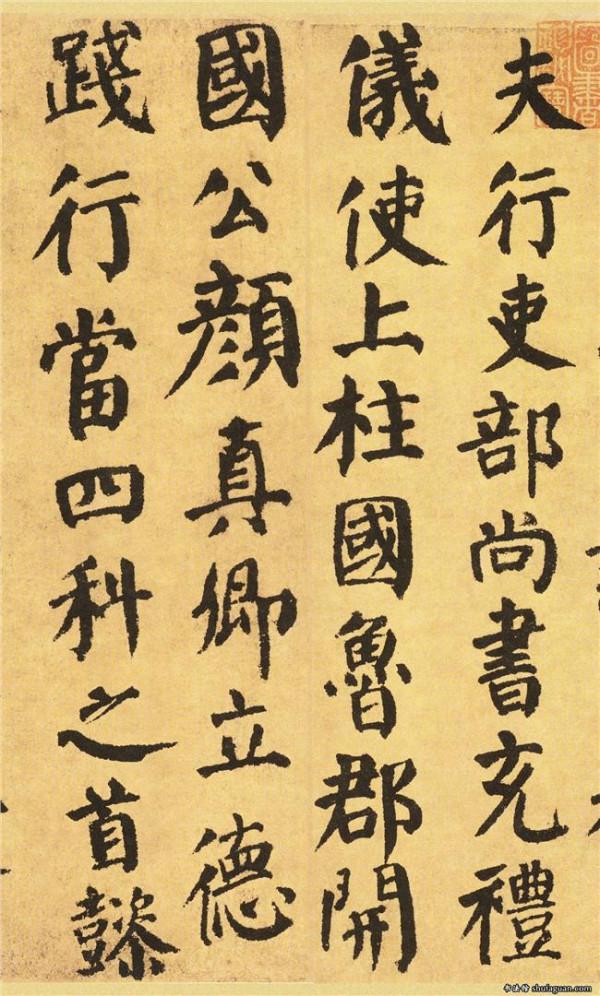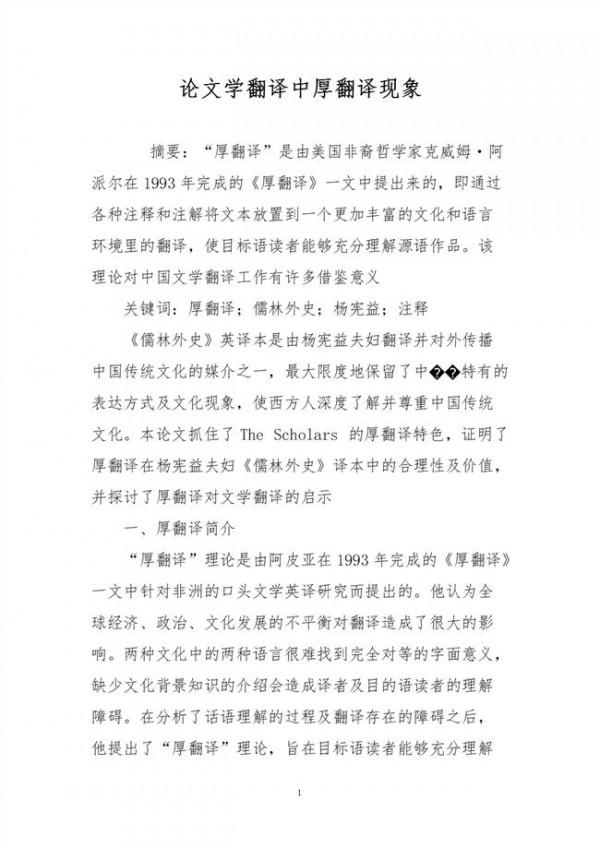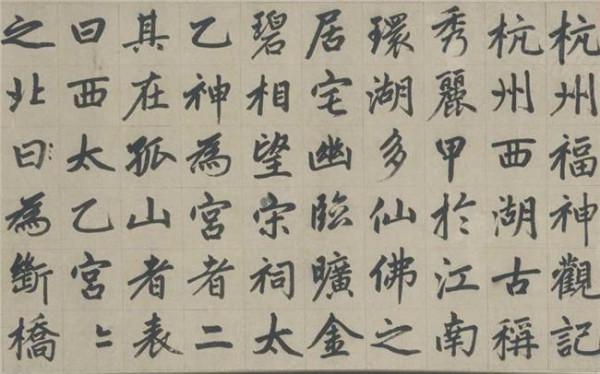《骆玉明老庄随谈》试读:天地不仁
天地不仁 “天地不仁”,后人常常用来表达一种悲愤的情绪。但在老子的本意,这是对于事实的冷静的说明。天地自然,故不仁,亦未尝有意加害于万物。 中国的一句成语,叫“怨天尤人”,很常用的。 以情绪强度的次序来说,应是“尤人怨天”。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遇到不如意不公平的事情,譬如受了人恶意的捉弄,免不了要“尤人”,指责旁人破坏了自己的生活。但是,倘若遇到太大的灾难,特别是那些无可理喻的灾难,我们就不止于“尤人”而要“怨天”了。
《诗经》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民今方殆,视天梦梦。”———人民生计艰难,老天却是一副昏沉不醒的样子。元代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中,那位孝妇无辜地被处死刑,她痛号道:“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 “怨天”不分古今中外,不过洋人是把“天”称作“上帝”。在人们的这一类怨责中,包含着一种久已习惯的意识:人世的公正和合理,在根本上应该是有保障的;即使我们遭受到某些不幸,归根结蒂应该仍会受到“天”或“上帝”的关怀眷顾。
总之,人类是被一种超越的伟大力量所爱着。这一种信赖,多少类于孩童对父母的感情。在基督教中,我们确实看到上帝被描绘成父亲的模样。 相信天或上帝的仁爱,普遍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中。
在古老的时代,恐怕没有一位哲人像老子那样,明白地、简洁而深刻地指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刍狗”是草扎的狗,用于祭祀的场合,其意义类于现代的花圈。当刍狗被郑重其事地扎成、郑重其事地放置在鬼神的灵位前,倘刍狗有知觉,它会以为自己确乎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 然而,到了仪式完毕,刍狗就被随便地扔到路旁,任由人猪狗羊去践踏。
天地间的万物,莫非如此罢?各自以某种形式存在过,随后化为残渣废料。
天地是自然的,自然的世界毫无感情,也就说不上仁爱之心。河里活着的鱼虾虫豸,忽然水干了,多少万生灵立即枯死。 人类本也受着这规则的支配,却偏偏自信特别为天意所爱,其实何尝有甚根据呢?洪水、干旱或者瘟疫,死起人来就是成千上万。
你若看见大饥荒的国家的儿童们瘦骨根根浮凸于皮肤之下,一群群等着死亡到来,不觉得这正是废弃的“刍狗”吗?更残忍的恐怕是人类自身。一颗原子弹的残杀圈内,就躺下几十万具焦黑蜷曲不可名状的尸体。
倘若有天意的仁爱存在,又怎能容忍这样的事实?获得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美籍犹太人伊利·威塞尔,写过一本薄薄的、内涵却无比沉重的小书,名为《黑夜》,记述了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在波兰的小镇奥斯维辛所建的集中营,于一九四○至一九四五年间,共杀害了四百万犹太人和反法西斯人士。那里的煤气室和焚尸炉,每天能“处理”六千个生命。作者记述道:当他们被迫看着一个天真可爱的犹太少年同成人一起被吊起在绞刑架时,有人低低地在他身后发问:“上帝现在在哪里?”而威塞尔本人,也就从这一天起抛弃了他一向虔诚敬仰的“天地万物之主”。
“天地不仁”,后人常常用来表达一种悲愤的情绪。但在老子的本意,这是对于事实的冷静的说明。
天地自然,故不仁,亦未尝有意加害于万物。所以人类的残忍,不能归于天意,或那个不存在的上帝的意志。并且,老子哲理,总是从自然之道引向政治方面,在“天地不仁”之后,是一句听起来更为骇人的话: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圣人”在《老子》中表示理想的、完美的统治者。这句话非但没有指斥的意思,相反,还是对理想的政治的描述。在老子看来,“圣人”的统治,就是效法于道。所以他不需要爱人民,当然也不需要仇视人民;他只是让老百姓自然而然地生活,耕耘纺织,各自度过他们的一生。
关于老子的政治思想,后面还将专门介绍,这里不多说。 也许可以这样说:相信天或上帝的仁爱,是人类幼稚时期的心理需要。所以上帝被有意无意地描绘得像个父亲,祈祷的语言往往像孩童对父亲的求诉。
在这一虚构的伟大关怀之下,人类建立了面对灾难与巨大痛苦的信心与勇气。 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则是一个冷酷的断定———它令我们注视一位美丽女孩时,会忽然想到老年妇人松弛而满是皱褶的肌肤和垂荡如破口袋的乳房。
然而,这确实是一个智慧的断定。就老子的本意,虽不是激励人们有所作为,由此作引申的思考,却令我们面对事实生活,自己背负起自己的灾难与痛苦。
在这样的处境下,人并不一定会失去信心和勇气,相反可能变得更为坚毅有力。《黑夜》的作者在抛弃上帝以后,以他的劫后之身,长期而坚定不移地为世界和平、为维护人权而奋斗,获得了全世界的钦佩。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赞扬他“是人类的使徒,他传递给人类的信息是和平与人的尊严。
他坚信,世界上正在与邪恶作斗争的力量终将胜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个人的生命终将归于虚无,如祭祀后的刍狗,生的意义却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即使人类无法从上帝那里获得仁爱与公正,人类还是要为自己选择合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