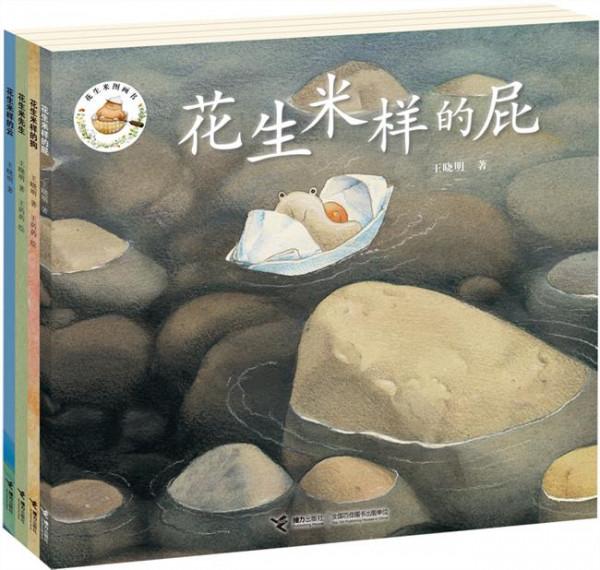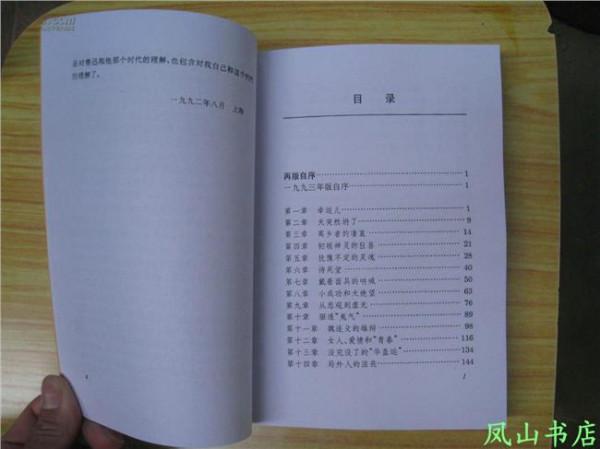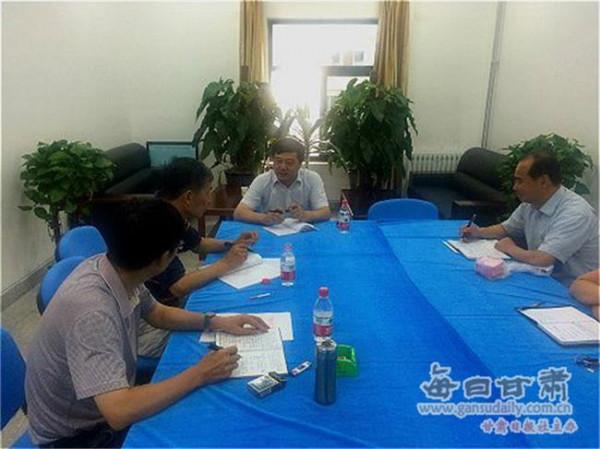马嘶岭血案陈应松 王晓明:读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
红水晶与红发卡 ——读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 王晓明 小说的头开得好: 我就要死了,脑壳瘪瘪的,像一个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红薯。头上现在我连摸也不敢摸,九财叔那一斧头下去我就这个样子了。当梨树坪的两个老倌子把我从河里拉起来时,说这是个人吗?这还是个人吗?可我还活着,我醒过来指着挑着担子往山上跑的九财叔说:“他、他要抢我的东西!
”我是指我们杀了七个人后抢来的财物,又给九财叔一个人抢走了。医生在给我撬起凹进去的颅骨时说:“撬过来了反正还是得崩。
”[1] 聪明的小说家早就知道,如今的读者大多神经粗糙、缺乏耐心,要让他们静下心来读自己的小说,小说的开头就一定得“好看”。什么最“好看”呢?自然是“血”和“性”,于是陈应松以“血案”标题,以“杀”字开篇,不但写“杀”的器具(“一斧头下去……”),还细描“杀”的后果(“凹进去的颅骨……”),不但九财叔杀我,我还和九财叔一起杀了七个人!
好家伙,的确够刺激的。但是,我说小说的头开得好,并非指这血光一片。
上面抄出的一百七十个字里,分明还嵌着整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先是两个农民合伙杀了七个人,然后两人中的年长者又砍了年轻的,年轻的被救了,年长的也逃不脱,于是双双入狱,被判死刑。
除了交待故事梗概,这一百七十个字还告诉了读者是谁——以及他怎样——在讲这个故事:是那个年轻的杀人者,养好了伤,在监狱里,用一副土气的语言(“……像一个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红薯”)在回忆。这似乎是犯了快餐文化时代写小说的大忌,你开头就把故事和结尾都说出来了,谁还会有兴趣读下去?看起来,陈应松依然对读者有一份信任,虽然是用血淋淋的标题吸引来的读者,他却相信,他们除了“好看”的情节,还要看别的东西:细节、人物、心理、情绪、甚至思想…… 他显然也相信,他的小说正可以提供这些内容。
就是这一份对人对己的信心,让我觉得好。 作家这自信并不虚妄。我跟着他的叙述往下读,越看越有意思。九财叔们杀了谁?是六个雇用他们当挑夫的勘探队员,他们是大学教授、工程师和研究生,为了帮助当地的经济发展,到马嘶岭来探金矿。
勘探队长祝教授是个工作狂,成天想着“把一个完整的矿山留给县里”,几个队员去洞里挖水晶,他大光其火,“说他们是搞破坏,当场就把小杜说哭了”。
小杜是祝队长的研究生,一个爱笑、爱唱歌的女孩子,却跟着勘探队餐风宿露,起早摸黑。另一个助手小谭,放着深圳月薪八千的工作不去,干这月薪两千的辛苦活儿,任劳任怨——一句话,都是好人。
九财叔和“我”呢?一个是几近赤贫的鳏夫,一个是身薄力弱、想起待产的妻子就愧疚不已的丈夫,他们一心指望干好挑夫的活:挑一天能得十块钱呢!“我”都累得屙血了,还坚持要挑下去——也都是本分人。
这两拨人彼此如何相待?挑夫们就不用说了,连日大雨困得勘探队粮尽油绝,九财叔为了博取祝队长的好印象,不惜主动冒险出山去买粮。勘探队员们也不错,虽然与挑夫分锅吃饭,但有了酒,会递一杯给挑夫;九财叔生了病,也会立刻送上药片;“我”唱了几首山歌,小杜立刻兴致勃勃地录下来,还向“我”讲解岩层的知识,又借给“我”一本《金矿地球物理找矿》,令“我”一时心潮澎湃,像小杜一样沉浸在地质勘探的豪情之中…… 可是,就是这样的两拨人之间,却不能善始善终,在一个冬雾弥漫的上午,九财叔挟裹着“我”,逐一残杀了所有的勘探队员,连同他们雇用的厨子老麻。
作家用了相当精细的笔法,一步一步地写出挑夫和勘探队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如何由最初的友善、羡艳、以貌取人和隔膜,逐渐生出误解、不信任、紧张、彼此提防、嫌厌、仇恨、绝望,最后拼死一搏。
虽然两次用了奇特的自然现象(夜间的白光和如密集枪声的巨响)来制造人物之间的误解,整个过程还是呈现得相当自然。
唯其自然,这个发生在荒僻的马嘶岭上的血案,就格外令人战栗:大家都是好人,都想好好相处,却硬是被差异和隔膜推入愈演愈烈的矛盾,最后全部丧命!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分站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只要按照自己的惯性行动,就一定会彼此冲突、不可收拾?这小说里的人事变化的逻辑,难道真是要昭示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倾斜到如此程度,不同阶层的人是越来越难以平和相处了?而一旦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小说,你立刻就会发现,祝队长和九财叔的故事包含了太多的社会和心理内容:城乡差别、阶层分化、文化隔膜…… 不单是人人皆知的那些方面,还有不少你平时不容易想到的事情:读到王博士对“我”唱的民歌的那一段评论:“吃饱了饭没事干,就想那公鸭撵年母鸭的事,听说这山里的女孩子是很开放的喔”,你一定会佩服作家对文化人的恶俗趣味的精准的把握;与王博士相比,“我”对水香和小杜的那一番从脸型到“胸奶”的暗自比较,明显是健康得多,似乎农民依然葆有本色的爱美的痴情;但一夜露宿之后,“我”对勘探队员的体力的由衷赞叹:“这些城里来的知识人,还真能吃苦呢……啥病都不生。
我却因受了风寒发起高烧来……”却让我刺心于农民的一无所有,竟然连体力都不如城里人!
正是这些散落在小说各处、好像荡开去了的闲笔,赋予整个叙述一种从容密实的品质,仿佛是用各种大小粗细的柴枝,耐心地堆起一座燃火架,小说最后的残杀场面,则如同扔上去一支火把,“轰”地一下,火苗直冲半天,再冷静的读者也禁不住要激动、甚至恐怖了。
如果说小说家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就是用一个精彩的故事,讲出人世间某种常人也许天天碰到、却从没有看明白的生活境况,我就觉得,陈应松正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故事。
说不定,这个故事的标题:“马嘶岭血案”,也会成为一个固定的词组,专被用来表述某种恶劣的不可化解的人际状况。这当然是个难看的词组,但是,碰上了难堪的时代,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别的更有意思的地方。
作家把故事安置在这么一处荒山野岭中,少不了要调用自然景物来烘托气氛。不知道陈应松是否出身山区,自小就熟悉马嘶岭式的山野景象,至少从小说来看,他很有一点描山绘水、调风遣雨的能力。小说开头不久,祝队长兴致勃勃地对众人指点马嘶岭:“这就是我们的勘探靶区了”,出现了小说的第一段风景描写:“巨大的河谷吞噬着天空,马嘶河和雾渡河在这儿汇合,流淌着的河水在秋天通体泛红,好像一头巨蟒吐出的信子”——上来就是一个不祥的暗示。
接下来,故事曲曲折折地往前走,马嘶岭上的植物和天气也配合着不断变化。“我”给小杜们唱了山歌、又吃了小杜的巧克力糖以后,“几天里,山岭却是极安静和明朗的。白云们在天空如影随形,有时候,一阵小凤吹过,会带来一种强烈的野果成熟的气味”;挑夫们和勘探队的“蜜月期”很快结束,讨厌的王博士指挥挑夫们加固营地,却不让他们进勘探队的帐篷,又搬出一架观察仪四处张望,“远处的森林浓如烟霞,依山势的爬高而呈现出陡峭的层次,树干白得耀眼,山壁黄得瘆人,天空云彩斑驳”——怎么看怎么别扭;矛盾终于明朗化,九财叔知道了祝队长们讨厌他,马嘶岭的风“凌厉凶猛了,落叶像波浪一样翻滚在山坡上,整个山岭笼罩在死灰色的烟幕中…… 大雨呼呼地来了,……狂乱的水流在巨石间粗野地激荡着,把河岸推向角落,山与山之间的联系湮没在一片啸声中,远远地制造着深沉的恐怖”;“我”仍抱着一线希望:矛盾会过去,“他们会把这一切忘了”,于是,“天亮了,雨住了,几只猕猴在树上发出了呼唤太阳的安静唳叫。
……整整一天都平安无事,阳光亮得人晕晕醉醉的,风也温暖柔和起来”;但事情无可挽回,九财叔陷入绝境,起了杀心,“晚上的风很大,依然是北风,河谷的冬汛好像在做最后的挣扎,在宽阔无边的河床上扑腾着,整个山岭到处是它们的腥味”;终于到了最后一天,“雾气很大,我们出去四面都没有路,到处烟雾腾腾,像着了山火一般”:就在这乖戾的雾景的熏陶下,九财叔挥起了开山斧…… 这么一路说下来,你一定觉得,像这样处理马嘶岭上的自然景物,还唯恐读者不明白,不断地加上“深沉的恐怖”、“最后的挣扎”之类耳提面命式的解说,未免有一点幼稚。
但是,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并不全都如此。
当小杜对“我”讲解马嘶河谷中冰川运动的痕迹的时候: 她轻描淡写地给我说着这些,我却觉得她的话撼人心魄。在那个晴朗无风的傍晚,无数玄燕和蝙蝠滑翔的河谷上空,我听到了冰川轰隆隆运动的声响,而当时的山谷是寂静的,旷古的寂静,这女娃子的话让我仿佛眼际滚过了那个壮观的七八十万年前的场景。
最初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中真是一动,好像在一条逼仄的甬道中突然出现一个缺口,大片开阔的景致涌到眼前。那由杀字连篇的开头、通体泛红的河水之类描写聚成的阴郁、紧张的气氛,一下子从我头顶散开了,一抹苍茫幽远的气息冉冉升起。
一面细描眼前的河谷的寂静,一面渲染“我”所感觉的昔日冰川的巨大声响,作家就以这静与动、今与古、物与我的强烈反差,突击式地抓住了读者,令你根本无心去考究:一个如“我”这般的挑夫,怎会有这样书生气十足的感喟?而一旦被如此抓住,你也就不知不觉地出了马嘶岭。
这就和我前面列出的那些风景描写完全不同了,非但不是亦步亦趋地给故事帮腔,反倒像是有意作对,前面走得好好的,它忽然插进来,引读者偏离了主线。
九财叔们杀完了人、逃下马嘶岭的时候,又一次出现了这样作对式的风景描写,也是在“我”眼见的景致中夹进“我”的感受,而且也再次用上了“壮观”这个词: 西坠的夕阳突然间挂在万山空岭的天边,苍山滚滚,晚霞滔滔,好像在洗浴那一轮夕阳!
我回过头,马嘶岭上,那几个或蜷或卧的人,都在夕阳里透明无比,像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红水晶,静静地搁在那儿,神奇瑰丽得让人不敢相信!
我被这壮观的景象惊呆了…… 这是偏得更厉害了。如此残忍、野蛮的凶杀场面,居然被渲染得好似一幅油画,刚才还吓得浑身哆嗦、瘫坐在地,胸口更被小谭刺了一刀的“我”,怎么会一下子生出这样超然的“审美”心情?倘说小说写到这里,应该是推你更深地沉入对马嘶岭悲哀境况的体味,这一段“红水晶”的描写,却差不多是将你一下子吊上了半空。
可作家并不在意这些疑问,在小说结尾,他再次写到了“红水晶”: 天完全变成了红色。
我又想起那个让我惊讶的傍晚,……那些红水晶一样的透明无声的死者。我的意识突然觉得,结局只能是这样的,他们最后只能在那儿——在那个时刻,安安稳稳地躺在那里,永远地躺在那里。
“结局只能是这样”,这似乎是作家对整个故事的总结,阴郁而透彻,可是,“红水晶”的比喻却在旁边捣乱,不但与阴郁的语调明显冲突,而且涂改了整个总结的涵义:“只能”云云,是说那些人只能死呢,还是说只能如此地死——像一块透明的红水晶?或者,更复杂地说,是同时包含这两种涵义?可是,综观整篇作品,并没有多少描写是指向后一种涵义的,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大动作地挥舞这块“红水晶”? 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情,小说里的任何一段风景描写,都对应着一双特定的眼睛,和这眼睛背后的一副特定的头脑。
当陈应松将绝大部分风景描写都编入故事主线,充当情节发展的忠实助手的时候,这些风景对应的眼睛,显然都属于故事的讲述人。
同样,当读到“旷古的寂静”、“形状各异的红水晶”这样明显蹦出了故事主线的风景描写的时候,你也就可以断定,在那个意在揭示社会冲突的讲述人之外,还有别的眼睛和头脑。在大多数时候,这些眼睛都顺从地闭着,听任“我”以土气的口吻唠唠叨叨,但也有几次,它们突然张开了,并且不由分说,驱迫“我”详尽地说出它们的所见。
这所见与“我”的其他叙说是那么不同,认真的读者一定深为惊愕:究竟是谁在回忆? 不用说,这些不同的眼睛都是来自作家,它们的那种作对式的呈现,正暴露了陈应松创作时的心绪的芜杂。
他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写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揭示某种社会的真实。当马嘶岭上的悲惨世界在他心中和电脑屏幕上逐渐成形的时候,他的另一些并不与之配合的感受和印象,也同时被牵动了。
如果可以用其中的若干,来营造某种“超越”马嘶岭的象征符号,给小说的细密的白描式叙述,填上几抹抽象的油彩,岂不是更好吗?1980年代风靡中国的那一股鄙薄现实主义、崇尚“现代主义”式的象征意味、以晦涩、怪诞为新意的创作风气,早已经沁入了几代作家的心脾,即便是关注现实、擅长写实的作家,内心也常有营造抽象情境的冲动。
或许,那一双从鲜血淋漓中看到“红水晶”的奇异的眼睛,那由此铺开的相当突兀——有些也颇能动人——的油画式的风景,正是由此而来? 小说中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小杜佩戴了一对红发卡。
虽然以“我”的标准看,“小杜长得不漂亮,但不知怎么,夹上那两个红发卡在右前额的头发上后,就显得好洋气”。
在马嘶岭的九人世界里,小杜是唯一的女性,她额上的红发卡,自然成了女性之美的一个聚集点。不仅如此,这红发卡还以它“穿了洞的小树叶一样”的精致的样式,将女性之美和金钱联系起来,它引来的目光里,就不止有对女性的欲望,更有对财富的欲望。
九财叔试图捞回被祝队长罚扣的二十元工钱时,第一个下手偷的就是这红发卡;“我”熬不住要想家、想妻子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也正是“去县城给水香买一对那样的红发卡”,而且也要“夹在水香右额的头发上”。
在一个善用细节的小说家手里,再小的物件,也可以像连环鱼钩那样,将许多游向不同的鱼,唏哩哗啦都钩上来。“我”对女人的那份本真的爱恋,就是被这一对红发卡勾起来的。
九财叔的形象的完整呈现,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靠了它们。九财叔是小说的主人公,可在“我”的大部分回忆里,他都是以不讨人喜欢的面目出现的:自私、贪财、老相、独眼龙,让三个女儿辍学跟他受苦,“打着”她们小小年纪就上山去放羊…… 可是,他对红发卡的注意,却泄漏了内心残存的父爱,正是佩着红发卡的小杜,激起他的强烈冲动:“我给妮子筹几个学费……”杀人杀得神经错乱了,他也不忘记将两枚红发卡都掳入自己的箩筐。
而一旦曲曲折折地表现出了这一面,他那一钱如命的习性,甚至那为了钱财而杀人的凶恶之心,都变得含义暧昧起来。当然是讨厌的,是恶劣的,但同时,你是不是也有点理解、甚至同情他了呢?今日社会的一大坏处,就是用种种方法,将人民训练成头脑简单、稍微复杂一点的事情就看不懂、也没有兴趣去了解的低能儿。
文学,也就因此要特别针锋相对,发挥它的一个特长:生动地呈现人和人生的错综复杂,吸引读者去体会、想象和理解“丰富”和“复杂”。
九财叔因了红发卡而显露出来的内心的另一面,不但在一般所谓善恶相杂的意义上,大大丰富了他的“性格”的内涵,更可能是向读者打开了一片视野,使我们对今日世界的“罪恶”或“邪恶”的理解,不再如时论教导的那样狭隘。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也和红发卡有关。九财叔杀完了人,将小杜头上的另一枚红发卡掳入箩筐之后,“我”忽然看到: 九财叔正在拉小杜红裤子前的拉链。 ……“叔,别这样!”我死死地拽着,我一掌就把九财叔推出了老远。
九财叔在地上爬着,支棱起脑壳不解地望了我一眼,他手上拿着许多东西,估计洗劫得差不多了。他恶毒地骂了我一句,就说:“快!快!”他挑上了箩筐就跑。 作家特意点出小杜的裤子的颜色,令人很自然想起红发卡。
在前面的叙述中,这红裤子正是和红发卡一起出现的,它们共同引出了“我”对女人肉体的遐想。“我”会如此,九财叔想必也差不多,只不过“我”的遐想有水香可以着落,九财叔却丧妻多年,只有在理智崩溃的情况下,才会以这样一种类乎发昏的方式,发泄久被压抑的冲动。
这冲动又是那样薄弱,仿佛梦游一般,一旦被“我”的那一掌推醒,就即刻消散了。九财叔先是像被唤醒一样地发懵:“不解地望了我一眼”,接着意识到冲动受阻:“恶毒地骂了我一句”,但也只是骂了“一句”,因为恐惧感迅速支配了他。
这个在故事里似乎越来越胆大的庄稼汉,终于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贫弱,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苦日子之后,从本能到理智,他其实都所剩无几了。
作家真是看透了九财叔们,在这篇小说里,他对他们的了解明显超过了对别人。陈应松并非那种漠视现实的作家,他在今天写这么一篇小说,显然是有某种为弱势者“呐喊”——借用鲁迅的话——的用心的。
但是,这一对红发卡却清楚地表明,他并无意为此减弱对九财叔们的透视之光。他不但要写出他们的可爱和可畏,也要写出他们的可厌和可怜。在我看来,主要正是他的这一种坚持,给《马嘶岭血案》力图表达的那些社会政治的寓意,夯实了一层小说艺术的基础。
这就使我忍不住还要多说几句。今日中国,种种严重倾斜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弱势群体遭受的损害,正强烈地激起各种反向的意识,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对“底层”的关切和认同之感也愈益分明。
中国文化人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普遍的萎靡不振,终于有了一个被打破的可能。但是,也就在同时,一种对于“底层”的幻想也开始膨胀:似乎“底层”并不是从精神到肉体都处于“赤贫”状况,它足以向我们提供想象新世界的充分依据,似乎一切希望都存在于弱势群体中间,“被剥夺”本身成了政治和伦理价值的天然证明——我这样的描述自然是非常粗暴的,但愿以后的事实能证明我说错了。
但最近一两年,我确实屡屡惊愕于闻见这样的言论和思想气氛,有时候甚至怀疑,这岂不是反而看轻了当今世界的严峻,也忘记了历史教训的巨大吗?倘只是怀着这样幼稚的认识去反抗错综复杂的现实,怎么可能成功呢? 一方面是远比过去更厉害的社会,一方面是至少和过去同样严重的糊涂、头脑简单和——不客气地说——愚昧,要戳破这两方面联手造成的“好世界”——再次借用鲁迅的话,文学是有它无可替代的力量的。
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就是一个例证,它不但以惊心动魄的故事,凸显出社会冲突的巨大的死结,更以九财叔这个轮廓分明的形象,表现了对于被压迫者的一种开阔、犀利、无所避忌、因此也就称得上是深切的眼光和关怀。
或许我太天真,我总觉得,这样的小说读多了,头脑的简单和幼稚是会减少的。 [1]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曹文轩等编:《2004年最佳小说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本文所引小说中的文字,均出自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