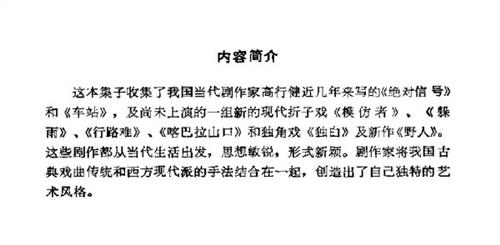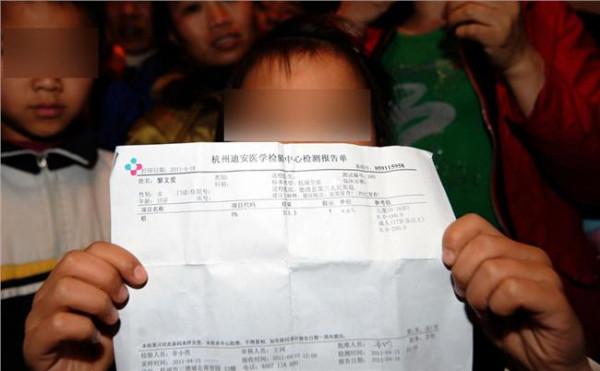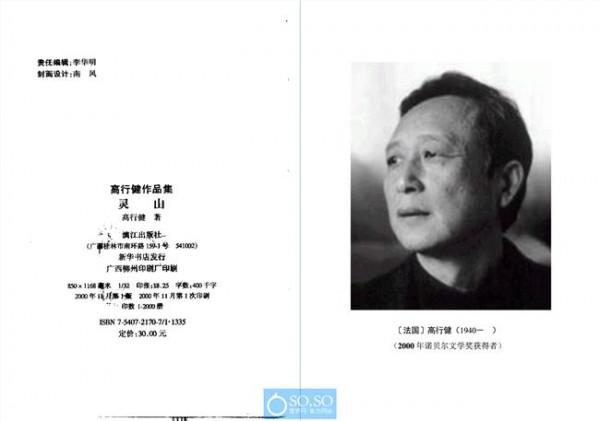高行健的作品 从高行健作品看戏剧的文学意义
内容摘要:高行健的"完全戏剧"观倡导戏剧以多元因素、尤其非语言的因素为主,主张"戏剧不是文学",应该回归到戏剧动作本身。这对于戏剧的文学意义的表现而言,究竟是丰富还是贫困?是以形式的丰富掩盖其意义的贫困,还是相反,在质朴的形式中寻求丰厚的意义表达?"完全戏剧"观的提出既是出于20世纪80 年代中国话剧突围的需要,也是高行健戏剧创新的艺术原点。
高行健的戏剧创作虽然并非只是体现"完全戏剧"的旨趣,然而却是在"完全戏剧"的宣示中实现了他对于文学意义的丰富与开掘,特别是他以"禅境剧"的创造而在当今世界剧坛上独树一帜。
关键词:高行健;完全戏剧;文学意义;禅境剧
华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是十分推崇文学的价值的。然而,他在完成《绝对信号》(1982)、《车站》(1983)、《野人》(1985)以及《彼岸》(1986)等一系列剧作的同时所提出的"完全戏剧"观却是"非文学"甚至"反文学"的。
他明确指出:"戏剧不是文学"[1],认为"戏剧是一种综合的表演艺术,歌、舞、哑剧、武术、面具、魔术、木偶、杂技都可以溶于一炉,而不只是单纯的说话的艺术。"[2]这是否意味着高行健戏剧创作完全否定文学的意义?而他所谓的"完全戏剧",是否完全消解了文学的价值?或者说,究竟怎样理解作为"综合的表演艺术"的戏剧的文学意义?高行健的"完全戏剧"观在表现形态的丰富中是否意味着文学意义的贫困?以及,高行健是如何在戏剧艺术的创造中践行他的文学使命的?诸如此类,对于理解高行健创作实践及其观念演变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结合高行健的戏剧创作实践,就"完全戏剧"观的提出、内涵及其意义做一简要的阐释。
一、话剧突围: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构
高行健"完全戏剧"观是在怎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与艺术态势之下提出来的呢?
我们知道,高行健步入剧坛始于1981年调入北京人艺担任专职编剧。而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都已经起步;此时的中国剧坛,也在经历了"文革"这个荒诞的年代之后,开始了艺术上的全面复苏。
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戏剧观"的讨论正在广泛展开。中国戏剧从观念到实践都面临深刻的嬗变。于是,以一个高调的"闯入者"的姿态涉足剧坛的高行健所面临的,一方面是五四以来的现代话剧传统,一方面则是1950年代以来北京人艺的演剧传统;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戏曲乃至传统文化的价值已越来越被人们所看重,一方面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戏剧流派纷纷涌入。
如果说,五四以来的现代话剧传统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一部分主要体现为话剧艺术的文学性的成就,那么,以北京人艺为代表的演剧传统则代表了走向成熟的话剧艺术的剧场性的最高成就。这两个方面原本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作为杰出剧作家的曹禺就曾经长期担任北京人艺的院长,曹禺、老舍、郭沫若的剧作对于成就北京人艺的演剧艺术功不可没。然而,实际上却由于戏剧艺术的特殊性而常常被人们分别开来加以谈论和对待。
更重要的,20世纪初兴起的中国现代话剧,自从20年代被洪深等命名为"话剧"且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一员以来,一方面出于适应"启蒙与救亡"[3]的急切的现实需要,表现出明显的急功近利的色彩(即所谓话剧的"战斗传统"),另一方面,也由于深受西方写实剧的影响从而一直行走在一条相对仄逼的写实的路途上,并逐渐成为一种只注重"说话"的剧。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话剧基本上被取消;而江青主导的"革命样板戏"更是形成了诸多的艺术教条;其中,"剧本,剧本,乃一剧之本"甚至流传至今;其实质就是企图以剧本文字去一劳永逸地规范舞台演出,以至于作为"样板"而一字不易[4]。
其后,被称为"新时期话剧"的复苏又是从"社会问题剧"开始,《于无声处》(宗福先,1977)、《丹心谱》(苏叔阳,1978)乃至《小井胡同》(李龙云,1981)、《天下第一楼》(何冀平,1988)等基本上都还是重复着五四以来的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关注"问题"并以"说话"见长的编剧与演剧的路数。
于是,"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话剧状况是:一方面是文字所体现的思想意义的日趋僵化,一方面是剧场演出形式的极度贫乏。而中国话剧的新变究竟路在何方?或者说,如何寻找中国话剧的突围之路?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的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
可以说,高行健的"完全戏剧"观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语境中应运而生的。
诚然,戏剧艺术应该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剧场性。而对于高行健来说,他更确信:"戏剧的生命在剧场里。"[5]而且,有趣的是,在面临着剧场性与文学性的两难选择的时候,作为剧作家的高行健宁愿选择了前者;并且高行健似乎是以对文学性的否定来显示其对于剧场性的强调。
从而,受其影响,差不多与之同时兴起的探索剧的热潮中难免使得戏剧的文学意义有意无意地被弱化甚至被取消,不仅有些所谓"探索剧"的剧本让人难以卒读,而且其文学意义的贫乏仿佛回归到游戏和杂耍。
然而,结合高行健1980年代以来的戏剧创作,他所倡导的"完全戏剧"观却完全可以有着另外一种解读。那就是:它不仅是对于既往文学意义的消解,而且更主要的还着眼于新的意义的重构;它不仅是寻求中国话剧突围的一种策略,而且也体现了高行健等一代中国剧人一个根本性的美学选择,即所谓"东张西望,开拓新路"。
为了到达他的戏剧的"彼岸",高行健伫立于东西方的交叉路口上,左顾右盼,既汲取东方戏剧特别是中国传统戏曲之所长,更能够自觉地以西方现代戏剧为样本,并根据自己的体验加以取舍,从而提出了迥异于东西方其他任何一种戏剧的"完全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