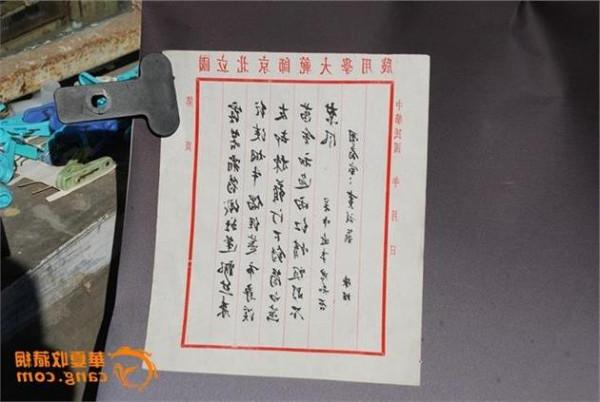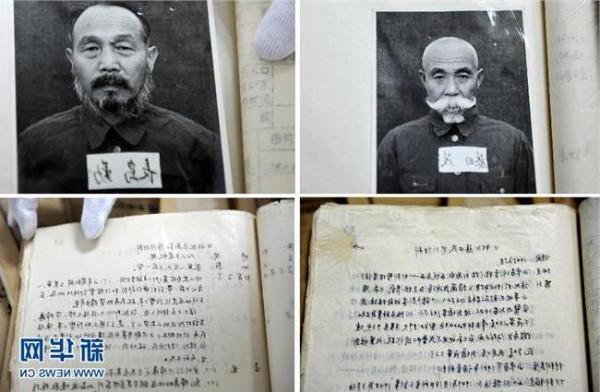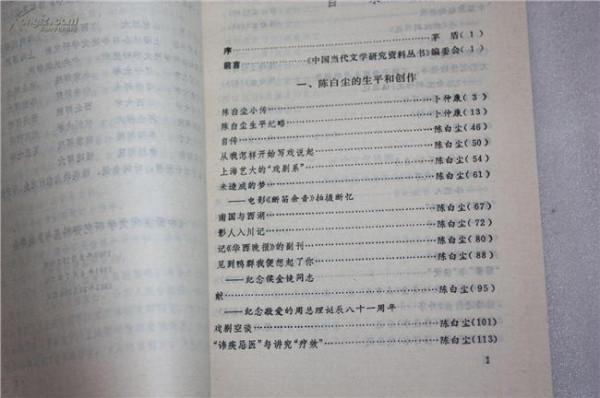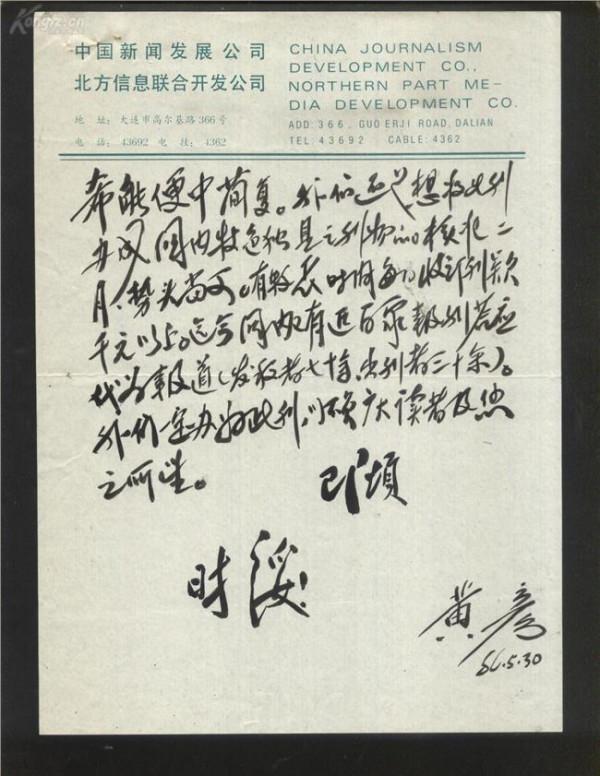作家陈应松 陈应松作家与作品互为照应(李云雷)
■《马嘶岭血案》使我真正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所在,作家是与他的作品一起进步和升华的
李云雷:你的《马嘶岭血案》在2004年引起了广泛影响,也可以说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但与其另一代表性作品、曹征路的《那儿》相比,你这篇小说的影响似乎仅限于文学界内,我觉得这与两篇作品在现实关怀、艺术表达以及思想追求上的差异有关。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使我荣幸地成为了“底层叙事”的作家。可是写这个小说时,我并没有听说过“底层文学”、“底层叙事”之类的说法,关于“底层”的讨论我也不太关注。我是糊里糊涂地上了这条“贼船”。
这个小说发表前叫《浴日》,里面有一句“苍山浴日”——是那些死者在夕阳下的悲壮景象。后来编辑老师说这名太雅,我就想干脆改个俗名算了,很直接。我的《狂犬事件》也是如此,原名《疯狗群》。事实证明,这两个小说改名都很成功,真是阴差阳错!
你看到小说原名就知道了,我偏重于艺术表达,我要让别人认为它们是地道的小说,我总是希望我的小说要能站住,多年后别人读还魅力四射。当年,有十五种年选本都选了《马嘶岭血案》,选刊也大都转载了,各种奖也得了,证明在艺术上站住了。
我的《马嘶岭血案》跟曹征路的《那儿》的确有差异,我除了表达某种现实忧虑外,还写了一种人的孤独,无法诉说和交流而产生的心理暗流,人在万念俱灰中的铤而走险。孤独一直是我小说探索的问题,《豹子最后的舞蹈》、《云彩擦过悬崖》也是如此。
李云雷:我认为《马嘶岭血案》的意义在于丰富了“底层文学”的表现力,提高了“底层文学”的艺术水准,这是很重要的,它让人们意识到“底层文学”不只是描写底层,而且在“艺术”上有远大的抱负。这篇小说将你的个人风格和社会关怀融合得恰到好处,不管读者是否认同底层文学的理念,首先都会承认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我想这是它在文学圈内影响更大的原因。
陈应松:关于“底层文学”的先锋性是你首先提出来的,你一定感受到了它的先锋姿态——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马嘶岭血案》是我的激愤之作,我当时只是想到要把它细细道来,让人感到真实可信——由一个没有任何犯罪前科和杀人动机的人,去杀死七个人,这需要在叙述时有极大的自制力,必须小心谨慎。
写这个小说之前,我去了海拔三千米的神农架韭菜垭,西风残照,一片安静。我想到了40年前血腥的一幕。40多年前,两个挑夫在这里杀了7个来神农架踏勘的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我在神农架挂职时听到这个旧案,决定写成小说。
我在荒凉的山顶上想山下的和山外的世界,只想大喝一声:人们,要警惕!这篇小说使我真正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所在,这是最大的收获。作家是与他的作品一起进步和升华的,他们互为照耀,互为温暖,互为激励和感动。
■怜悯,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总会有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平衡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责任
李云雷:现在不少论者都对“底层文学”的艺术性表示质疑,但你的作品似乎是个例外。我觉得有两个误区,一是批评者认为“底层文学”本身就不可能有好的作品;二是“底层文学”的倡导者更多强调题材或立场,而对作品的艺术性持宽容的态度。如何将现实关怀与美学结合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陈应松:去年底,我在“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上为“底层文学”进行了一点辩护。当时有一些批评家对“底层文学”甚至当代文学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好像不这样就不能证明他们的不凡见解。我老以为,批评家也要写点儿小说,否则批评是很难说服作家的。就像那次阎连科发言所说,每次参加这样的会,作家就是一小撮,就处在了被批判的位置。
我只想说:一,近年来最好的小说几乎全是写底层的;二,题材和立场必须是以小说的、艺术的形式出现的。确有一些比较差的小说,但总体上看“底层文学”是有相当艺术价值的。以刘震云、池莉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如此琐碎和啰嗦,也留下了一批好作品,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底层文学”失望呢?
根据你和其他人的研究高见,加上我的想法,我在南京的会议上也对“底层叙事”作了点概括:1、它可能是对真实写作的一种偏执实践,小说必须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哪怕是角落里的生活;2、它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现方法;3、它是对当下某种恶劣精神活动的抵抗、补充和矫正。
我们面临着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我认为,怜悯,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总会有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某一部分平衡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责任,并且努力弥合和修复我们社会的裂痕,唤醒我们的良知和同情心,难道这有什么错吗?
■好多作家的作品里都有一块“根据地”,因为滥了也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能把它写到什么程度
李云雷:“神农架”可以说是你创作上的根据地,它既是与社会对应的自然,也是与城市对应的乡村或底层,还可以说是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楚地”文化特色,或与现代相对应的一系列“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写作上的“根据地”?去神农架前后,你的写作方式有什么变化?
陈应松:首先,神农架是我的一个“喷发口”,这证明我有可爆发的东西,胸中有一些岩浆。如果说我的写作有什么变化的话,过去写虚了,现在写实了;而过去写实了,现在又写虚了。怎么讲?现在的写实,是基于神农架山川人物一切的真实,我写的任何细节,吃什么,用什么,什么植物,都是可以考证的真实。
另一种“实”就是对现实的关注不来虚的,直面人生,让一个人、一种生存现状站在你面前,真实得让你颤抖。而写“虚”了,是指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象征物,这里面的万物都可作为我的象征,没有象征不能成其为小说,没有象征的细节和语言我是不会用的,故事没有象征意味我是不会写的。
“根据地”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一块能彰显你才华和思想的地方,互为照耀。好多作家作品里都有这么一块地方,其实已经滥了,甲市、乙镇、A村、B河、某山、某坡等等,因而也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能把它写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你的造化,你的能力,你自己做人的深度。
神农架对我来说是一个虚拟的现实,是一种高度,是宗教一样的远方。今后不管我到哪儿都是到“神农架”,反正总会与它有点儿瓜葛,甚至不管当地人喜不喜欢我。当我把这块地方神化的时候,我将怀着虔敬,终身仰望。
■高尔基定义的“现实主义”让我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好像找到了组织
李云雷:现实主义是当前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我认为你的一些小说既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同时也具有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的特征,比如《豹子最后的舞蹈》有一种瑰丽的色彩,《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松鸦、路、守护人等都具有象征意味。请问你是如何看待这些的?
陈应松:谈“主义”的确是一个令作家头痛的问题。我过去从来不管什么主义,我只想把小说写得更有表现力。后来慢慢地有人说我是现实主义,其实你说的“底层文学”是真正的先锋文学是有说服力的。但说我是现实主义我也很得意,这就等于被主流文学接纳了。
有一天我读高尔基,终于看到了他的一段话:“对人类和人类的各种情况作真实的赤裸裸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这句话就让我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好像找到了组织。高尔基还说过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浪漫主义就是现实主义。”你去猜吧,为什么是。
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必须汲纳所有前辈的长处,让你的作品有着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浑然一体的魅力。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因素,与我十年写诗有关。我知道怎么让象征不别扭,浪漫不恶心。这可能纯粹是一种技巧问题,庆幸的是,我掌握了。
李云雷:在你的小说中,可以读出诗歌的影响,比如《星空下的火车》就像一首诗,比如黑夜中少年在火车上的意象,还有这样的语言:“那样的豹子死了,死绝了,独剩下我,一道衰败的微风,一缕夕照,长着牙齿和爪子的树叶,徒有其表的枯涩皮毛,绝望的影子,流浪的尊严,渐渐消失的秘密,比天空还深的伤感……”
陈应松:意象派诗歌是我的最爱。诗歌是我的灵魂。过去我把诗移植进小说十分生硬,经过二十年漫长的摸索,我的诗与小说的融合应当说自然多了。我在小说中加入诗意的因素,是希望小说更好看,排列出来有着诗的美感。我的语言系统肯定与许多小说家是不同的。你提到的《星空下的火车》、《豹子最后的舞蹈》,恰恰是我最得意的小说。我认为这是为历史写的。
■我要虚心听取批评家的意见,我的反批评只能证明我的不成熟和心胸狭隘
李云雷:关于《太平狗》和《母亲》,被广泛选载,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但北大的一些青年研究者批评这两部作品一是“堆积”了过多的苦难,二是对现实的理解与把握有些简单化,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的评论?
陈应松:福克纳说他从来不看评论,因为他是大作家,我有时还是看一点并且还想较真。不过慢慢我也就麻木了,不太在乎别人说什么了。但遭人误解毕竟是痛苦的。《太平狗》难道不是个好小说?在南通,张炜给我讲:应松,你的《太平狗》写得真好,我看了三遍。我真的很感动,还是有明白人的,这就是同行。而批评者与我们离得太远了,现在我真的知道这是不可强求的。
不过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说几句。一是:一个中篇小说就那么三四万字,不可能面面俱到,公允中庸、不偏不倚的人,不会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二是:城市是否丑陋,是否就应写成打工者的天堂,值得商榷。说我艺术处理过于简单,更是冤枉,我把一条狗写得这么细致、伟大,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中国当代的生存寓言,还简单?我这样的小说简单,那如今文坛就没什么复杂的好小说了。
李云雷:我部分同意北大青年研究者的看法,那就是这两部小说尤其是《太平狗》有些“二元对立”,它不如《马嘶岭血案》那样丰富复杂,也不如《豹子最后的舞蹈》等生气勃勃,但它的力量正来自于这样“单纯”的道德立场,这样的说法不知你能否接受?
陈应松:老话说一心不能顾两头,作家也有他的局限性。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景观就是“二元对立”,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好人忒好,坏人忒坏;乡村忒好,城市忒坏;穷人好,富人坏;群众好,干部坏;工人好,老板坏;进城就变坏……中国的戏曲更是如此:媳妇好,婆婆坏;孩子好,后娘坏;读书人愚讷,文盲人机巧……我受到了这种不良影响。
但我依然不认为我的道德观就是简单的。假如我把这个狗的故事写成一个长篇,肯定会完全不同,我当时的想法是:写疼为止。以后,这种小说不会在我的作品中出现了,我要虚心听取你们的意见。我的反批评只能证明我的不成熟和心胸狭隘,呵呵。不过,一个作家真到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程度,这个作家也完蛋了。
◆印象
三篇新作
陈应松最近发表的小说《野猫湖》、《夜深沉》和《一个人的遭遇》,向我们揭示了当前乡村中的新现实与新经验,写作风格迥然不同,艺术成就较高。我想,这首先得益于陈应松在家乡荆州一年的挂职生活,这让他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与理解当前社会的变化,并对各阶层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与心理有细致的把握。
《野猫湖》讲述的是一个有点怪诞的故事:乡村女子香儿在孤苦无依的状况下,得到了同村庄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于是在这两位中年女子之间,发展出了一种超越友谊的感情。小说并没有突出故事的传奇色彩,而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现实合理性与内在逻辑,于是这便不只是一个可以满足猎奇心理的“故事”,而成为了对现实生活及其秩序的一种反思与批判。
以往这类题材,通常放置于都市空间,多以性别认同的差异来突显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但《野猫湖》则截然不同。
《夜深沉》涉及到当前农村中出现的新问题:小说的主人公隗三户早年外出打工,在广东做生意并小有成就,在一场大病之后,他萌发了叶落归根的想法,他想要回承包地、批一块宅基地,为此费尽周折,最终也未能如愿……小说对隗三户无所归依的精神处境以及他为走出这一困境所做的努力与挣扎,做了精彩而细致的描述,而且,陈应松敏锐地捕捉到了当前农村土地关系的最新变化,并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值得认真思考。
《一个人的遭遇》与肖洛霍夫的名作同名,显示了陈应松的抱负。小说写的是主人公刁有福上访的历程,涉及到一个尖锐问题——信任。
在艺术上,这三篇小说各有特点,风格有较大的差异,不过在差异中也有相对的统一,那就是陈应松始终关注社会现实的变化及其对底层民众的影响,他的小说从不同方向指向这一核心问题。
陈应松的写作,努力的方向有两个:在深入生活中发现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关注底层民众的命运与心灵;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开拓新的可能性。
◆简介
陈应松:祖籍江西余干县,1956年生于湖北公安县。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出版有长篇小说《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等,小说集《太平狗》、《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豹子最后的舞蹈》等,随笔集《世纪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镇逝水录》,诗集《梦游的歌手》等30多部,有《陈应松文集》6卷。
小说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全国环境文学奖、湖北文学奖等,曾连续五年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十佳。现为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