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松猎艳图 走出艳俗——王庆松访谈录
胡:你能不能简单地讲一讲你的学画经历? 王:我出生在大庆,所以我的名字中间有一个庆字。我是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开始对画画有兴趣的,那是1982年。那时,我还在油田的子弟学校读高二,那时喜欢看文学、诗歌,尤其喜欢诗歌。
有一天,我在走路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张画――可能是大学生临摹的素描――画的是陕北的老农,就是那种扎着白手巾的那种。我就拣起来了,觉得他画的很好,回家以后,就拿纸罩在上面,描了一通,当时描的还挺象。
后来,我就找了一些杂志的封面上的明星头像,又描了一些。高中毕业以后,我听说有一个我原来认识的人上了沙市美校。我才发现,还有美校这样的地方,而且沙市就有!因为我没觉得他是画画的,没有感觉他是干这个的。
我就问他:你在哪儿学的画?把我也带去。他就告诉我:在沙市六中有个美术组,有老师教。我当时就带些平常画的东西就去了。那个老师特好,当时一看我的画,笑笑而已。因为肯定每天都有这样的人来要学习。我跟老师说我想学画画。
他说:行,你留下来吧。这么我才开始学素描,开始画立方体。当时还有一个笑话。有一个朋友,跟我差不多的,但他比我画得好,但是我比他来得早。他问我:他们画圆球怎么画那么圆啊?是不是用圆规了?我没有看见有人拿圆规画过。
因为我比他先进一个星期嘛!不用圆规,都是用手画的,这个功夫很深的!就这么学了一个月。 胡:你当时学的目的是什么? 王:就是爱好、喜欢。学了一个月以后,因为当时家里比较困难,大概那年9月份的时候我就招工上班了,做油田的钻井工人。
我在油田干了六、七年呢!干的是真正的王进喜干的那个行业。到元月份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沙市办了一个专门学画画的班,3个月一期的业余美校,是群艺馆跟文化馆合办的。
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了,我应该去学。进那个班才知道,这帮子人全都是冲着考学来的,导噬鲜歉隹记鞍唷D谴尾胖?酪???郏??参铩5??个月我收获特别大,从不会画就入门了,知道它的行规了,学习了画苹果,画罐子,还有各种布摺怎么画,完全是考学的那一套。
胡:当时你的身份还是一个工人? 王:对。请了3个月的假。学完之后,很多人去考试,我也跟着去考了,当时报的是黄冈师专。其实当时的专业就是背的套路,但一考还考得挺好,差的也是60多分,有的还七、八十分,专业过了,可以考文化课了。
有的人学两、三年还没有我考的分高。从那时一下子就有兴趣了。但是那年还是没考上。因为我是学理科的,根本就不知道历史、地理是怎么回事儿。
那年的文化课分数线好象是180,但我考了80分。结果就回去上班了。但是后来我每年来考,大概是考了5年,已经考成老油条了,中间停过一年。四川美院开始对外招生以后,因为我们家原来也在四川呆过,就通过关系,到了四川美院。
我88年就到重庆去了,先上了一个考前班,专门有个文化课补习班,边学专业边补习文化课。那年考试下来,文化课考了将近200分,但文化课的分数线好象是230,结果就花了2000块钱。
那时候这些钱还是挺多的。但是我还是想在正规学校,画一画那种长期作业,受一个头像画一个星期的那种训练,这对我是非常有作用的。但真的去上学以后,觉得也挺没劲的,还是那一套。 胡:你在那儿学什么? 王:油画大专班,91年毕业。
那个时候,在89年过后,绘画已经是很无聊的事了,很多人找不到路,就去搞装修,我就去搞了点小买卖,但是还是一直想画画。92年的时候我到北京看了富士美术馆的那个展览,特激动,虽然那不是最好的作品,但那毕竟是原作啊!
开幕的时候,特别多人,很多人还做笔记。那种气场一下子把我吸引了,我说:我一定要到北京来!第二年就跑到北京来了。 艳装时代 胡:你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来到北京的吗? 王:对。
我先到了山东,在我哥开的餐馆里干了3个月,他给了我1200块钱。我拿着这个钱就到北京来了,本以为坚持半年没问题,但是3个月以后就没钱了。那时我和另外一个先来的同学一起合租了一个房子。因为他姐姐在国际关系学院,就在圆明园附近,就住他姐姐的学校后面――哨子营。
那时他已经熟悉圆明园了,知道圆明园有个画家村。 胡:你当时去看过圆明园的画吗? 王:看过,但我不太喜欢,觉得挺乱的。我去过方力钧的画室,但是当时他不在,我也不知道方力钧这个人。
因为我知道刘小东,我一看,觉得他肯定比刘小东厉害。其实那时他刚从威尼斯回来。 胡:但是你对他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事一概都不知道? 王:不知道,也不知道有威尼斯双年展,对这种国际的展览完全是陌生的。
当时还看了伊灵、何勇的画。那时候,圆明园很多人画抽象画,画得很差的,还跟几个人也在一起吃过一次饭。对那种状态,我是真的不喜欢。他们说让我搬进去,我说不搬。住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我都在画画,画一些人在搏斗,在角斗,摔打。这是我那时的感觉,刚到北京来的那种压力很大,觉得很艰难,那些画名字叫竞争系列,画的人通红通红的,象血肉模糊的感觉。 胡:你实际来北京生活以后,与你第一次来北京时感受到的北京有什么不同吗? 王:生活太艰苦。
当时觉得圆明园村里一帮很穷的人,那么穷,还拼命在搞艺术!这种感觉还是挺打动我的,但这种生活方式确实很难。 胡:你画画这种方式坚持到什么时候? 王:到96年。
大概94、9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所谓艳俗的东西,用油画画的,画到95年圆明园撤了以后就停止了。那时圆明园一撤,其实对我的压力非常大,那时我觉得对我的文化伤害是次要的,完全是一种人身伤害,没有安全感。
胡:你直接面对了一个最为繁杂的世界。 王:因为那年我搬了五次家。赶来赶去,所以我一下子就扭转过来,转回最早的竞争的感觉,我就画了用塑料布裹起来的,缠绕的人,人在挣扎,想从里面出来的那种感觉。
画了一阵子,觉得那股劲过去了,这是简单的情绪发泄,很快就不画了,就一阵子,好象是解脱了。还是老在想流行文化、商业文化、包括西方的文化的影响。后来完全是丢掉了,变成了艳俗的那种。 胡: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流行文化这个概念有兴趣的呢? 王:94年。
胡:什么原因呢? 王:94年夏天的时候,当时还在圆明园。到94年的5月份之前,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我一笔也没有画,没法画,觉得没法画。当时碰到徐一晖,他问我:庆松,最近怎么样?我说:画不了,房租都交不了。
他说:你觉得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现在对民族文化在当代的状况感兴趣,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了?当时刚好老栗也提出民族的当代性的问题,其实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
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原来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问我:你认识不认识杨卫?我说:我不认识。他带我到他住那地。画行画的!特别明显。我说: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画的那些东西。杨卫当时画了一些象李山的那种花瓣似的画。
徐一晖说:他也有一些想法,想搞一些东西。他就带我过去,大家就开始一起聊天,包括刘铮,后来胡向东又搬进来,也在一起聊。大概有两、三个月,天天在一起聊。 胡:就聊流行文化? 王:对,越聊越激动,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非常激动。
觉得这个不得了。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全部分散了,各自做各自的作品去了。因为当时我哥在山东开塑料厂,我对塑料那种透明的感觉感兴趣。我想把塑料直接做成人。结果到了山东一看,我哥那塑料厂也倒闭了。
但没有办法,因为我既然过来了,就必须要做东西。那时也没有钱,我哥那里有现成的铁皮,我就拿铁皮做了一些被伤害的人。当然,这跟我原来的想法又不一样了。回来以后一直到那年的元旦,又很失落,觉得特失败。
只有画吧,就画艳俗的那些东西。当时画的就是白菜什么的,也画了一些婚纱。当然还是对民俗的东西有兴趣,都是画在金丝绒的布上的,类似于农民画。 胡:艳俗这个概念是你们这些人篡出来的? 王:没有提艳俗这个名。
胡:是老栗起的吗? 王:应该是他起的。当时我们说是民俗喜剧风格主义、庸俗艺术,但是没有提艳俗。到95年,圆明园快散的时候,老栗来看画。那时我跟老栗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也看过他的文章,可是从来没见过,没打过交道。
老栗95年来看的时候,我就在画屏风,画的是民俗的内容,但是形式是屏风的形式。老栗说:你们可以做个展览啊。当时其实很多人来看,都是没感觉。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栗,一个是老邹――邹跃进,也是95年来看的。
他当时好象对红粉文化挺有兴趣,想研究红粉文化。他也特别有兴趣,哎,这个东西挺好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挺有意思的。但是就是因为老栗说这个可以做展览,一下子把大家挑起来了。
这个可以做展览了?!变成一个潮流的感觉,我们没有想到,原来也没有想。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应该吸收前面玩世的有用的东西,同时也要避免他们那种政治性,那种意识形态很重的感觉。我们主要对流行文化这种综合性、文化性比较感兴趣。
胡:那你们这批人在年龄上是不是和玩世那批人…… 王:一样的。 胡:那既然年龄是一样的,是什么原因是你们的选择和他们的选择有这么大的差别? 王:他们89年的时候都在北京,对政治的事情也比较敏感。
而我们都是从外地到北京来的,感受更多的是生活的压力,这个对我们来说感受更深,对我们是一种伤害。其实在这个商业社会中,我们非常失落,最后我们就考虑商业社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是找这种感觉。
但是当时也吸收玩世这批人的优势,一种真实的感觉。当然到现在有编造故事的了,但当时还是有一种体验的感觉,面对社会的直接的一种感觉。 胡:有点象电视剧又编了续集的意思。 王: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但对于我们的做法,当时也有很多人在打击,圆明园里也不停地有人在攻击:这帮人,他妈的差得不得了。全是样式主义!包括批评家,全是一种嘲笑的态度。玩世刚起来,你们又想闹!因为他们当时觉得,至少应该是五年一个潮流。
胡:你们的第一次展览是在什么时候? 王:96年的三、四月份,在云峰画苑,名字叫《艳装生活》。原来这个展览打算跟徐一晖他们那个《大众文化展》要一起展的,但是后来分成了两个展览。其实,我觉得两个展览合成一个就更有意思了,影响也会更好。
当时老栗对我们艳装生活这部分有比较准确的表达:一个就是还有些不成熟,这是主要的问题;还一个就是有些雷同。 胡:当时你拿了几件作品? 王:拿了两件,一件是独幅的,一件是屏风。
很多人觉得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当然不是指作品,是指这个想法。 胡:有人从这个展览里获得比较实际的好处吗?比如钱? 王:没有,没有人能卖或者有人来经营你,也没有说因为这个展览就会得到另外一个展览。
反正是我没有。但是有人开始知道你的名字了,知道你的作品了。知道你是王庆松,而且是做艳俗的,大家都是说:艳俗艺术家怎么怎么,而不会说:你王庆松怎么怎么。 胡:好象就把你们扣在一个大的框架里面了。
王:这以后,大家在艳俗这个阴影下活了几年。反正差不多到99年,别人一直谈你是艳俗艺术家,而不谈你个人。 胡:就好象这是谁谁家的孩子似的。 王:对,就这个意思。也很烦恼,也卖不了。当时都画得很漂亮,都以为能卖,但是卖不了,非常痛苦。
图片生活 胡:这几年慢慢地有人开始注意你个人的声音了? 王:对。差不多从98年开始有人谈你的作品了,包括国外的人也开始谈。那年参加台北双年展,台北那个也是第一次作为国际性的展览,跟我们今年的上海双年展很相似,它当时是第四届,改为国际化了。
98年的那次主要是对亚洲开放,请了大陆的艺术家,和韩国、日本,主要是东北亚的。 胡:大陆的艺术家都有谁? 王:北京的有我跟顾德新,还有郑国谷、徐坦、林一林,还有海外的徐冰、蔡国强、陈箴。
从那个展览开始,很多人对我有新的认识,因为那时也是刚好我做图片展的。但那时我是把照片印在金丝绒布上的,我想延续我的金丝绒布的观念。当时展了5张作品,配了金色的框子,或者是粉红色的框子,很俗气的。
胡:这框子是你自己弄的吗? 王:是我要求给我的作品配这种框子,他们做的。后来因为这个金丝绒布印刷也非常麻烦,也褪色,后来也选择了很多材料,全不行,包括那种很亮的材料,也是废弃掉了,因为展出的时候会出现非常多的麻烦,比如起皮了,裂了等等。
而对我来说,重要的还是要展出,我首先要保证图片的意思能够看出来,因为只有照片可以保证这些,所以又回到照片了。
胡: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电脑的? 王:96年底。当时是一种简单的置换,象商场里的那种感觉,假的。当时就是对现实身份的虚假有感觉,在图像上倒来倒去。 胡:这个是你当时提供想法,然后让他们帮着去做的? 王:找他们的图库,我选的。
胡:是你自己拼的吗? 王:我不会拼,到现在我也不会拼,找别人帮忙。 胡:你只是提供想法,提供要求。 王:我也没有相机,只有一个傻瓜相机,所有的东西都是租的,开工了就租。但是最后我发现,电脑做图还是有很多麻烦,想等慢慢有钱了以后,拍现场的感觉。
以后的作品中可能电脑的痕迹可能会越来越少,我希望越来越少。 胡:你在国内用电脑合成的方法是最早的吗? 王:我觉得用直接拼贴的,我是最早的。
赵半狄也做,他是用电脑在图片上加字,对图像自身没有改变,到现在他也是一样的。当然,赵半狄差不多也是96年开始的。 胡:工具是近似的,但是追求是完全不同的。 王:也算是运气,刚好赶上了90年代中期中国图片的潮流。
但是我觉得我的好处是没有马上进入图片,跟做图片的艺术家发生关系。其实直到今年才发生关系。第一,我也不想跟图片发生关系,希望保持一定的距离。其次,别人也觉得我这个不是真的摄影。 胡:是用图片拼贴的方式,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摄影的效果。
我注意到你的作品中间也有一些有意识形态的意味? 王:比如《新兵与老兵》,我用的材料是97年的一本挂历,全是介绍女兵的,我主要是想嘲讽这种庄严性,假惺惺的感觉。
包括铁窗的那张,它的社会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铁窗是可乐,更多的表现的是流行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中国的这种社会中产生变异?我觉得它是肯定跟这个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包括跟国家对流行文化的态度,都有关系。
胡: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把以美国的快餐文化为代表的图像作为你作品的资源的? 王:差不多是97年的时候。为什么?我第一次去麦当劳,当时外地一个艺术家到北京,请我吃饭,我在那儿坐了四个小时,这对我刺激非常大。
这是快餐厅啊,为什么能吃四个小时,潜在的是对这种东西的崇拜,觉得这个环境非常优雅,非常好。后来,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东西,是一种西方文化的侵略。 胡:在不知不觉中让你改变对他们的看法。 王:我们现在去看,很多人在里面开party,过生日,放着那种很可笑的麦当劳音乐。
这种变异如果政府干涉,可以改,但是政府觉得这个东西也很好。而且所有的麦当劳,在西方没有很大的广告,在中国有巨大的广告,它那个大杆子,太有挑战性。
我98年做的几张图片,包括象十字架的《守望者》,都是针对这样一种问题。97年的时候,还是更多的对中国的、民间的东西感兴趣,到98年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丧失了很多,是因为有西方的那种虚假的现代性进入中国,干扰了你。
胡:你原来是借用中国通俗文化中的东西来做艺术,但是你那时突然发现这种东西被西方文化替换掉了。 王:它的压力非常强大。所以有时候到西方做展览,人家问我:你是不是反资本主义?我说:我也不反资本主义,我也不反社会主义,但我觉得这是我作为艺术家的一种态度。
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就说什么话。倒不是要反对谁?资本主义肯定有好的东西。 胡:别人在你的作品里看到对资本主义、对商业文化的嘲讽。
王:对。当时展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可口可乐驻中国总裁的夫人,开始看得特高兴:你看,用我们的图案!但是她看到这张《守望者》的十字架时,一下子傻了。她觉得这个很厉害。因为宗教在西方是很神圣的东西。
胡:她本来以为你用他们的商标是对他们的承认和宣传,但是后来她发现你的作品里有拿这种东西开涮的意思。 王:我希望我的作品有一种幽默的东西。 走出艳俗 胡:我发现你的作品所依据的资源是在不断地进行转换的,从原来的中国民俗到后来的流行文化,好象做一个作品就在转换一种资源。
同时,我注意到你最近的这些作品的资源则相对集中,基本都来自于中国传统精英文化中的绘画,我不知道这种转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从99年做千手观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传统有了兴趣。
我试图寻找传统文化中究竟改变了什么?后来我发现好象没有改变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跟旧上海是一样的。再反回来看古老的,象韩熙载这个时期,其实你发现也没有改变。
其实过去和现在没有改变,我们所说的现代性,其实是虚假的,骨子里的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但是他要强加一种现代性,小情趣,象驴屎一样,表面很光。我以后的作品可能就和历史越来越象,但是就不借用历史画面了,就是现在在演绎一种过去的东西。
我让你看到,你会觉得它是历史的,但是其实没有,找不出这张图像,伤感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 胡:你提到幽默和伤感,从你的整个的作品来看,你的作品中的幽默的成份可能要小于伤感的成份,这种悲剧的气氛是始终弥漫的,包括《老栗夜宴图》,是一个人失意的时候的反映。
我觉得你过去的作品都是以你自己为模特儿,而近来的作品中,你的面目不象过去那种正面的、特写的,大多也不是主角,身份也多是比较卑下的,是以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出现,观众不感觉你和别人有什么差别。
这是为什么? 王:刚开始别人问我:你做的那么难看,还把自己做得那么大?是因为没办法,我用你也不行,用他也不行,会出现很多麻烦。
原来的图也比较简单,就一个人,再拿别人的话,好象也不太合适。后来我很多还是考虑虚假的因素,生活的虚假,我参与不到这种虚假,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我是想把我越来越隐藏下去。后来我觉得,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小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实际上是很渺小的,就象《夜宴图》里,知识分子过去是这样,现在还这样。
在这里头,我尽量缩着,让别人阻挡了我,我只是在那儿看,参与不了,或者他快乐,或者他悲哀,我都没有办法,因为我只是个知识分子,没有办法去解决很多问题。
胡: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 王:非常尴尬,但是我不想用那种骂娘的方式,我希望观众自己在里面看到一点东西。 胡:你能不能以《老栗夜宴图》为例,讲一讲你拍摄的过程? 王:其实想拍实际这个图是在99年的时候。
在此之前,我曾经想拍一个《清明上河图》,因为我那个时候对中国的城市变化非常有兴趣,我准备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后来因为难度太大,放弃了。从那以后,我就慢慢进入了传统,主要也是去年拍东西比较多,实际上主要还是因为钱的问题,因为影棚也比较贵,一个小时600块钱。
我是拍了整整一天。当时出了点意外,当时摄影师的助手由于没有经验,把胶片全装反了,都要拍完了才发现,把我急坏了,这一下子,至少一万块钱没有了,只能赶快重拍。
结果花了两个小时,又全部重拍了,要不当时拍的效果会更好。 胡:你的模特儿是哪儿找的呢? 王:我找的一个主要的是在美院做模特儿,她再帮我找,如果我要一个个的找比较难。
我当时跟她讲:第一,不能太漂亮;第二,稍微胖一点,不限制年龄,年龄大小无所谓。给了她一个标准,这样她就会非常轻松地去找。因为我这不是完全色情的那种,也不是脱得特别多,而且化妆化得很浓,尽量让人看不出来她是谁,再穿上假衣服,戴上假头套。
这些衣服全是我买的,在批发市场和地摊上买的廉价的,好多衣服穿一次就烂掉了,炸线了。但你会在在国贸或者赛特里面看到几百块、上千块钱的衣服,样子跟这一模一样的。
非常贵。就是说它其实是很贵族的,但是我买的是假的。这主要是根据我的意思吧。拍出来还挺好。 胡:当时其它的道具是怎么弄的? 王:全部是租的。家具就是在做古家具的那儿租的。当时的屏风是三扇,最后拍出来的效果好象就一扇了。
如果是第一次的话,会更好。第一次时,我拍一个故事就换一个服装,后来的服装就没有换,所有的服装都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只有这样了。拍完以后,再用电脑处理,还好,基本上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而且我把颜色也调得更冷艳一些。
胡:更切近了夜宴的意思。 王:男的基本上都是画画的朋友。 胡:其它的是不是也基本都是参照这种方法来做的? 王:其它的就会有经验一些,我拍了这个以后,也考虑要拍一些独幅的,后边第二次拍的背景是空的,更干净一些。
《夜宴图》这张画太有意思了,我拿中国美术史上对这张画的评价,来看现在这张图,同样是适用的,什么对当时的社会的浮华生活的批判……,我看了以后:哎,整个是对我作品的评价嘛!
原来官方的语言就可以用。 胡:现在看来,如果你当时更有钱的话,还可以把这个场面做得更接近原画一些。 王: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再说,我觉得意思表达出来了就够了。
胡:当然,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往深推进,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张作品。 王:明年可能会多拍一些,我想把我积蓄了多年的想法在明年拍出来,大概会拍六、七张比较经典的。我想明年一月份,如果顺利的话,会拍两张,具体地到时候再看吧。
应该从视觉上会有所改变。 胡:这些图出来以后,你是不是还不利用这种方法去做? 王:还会做。 胡:你有没有一个比较主观的想法,比如你做图片已经做得不少了,你准备尝试另外一种方法? 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我两年以后做video,但是做video,我想我要考虑各方面的东西,包括技术和观念,都要考虑。
胡:我注意到有这样一种差异,就是在前卫这个圈子里面,你们这一些人的方式还是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虽然形式上也比较刺激,但你们的这种方式并不会对于参与这个艺术行为本身的人的身体有什么直接的伤害,不象以张洹为代表的那些人,好象是有自虐倾向,老拿自己真刀真枪的干,割个口子种棵草什么的。
你觉得造成这么大的差别的原因是什么?据我所知,你们也基本上都是朋友。 王:这是一个很大差别。当然这也有国际背景,90年代以后,西方艺术家,主要是以英国为主的,他们老做这种自虐性、伤害性的,有些人还因此非常成功,而且迄今为止,他们还是成功的。
这肯定是对中国艺术家有些影响,包括过去做女权的那些艺术家也开始这样做,等于他们两个合流了,全做这种自虐性的,非常暴力的,包括行为也是。当然,中国的艺术家倒也不一定是学他,但是肯定会受他们影响。
有一批艺术家做得挺好,但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更喜欢是一种中国方式,我觉得中国方式是一种内敛的,中庸的,象一个小针一样的。很大的板斧一劈,肯定会引起社会上人们的关注,但是也会造成伤害,很难让艺术家平步往前走。
我经常跟别人举的一个例子:假如这个人是仇人,中国人狠的就会拿针扎他1000针,让他死亡,每一针你都不会觉得疼,但是1000针以后你绝对死了;在西方,肯定很多人希望拿一个斧子就砍死了。我希望是用一种温和的方法,这样我会走得更长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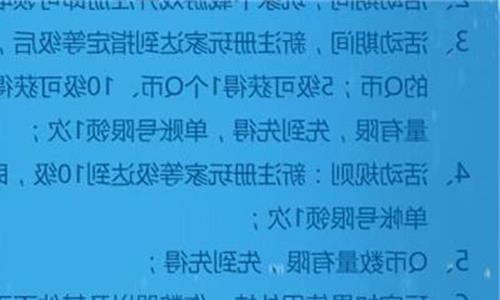


![从北京电影学院走出的九大美女明星[组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8/e3/8e3339d46c3309cb259eec7142ea99dd_thumb.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