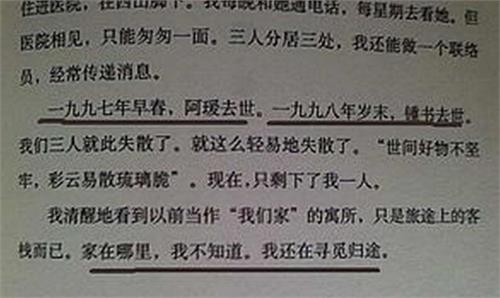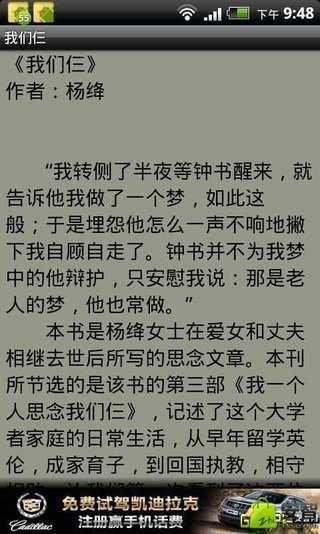【我们的钱瑗】钱钟书文集
核心内容: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100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杨绛先生即便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尤其是整理出版了钱锺书数十部遗著,其中,费时三年多整理完成的48册《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今年刚刚出版。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文/杨绛 节选自《我们仨》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
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
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
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
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文/张者●关于生死:死后寂莫,没人记得,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关于财产: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关于女人: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关于文化: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钱锺书先生去世两年了,杨绛先生近况如何?笔者冒昧拨通了杨绛先生的电话,说想采访……得到的答复不出预料,杨绛先生婉言谢绝。说:「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我说:「想以一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您,就算是关心您的读者之代表如何?」杨绛先生在电话中沉了会儿,末了说:「好吧!
你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这个老人聊聊天吧。」
留名干什么?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纹丝不乱,穿着乾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台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序,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两年了,在他的忌日您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不爱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
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您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您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您的身体很好,能活到100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这本书的第一版一万本销完了,2001年就是第二版了。
现在我就算是休息过来了,开始做我分内的事。我不想活得长,活着实在很累。」
不愿做名人
钱锺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锺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锺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
隐身于书斋,邀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见苏轼诗)」。面对杨绛先生,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您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都看看,看些要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虽然杨绛先生的这番话让我赧然,但我还是被她的坦率打动了。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您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
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盖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切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字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鹊起之时,钱锺书却默默无闻。
一次,他们一起去看《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锺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让钱锺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兼了。杨绛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里,哪里干过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满脸油烟十指黑的。
她急切地等待着钱锺书完成小说,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终于,钱锺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
我只拿60分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这么多角色杨绛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够好,女儿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很多人都觉得您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
」杨绛骄傲地说。我不由笑了,没想到90岁的她还反应这么快。「那么作为一个学者您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据悉,钱瑗去世时将近60岁,可是在父母面前,女儿还是女儿,永远也长不大。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
布拉斯》、《堂。吉河德》……在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联大。
作为妻子我应陪他一起去内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做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国外。我回国时,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问:「您的专业好像和教育无关吧,怎么做了校长了?」
「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
「从资料上看,您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您学习法律的。」
「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大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作,各个领域很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
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杨绛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可是,这样一个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文革」在社科院开始得比较晚。杨绛和钱锺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的批斗。在一次陪斗中杨绛被剃成了「阴阳头」,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大暑天戴上,闷热不堪,也不敢坐公共车,上班只好步行。当时在社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的,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都会喊打。
「文革」期间杨绛的主要任务是扫厕所,杨绛爱乾□,把厕所打扫得乾乾净净,连水箱的拉链都细致擦乾净,而且注意通风,没有臭气。这个女厕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一来,她就躲入女厕。这一段经过,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纪事》中,讲得很详细。
没有恐惧感
杨绛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剧变时没有离开大陆,为什么留下了呢?
「很奇怪,现代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个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绕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为什么不出国呢?」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
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当时外国聘请您们,您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您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好像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您已是90高龄的人了,您是怎么看待生与死的?」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
死,想想总是不会舒服。不过死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摘自《英才》2001.1
最痛苦与最留恋
「在这生中您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我问。
「我说不出来,有许多高兴的事,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最高兴。」杨绛先生语气淡淡的。
「痛苦当然有,不去数它吧。」
「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留恋的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已无所留念。」
中国文字是统一保证
「现在台湾又搞了一套拼音来给汉字注音,您认为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杨绛先生以史为鉴:「越南和中国以前用同一种文字。
越南成了法国殖民地之后,法国人首先灭了他们的文字,改为拼音。我们出国时在船上碰到一个越南人,他痛哭流涕地说本来我们同用一种文字,现在不同了。那个人姓吴,可是拼音一变就成了「鹅」了,我都不记得是什么声音了。我们中国的文字是统一全国的保证,因为文字的统一保存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
无论成吉思汗还是清王朝,他们统治中国之后,都被中国文化同化了,这可以看出我们文化的生命力。现在台湾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在搞分裂。汉字现在已有了繁体字和简体字之分了,如果注音方法再不一样,那就完了。我们要想统一祖国,统一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钱瑗和杨伟成 钱瑗[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https://pic.bilezu.com/upload/3/42/3425c64764ac784a1ff129a6953b1ca4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