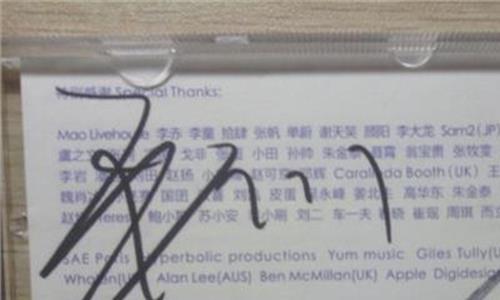新村乐队:关于成长的无畏与宿命
年少和梦想号召拥抱,成熟和成长催促分离新村乐队:关于成长的无畏与宿命初 识
2009年,夏,杭州旅行者酒吧。
开场时,我在洗手间里隐约听到音乐声,我知道,那首歌叫《Red House》,我没有想到,如此干净有力、具有光速般穿透力的声音,是从那个长发遮住半边脸,单薄,消瘦,黝黑的少年的声带里发出的。
长发,嘶吼,忿忿,这支乐队初生时自动套用了摇滚乐队的程式。青春年少的时候,总有那么几年,让人看起来有些装逼有些傻气。
那一年,新村乐队刚刚成立几个月,乐队的成员都是二十岁上下。
二十岁,已经不是孩子了。站在二十岁的端口上,一步一步往前方延伸,在二十岁的人生段落里,洒落音符,律动,渴望,梦想。
直到后来的某一刻我才发现,青春年少的确可以用挥霍的方式寻找意义,原来我没有错,只是很久以来,我以为我错了。
时光荏苒。2011年,秋,杭州酒球会。
“姑娘,你可以搭我们的车回嘉兴。”第二次在杭州看这支乐队的live,在一个朋友的引荐下,我得到乐队的允许搭车回家。
那个时候,关于新村乐队,我只认得出长发主唱周晨和戴眼镜的圆脸贝斯王鑫,很久以后我才想起,那晚的驾车司机是鼓手满经纬,一脸稚气未脱的小个子少年是主音吉他沈罕辰,笑起来一脸无辜样的高个小伙是键盘手张禄伽。
新村乐队的五个年轻人,经常与身边的人打成一片,却又显得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他们的言谈夹杂着一丝京范儿,音乐却没有北方的豪爽,距离魔都上海仅百公里之遥,却没有海派的小资,他们的着装打扮丝毫不出位,甩不掉的校园青涩味浸染了他们的音乐。
周晨和张禄佳在嘉兴月河街的酒吧里唱着别人的歌,不过如果遇到一位慕名而来,看起来文静可爱的女粉丝,他们也许会推荐一首小清新的DEMO《所有故事必须在酒醒后回忆》,或者自我陶醉地演那首被称为他们自己称为“大俗歌”的《八音盒》。
《八音盒》的歌词里,单车、落叶、夕阳、躁动、希望、深蓝、铅笔……这些词汇遗留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校园民谣的残羹。这是乐队原创歌曲里流传度最广的一首,所谓流传度广,恐怕也不会过千,无论是乐队豆瓣音乐人,还是新浪微博,粉丝数量一直徘徊在三位数,这些粉丝又以校园粉占据主流。
热情喧闹的篮球场,静寂整洁的图书馆,杂乱无章的宿舍,原本,校园内任何标志性空间与新村乐队没有太大关联,这支乐队是脱离校园之后才组建的,可它却与校园种种发生了丝丝缕缕的关联。校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诉说空间的词,它涵盖了青春,年少,是一个表达着初生、成长的概念词。
黄耀明曾经说过,我来大陆演出,你们来看舞台上的我,我也在看舞台下的你们。新村乐队同样享受与在台下随着音乐舞动的观众一起沉醉音乐的快感。2012年4月6日,杭州下沙高教园区,舞台不过一米高,与观众的距离几乎为零。深夜,他们会在园区附近的livehouse与一群同样热爱音乐的同龄人高歌,在寂静的校园里捡拾散落在地上的烟屁股,然后比比谁捡的烟屁股长,放入嘴里抽一抽,享受免费的快乐。
孩子气,多么难得的孩子气。
翌日,乐队和几位浙江工商大学的粉丝一起坐在花坛上等车,一位大二女生怯怯地对我说,我很喜欢他们的歌,但是我不敢跟他们说话,他们的气场很大。于是她坐在一旁,与他们保持两三米的距离。
孩子气与气场大,有时候只是一人双面。
王鑫是乐队主要词作者,这位曾经获得过新概念作文奖的白领青年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虽是地地道道的嘉兴人,却由于说话带着一股儿字音,经常被误以为来自于的北方。
“谁能告诉我,我该去哪里?”
“但是爱和少年啊,不相信梦会破灭啊,但是爱和自由啊,总有一天会消失。
什么时候从不相信梦想会破灭的少年成长为对于爱和自由的消失感到理所当然的大人?听新村乐队初期的那些歌,会触碰到我最脆弱的那根神经,害怕成长。然而,不知不觉中,岁月如歌,我们都在温水中渐渐成为那只青蛙。
小火车司机带着池塘里的猫
看见摩天轮的恋人们在嗑药
怀孕的孩子们骑着木马去寻找
发现池塘里的猫已经老早死掉
丢掉木马放弃城堡守着死去的猫
去吧去吧 吹着气球 没有烦恼
周晨是新村乐队的coreman。
集作曲,演奏,编曲等才能于一身的周晨,一文不名,体弱多病,家庭变故,自由乐观,具备了艺术家和偶像明星的特质。
“音乐意味着什么?”周晨自问自答,“对我来说,音乐就是生命。”
音乐就是生命,这样的表达更像一种习惯语,听起来似乎冠冕堂皇。
他解释:“音乐拯救了我,所以,音乐就是我的生命。”言语之下,我并不知道这个在组建新村乐队之前仅二十岁不到的少年到底经历过怎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复活,只是在之后的交谈中,我知道他曾经每天练琴8个小时,手指鲜血流淌依旧飞速运转,那种坚持濒临疯狂,以至于手指几乎要残废。
不过这些并这不能解释音乐如何拯救一个灵魂。可是有一句话可以解释:历经复杂,深处缭乱后的纯真,才是满溢着淡雅酒香的纯真。
周晨曾经这样形容过自己的嗓音:有点纯净,有点肮脏。
这两个形容词,在他自己最满意的初期作品《Paper Man》里可以比较清晰地感受到,而在其他的作品里,纯净一面,在天平的一端显得更加占上风。
在给这支乐队写新闻报道的时候,周晨叮嘱我:最好能提到每个人,拍到每一个,一个都不要少。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
然而,成长的脚步抑扬顿挫,节拍不一。
2012年上海草莓音乐节,乐队的形象和风格出现明显改变。周晨一头清爽的绿短发电子造型亮相,“大俗歌”的《八音盒》华丽转身,以四人阵容新编排的版本摆脱了校园稚气,平静优美的音符活了,编曲跨越旋律本身,张开口说话。上海现场酒吧微博评论这支乐队:有很大的进步,有不一样的感觉。与此同时,一些原本立场偏左的本地乐迷的对这支乐队的评价开始趋于中立。
事实上,身兼作曲、编曲及主唱数个角色的周晨一直主导着乐队风格的走向,经过三年的摸索与沉淀,周晨风格日渐成形,受Radiohead影响较深的他主动靠英伦风靠拢,他模糊流行和摇滚界限,崇尚草莓(音乐节)精神,尝试着流行、电子、车库等各种与“潮”字搭上边的因子,任何一段旋律到了他的手中,圈打出的框架,打磨的细节,流溢出强烈的周氏风格。
鼓手满经纬作曲的《两个灰姑娘》,在他的编配下,副歌部分点亮整首歌的基调,这只是小试牛刀,到了《taxibar》,英式时尚流行气质真正呼之欲出。
于是,又一个关于成长的诅咒被印证。年少和梦想号召拥抱,成熟和成长催促分离。
上海草莓音乐节前夕,在被问及“音乐风格和对音乐的态度”问题时,乐队词作者兼贝斯手王鑫的回答是:“其实音乐的风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音乐表达我们的人生态度,把我们对音乐的热爱融入生活中。”这种态度作为乐队的官方表达见诸于报。
而在私下里,周晨提起,他的梦想,是change the world,用音乐改变世界。他所指的改变世界,也许是引领一种流行音乐风潮,也许是用音乐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不过无论如何,很明显,王鑫与周晨对于音乐在生命中的角色定位,是截然不同的。
玩乐队,在香港叫作夹band,连TVB剧也一脚踹一踹摇滚乐,《天与地》煞有介事的通过三个摇滚中年探讨一个关于赎罪的主题,新裤子乐队的彭磊编剧导演的电影《乐队》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展映,这部电影在21世纪中国年轻人玩乐队的状态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乐与路》之间划上了明显的分隔符,西方世界《紫醉金迷》摇滚世界生命的疯狂和唯美,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可是新村乐队的故事不能免俗地戏剧化,核心成员的家庭变故,排练场地的尴尬流离,乐队成员工作与兴趣爱好的权衡,使这支乐队被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基于最初对于摇滚乐如拯救生命般的热爱,他们不能把做音乐演出和去KTV唱K消遣划等号。
“我有预感的,觉得将来会与众不同。”
“我为什么要妥协?”
对与周遭世界的抗争,周晨的姿态既是执着倔强的,又是自由随意的,他的音乐世界观在步入二十四岁年轮的那刻已经在心中扎根。
维小姐衣裳薄
201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