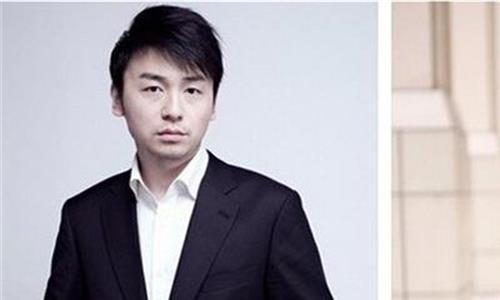雷平阳生活 雷平阳:尽最大的力量去发现生活之小
南方都市报:如何理解你所说的,“希望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亮的品质”?
雷平阳:这是我2003年参加《诗刊》青春诗会时写的一句话。意在强调“乡愁”对于我诗歌的重要性。说起来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们都不理解,我的确不喜欢远游,对许多人人视为天堂的地方我一直心怀恐惧,就算生活在昆明这么多年,我都一直渴望返回滇东北老家去。
在城里住着,许多像我一样来自乡下的人,把父亲母亲接到了城里,因此也忘掉了回故乡之路。我的父母还住在乡下,所以,天不下雨,我会着急,怕庄稼不能下种或禾苗干枯;假化肥假种子的消息见报,我会担心,担心我的父母兄妹也会受骗。
记得以前在一个访谈中我曾说过,对许多人来说,粮食和蔬菜,它们来自农贸市场,可对我来说,它们永远只来自一个地方,那就是土地。如果有一天,我也会认为,这些东西产于农贸市场,交上一点钱,就能带回家,那就有些类似于犯罪。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始终为我在遥远的乡下还有一片父母的土地而感到幸福。故乡,对一些人来说,真的是无法指认的,街道和门牌,变了又变,少年的痕迹,无处查找。我的故乡仍然那么具体,仍然可以让我的灵肉一次次地往返,尽管更多的时候,属于它的是秋风与明月,可我知足了。
正如佩索阿所言:“我知道,在南海中有一些岛屿,有宏伟的世界主义激情和……但我可以肯定,即便整个世界被我握在手中,我也会把它统统换成一张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
南方都市报:在《亲人》一诗里,你说:“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甚至生活在昆明,你也觉得像一个过客。对家乡偏执的爱和书写,会不会也限制了你的写作视野和思维?使你局限于一个“地方性诗人”的境地?
雷平阳:一生只写一个地方而成就斐然的作家,不胜枚举。我并不担心视野与思维的问题,更不害怕成为某种观念下的“地方性诗人”。我怕的是自己才情有限,完成不了“针尖上的蜂蜜”那样又锋利又甜蜜的写作梦想。我之所以一再地敦促自己,让自己尽最大的力量去发现生活之小,蚂蚁肚腹中的天空,母亲针尖上的蜂蜜,吃农药自杀的堂姐心头上最后的对爱情的梦想,乃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事物,除了没有子宫和乳房那么大,他们比什么都大,我再不是一个胸怀天下的没有心肝的少年,我知道在构成诗歌的众多材料中,我要什么,什么更有力量,什么更通灵。
所谓视野问题,并非说一个抱着地球仪写诗的家伙就一定掌握着人类的命运。所谓宽阔,基于体认,不基于面积。至于“地方性诗人”之说,我想,人们是太关注我写的那些地名了,其实,那些地名,完全可以换成任何一个另外的地名的。正如这首《亲人》,我就不止一次听人在读它的时候,把所有地名换成了与他相关的地名。
南方都市报:有人把你写的村庄和刘亮程的村庄做比较,认为同样写村庄,你的描摹冷静客观,不喧哗,不作派,有着原生态的真实。你怎么看这种评价?
雷平阳: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村庄,观念上的或真相上的。我的村庄是我生活过的村庄,现在我与它存在着一定的空间上的距离,所以我想让它更逼真,让它最大限度地复原。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它没有白养我一场。再说,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面,真实的村庄太少了,视它们为乌托邦、世外桃源的文字太多了。
现实的村庄,以我母亲还住着的那个为例。我离家出走二十多年,它真的没什么变化,缺食少穿的人,很多。我童年时的玩伴,现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没体会到衣锦还乡的滋味,相反,有的带着梅毒和淋病回去,有的只换了一身廉价的行头回去,带给家人的是更多的苦难。特别是当教育的现实主义意义(毕业分工)瓦解之后,很多人家已不再举债供儿上学,文盲又开始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