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中国 曹聚仁对新中国的雾里看花
[摘要]他居然要胡适率团在1957年这一共和国非同小可的年份来北京。
“适之先生: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们抛给我的问题,其中在关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我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是这样: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我在北京、上海的书店,找到你所著的各种书,各种版本都有。
朋友们藏有你的著作,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海外那些神经过敏的传说是不值一笑的。先生是实验主义的,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以照样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
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做一较长期的考察。
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了吧!”
三联书店出版的曹聚仁《北行小语》(2002年7月版),书中曹在“北行”一共“三语”的“第一语”,即《小语》的序中,抄入了上面一封信,信中提到的胡适给张慰慈的旧信,那是当年胡适主编《独立评论》,一反时流对苏俄取“洪水猛兽”态度的疾视,胡称:“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即“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
本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
记得十月革命后,胡适也曾路经苏俄,对彼的“实验”也唱过“赞歌”。其实这只是他进化论和实验主义思想的表示,对苏俄“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他只是同意它有试验的权利,一如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有同样的正当”,他宣称:“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却并不表示他就认可苏俄所“实验”的主义,他只是不愿“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反对“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和“许多学者的武断”而已。
一旦胡适明白苏俄所“实验”的种种,他的态度就很明确了。至于曹先生后来又以胡适的旧信做文章,劝说胡适再行“实验主义”,即于新中国成立若干年后“组织”一个由海外“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等等的“北京考察团”,来做“长期的考察”,却已是想入非非的一厢情愿了。
那封信,胡适只批了一句:“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1957年3月16日日记)妄,乱也,荒诞不经也,是很鄙夷的字眼了。
曹聚仁之“妄”,是他这位早有“乌鸦文人”称号、标榜自由主义文人(这应该是与胡适取同调的才是)的报人,不止对胡适其人根本不了解,也是雾中看花眼迷离——他居然要胡适率团在1957年这一共和国非同小可的年份来北京!设若胡适果真来了,历史会发生什么故事?这真是太撩人的假设了。
三联书店以《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作为《北行小语》的副标题,其实这个“新闻记者”前面还应该加一个“海外”才是。正如此书封底编者所述:“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谣诼纷集”,此时曹先生多次北上,以他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知共”的立场,也即“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这就是收入此书中的文字了。
应该说,曹先生的文字当时在海外有澄清是非、廓清迷雾的作用的,由此他也受托于中国内地方面,比如“双百”制定之时,向胡适等海外学人传达信息,甚至向彼岸高层传达口信等,曹先生为民族大义是尽过力的。
今天读曹先生的旧作(自然彼时的新闻已成为“旧闻”),不免让人反思,何以新中国如日中天之势渐渐委顿了下来,曹先生这本书中的“北行三语”部分,就不能不成为此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
这里,或许是基于“信息不对称”也或许是曹先生自己雾中看花,很多地方他不免看走了眼,这就如同后来巴金在《随想录》中说:要真正认清楚比如什么是“文革”,就必需自己身历才是,海外的曹先生毕竟是走马观花和隔岸观花,即使是中国新闻界的斫轮老手、曾经沧海见过大世面的曹先生,有时候落笔,也就不能做到一字一句都如“形容美女的身材,该凸出的地方凸出,该凹进地方凹进”了。
如《我看中共的“八大”》,曹先生是“相信毛主席是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因为他承认一党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也说,在阶级斗争终了后,也可以容许两党的并存的”。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怀疑者和批判者,他们一般不轻信任何许诺,这一时期曹先生的一些文章,如《苏联气氛知多少》、《沈从文教授在北京》、《民主人士的处境》等,就没有察觉出已经有不和谐的音符了。
此后,曹先生写反右、说斯大林问题、谈人民公社、看干部“下放”和“拔白旗”等等,未免轻易定谳,或先入为主。如果将之与现在已经出版的许多纪实性书籍并读,就会觉得曹先生的“客观、中立、公正”其实是有问题的。
再如“阳谋”的反右,曹先生怎么样看?文集中收有他《谈右派》的一组文字。总之是说右派们不免存有“狗抓地毯”的蛮性孑遗,而“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于是“这一回,毛主席的演讲就像经过了心理学家使用了催眠术,把他们下意识中的境界显露出来了”。
不过,右派如章、罗诸氏,曹先生认为“他们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等而下之,如吴祖光,“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至于全国各大学学生,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信口胡言,乱说一阵的颇有其人”。
好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反右运动,在曹先生笔下真似乎如他所喜好的京戏一场而已了。
再说反右之后,右派劳教,曹先生以为是“和风细雨”,“到后来,所有右派分子所受到的处分都是极轻的”。他报道说:“如海外所关心的吴祖光、丁玲、黄苗子这些朋友,他们都在参加北大荒的垦殖工作,生活得很愉快,进步得很快”,又说吴祖光赴东北是“欣然就道”,且“并非装出来的”,因为曹先生“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而北大荒,曹先生竟说“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以说接近天堂了”,真可惜他没有读过戴煌先生的回忆。
曹先生没有经过吴祖光等人的“沧海”,所以他在有人问“经过了劳动,有什么好处”时,可以想当然地“笑道:至少可以把若干都市病如失眠、神经衰弱之类医好,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说的,‘他领略到饥时吃,渴时喝,困时睡,他在这个时期所体验到的精神上的恬静’”(《草木神仙》)。
设若有不知底细的小辈从曹先生的“旧闻”中领略右派的境遇,他们或许会有一种惬意的体会?一如自称“我没有去过干校”的胡乔木,他读了臧克家赠送的《忆向阳》诗集后,却“仍能受到劳动激情的感染”一样。
(《胡乔木书信集》)又如“人民公社”早已是历史的产物了,那么,它为什么退出了历史?今天的人们大概绝难想到:1959年曹先生眼里的“公社”,竟是“一到农村,鱼、肉、鸡蛋就充分供应了,一席午餐,六大盘菜,一大碗汤,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从深圳到哈尔滨》)。
曹先生还以“宋明理学家,一直提倡氏族共产制度,张公艺九世同居,传为佳话”、民国蒋百里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和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语录书为依据,以为“依今日发展的过程看,全国可能分为三万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二万人”,而且他还相信“公社”是“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且“中国可能比苏联还早一步进入共产社会”。
他看老舍反映北京落后四合院内的人们如何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戏《红大院》,认为那“事实的发展比老舍的笔还快一程,那更是海外论客所不能了解的了”,(《谈人民公社》)却也正如彼时的大诗人郭沫若随周扬下乡采风,回来后痛感已经不再是诗人独擅于“浪漫”了。
类似曹先生这样的报人、记者、学人,曾经拥有过独立性,有过许多不同于流俗的见解,但是在严峻的时代面前、在现实政治势力分裂为两造的情况下,中间的或说是“乌鸦”色彩的自由主义文人是两面不讨好的,因为他们被给定的是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于是在努力追求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应有的作用和贡献时,他们会往往在“信息不对称”或“爱与真”的张力下,丧失清明的判断,这样一来,他们的有些文字就不能作为“史家之绝唱”来看视了。
这是他们的宿命。














![容国团的女儿 [难忘的中国之声]容国团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https://pic.bilezu.com/upload/4/76/47678200ddffcbc0c5323c12e85e5a5b_thumb.jpg)


![高建国元氏 [名校联盟]河北省元氏一中高一历史《第一课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建设》课件](https://pic.bilezu.com/upload/7/3b/73bf19117d478251d530cebf98b6bc83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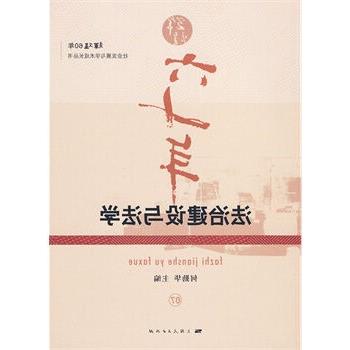
![>容国团和刘国梁 [难忘的中国之声]容国团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https://pic.bilezu.com/upload/7/33/733d78ace12386ea5bfcad76e08d4762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