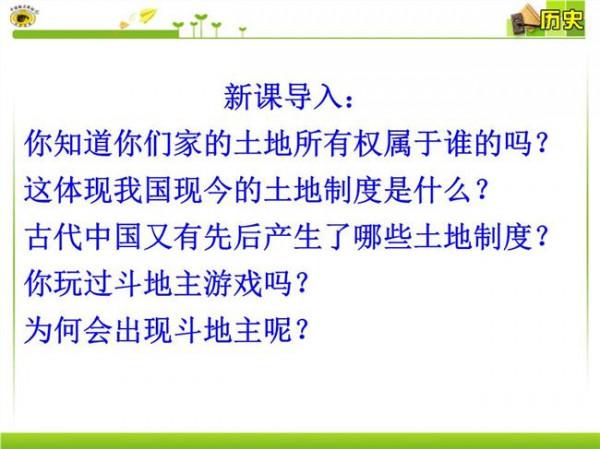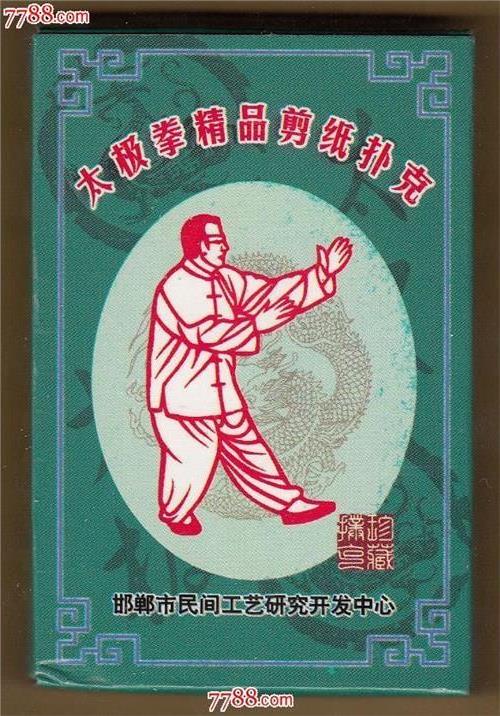张世明游牧 张世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类型学差异略论
在中国历史上,草原游牧民族往往迅速崛起,建立庞大的国家,如同狂风暴雨,势不可挡,但又迅速由盛转衰,仿佛昙花一现般归于沉寂。所谓“胡无百年之运”固属无稽,但游牧民族骤兴骤亡现象确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置身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学者回顾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亦觉不易,对游牧社会缺乏感性认知,在理解上更隔膜一重。
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不仅在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方面具有明显差别,而且在土地所有权等法律制度方面也大相径庭。由于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曾长期对垒和融合,缺乏对其特色以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差异的深刻了解,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也很难准确全面。
基于此,笔者希望践履多年前提出的“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主张,就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类型学差异略论一二。
发展与周期
与农作物产量以算数级数增长方式不同,人口、畜群的繁殖特点和规律中惯性力量往往很大。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其实是诗化的语言。农业生产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今年播种30斤种子,收获700斤粮食,明年播种30斤种子,可能收获800斤粮食,却不可能1000斤、1500斤这样增长。
但是,人口和动物的繁殖却不同,清代人口在康熙年间过亿后,在乾隆年间迅速增长到两亿多,到道光年间更是有了“四万万同胞”的概念。
在游牧社会里,如果赶上年景一直顺利,水草丰美,六畜呈几何级数繁衍,牧民人口由于生活资料的富足也往往表现为同步增长。但是,这种生命繁衍的特殊机制往往成为导致游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所在。一旦外延扩大导致游牧经济“过热”,数量迅速膨胀的牲畜过度啃食,使草场处于超负荷状态,“游牧社会经济危机”就会到来,被大自然的鞭子所惩罚的时间就会为期不远了。
在草场负荷过重、草原生态环境被破坏时,游牧部落摆脱危机的低成本的理性选择就是迁徙游移他方,而这也往往意味着激活彼此为争夺资源的战争,从而加重社会危机,草原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呈现周期性的震荡,游牧社会剧兴骤落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农耕社会的生产周期是以一年为单位的,春播、夏耘、秋收、冬藏,而游牧社会的生产周期其实不见得如此。牲畜往往需要几年才能长大,生产周期比种庄稼要长。而且,农业经济虽然在靠天吃饭的情况下极为脆弱,但是一年的自然灾害通常仅会影响当年的收成。
往往今年旱潦有灾,明年却是大好年景,甚至自我恢复机制所需时间用不到一年。例如,在发生洪涝灾害时,一方面洪峰破堤漫埝,冲村淹地,甚至“隔夜不找地界”,但另一方面,洪水过后,又因泥挟沙淤不粪而肥,地肥土润,其收必倍,谚云:“一麦抵三秋”、“一麦保全年”。
在清代,陈宏谋、孙嘉淦和方观承等人曾说到永定河之洪水泛滥善肥禾稼,所淤处变瘠为沃,秋禾所失,夏禾倍偿,一年之内即可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
据张謇言,江苏运河一带的下河之地,本有以水为肥料之经验,如兴化县,地势最低,受灾亦最酷,“然千百年来,遇灾何止数十百次,而居民安忍其毒而不去者,甲年灾,乙年必大熟,得犹足以偿其失故也。”然而,游牧社会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蒙古人称为白灾(即雪灾)、黑灾(即冬季无雪而畜群在严寒中干渴的情况)降临之后,古老游牧生产方式的灾害承受能力如果一旦被突破,经济就会发生崩溃,几年甚至几十年都缓不过劲来。
从年复一年的生产过程而言,农民种植的粮食可以储存较长时间。隋代广通仓贮藏的粮食在考古发掘出来以后还历历可见当初的胜景。但是,在游牧社会中,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畜产品的储存难度较大,牧民难以实现长期的持续的财富积累,不会像农耕社会中出现累世积谷而富的情况。
土地与心态
游牧社会所面临的自然资源分布格局影响到其以移动规避经济风险的行为模式,这种游牧经济与其权威性资源的配置具有密切关系。迁徙使得牧民群体适应资源条件的允许程度或根据需要而分裂和重组,并伴随产生社会关系的变化。
对游牧社会人群来说,迁徙不只是为了使牲畜在各种季节皆能得到适宜的环境资源,更是人们逃避各种自然与人为“风险”(包括权力掌控与阶级剥削)以及利用更广大外在资源的手段。这种迁徙很可能影响到游牧人群的族群认同、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以及其社会道德与价值观。
在游牧社会中,牧民与牲畜相依为命,并形成特有的生命意识。由于资源匮乏且不具确定性,马背上的牧民不像农民那样把自己的人生和庄稼一道扎根在土地之中,出于生存的需要经常有跨越种种边界的行动,亦多半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跨界。
牧民在许多情况下可谓对于政治权威可以真正实现“用脚投票”之人。由于需要因应环境变化,一起迁移的人群时大时小,因此各层次的社会认同与人群亲缘关系也经常“移动”。此种“移动”表现在大小、聚散无常的部落形态上,表现在相当有限或多变的领袖威权上,也表现在人群之共祖血缘记忆的变易上。
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在所有权观念的演化与表现上相差甚远,游牧社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畜群而非土地。骑马民族的土地所有和领属观念较为薄弱,但并非意味着了无土地领属概念。其原因在于:首先作为资源的优良牧场的供给并非无限制、无止境的。
司马迁《史记》载匈奴各部“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杜佑《通典》则云突厥(狭义突厥)各部“虽迁徙无常,而各有地分”。与汉族农耕社会中小农土地私有观念根深蒂固不同,游牧民族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体领属观念甚为发达。
即便是在使用土地时,游牧民族也与农耕民族不同。游牧民族选择所考虑的重心不在于土质是否膏腴,而在于水草是否肥美,此即史书所谓“种类资给,惟籍水草”的涵义所在。游牧民族世代繁衍生息的辽阔草原也是其精神生活资源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深情讴歌、虔诚礼拜的经久不衰主题,是其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不同民族囿于自身的思维模式对于另类文化的价值取向往往很难认同。在蒙元贵族进入华北平原后,别迭等人主张“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茂盛,以为牧地,”这一主张虽然因为耶律楚材谏阻而未被采纳,但现实中时有夺民田以为牧地的现象,以致“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
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与这种游牧民族无法切身体会农耕民族视耕地为命根的心态一样,传统农耕民族的价值观中往往缺乏“草地”的概念,而仅有对“耕地”的关注,草地俨然就是荒地,不加以垦殖似乎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典籍与记因
游牧社会逐水草而栖息,空间运动性相当大。从类型学而言,恰恰由于其移动性,游牧社会的文献资料容易散佚,不利于传承。人类学家著作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游牧民族在离开一个地方之前,将一些不便于携带的文献保存于某些山洞内部,准备以后再回来寻找,但是,有时往往游牧他方后便一去不返,或者经过很长时间重回故地,连自己也找不到当初埋藏这些文献的地方。
当今一些地方发现的所谓“伏藏”部分就是由于这种情况所形成的。在历史上,汉族读书人的定居生活使得官府和私人有条件在数代人的时间内对于文化典籍进行搜罗保存,以至于精椠秘笈,庋藏宏富。
例如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储书1.3万种之多,是瞿氏五世赓续努力的结晶;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达0.4万种,22万卷,系杨氏四代人百余年潜心搜罗之荟萃。诚然,农业社会由于兵燹战乱等原因,也会出现文化典籍荡然无存的情况,但在总体上,生活的定居特性对于书写文字的知识积累是较为有利的。
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因出版《自私的基因》一书而声名鹊起。该书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记因”这一核心概念。道金斯所谓的“记因”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基因。道金斯认为,演化的驱动力既包括基因也包括记因。“记因”类似作为遗传因子的基因,作为文化的繁衍因子,经由复制、变异与选择的过程,可能被升华、合并或以其他方式修改,形成新的记因。
道金斯的这一学说旨在提供一种与以基因为基础的生物进化理论相似的文化进化假说框架。如果我们借用道金斯的概念,游牧社会的文化“记因”的复制、繁殖和变异正是受到了其移动性的严重制约。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贡献各有千秋。但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游牧文化的资料零散且匮乏,迄今为止能够查到的史料又多依赖农耕文化的反射记载而得以流传,而出身于农耕文化的记录者往往厚己薄人,对游牧文化的记述难免存在讹传谬见。
从人类总体历史来看,欧亚草原游牧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创造的奇迹昭然可见;从中国的大历史来看,游牧文化亦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堪称揭示中国幽邃历史的秘密之关键所在;从游牧社会内部本身来看,依据生物行为学、文化人类学的思路从确凿的经验事实出发,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结构逻辑和演变机理,颠覆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识”。


















![>白明宠物 白明[北京睦明唐古瓷标本博物馆馆长] 简历](https://pic.bilezu.com/upload/6/b6/6b6736348700bd7828142b041e1459f9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