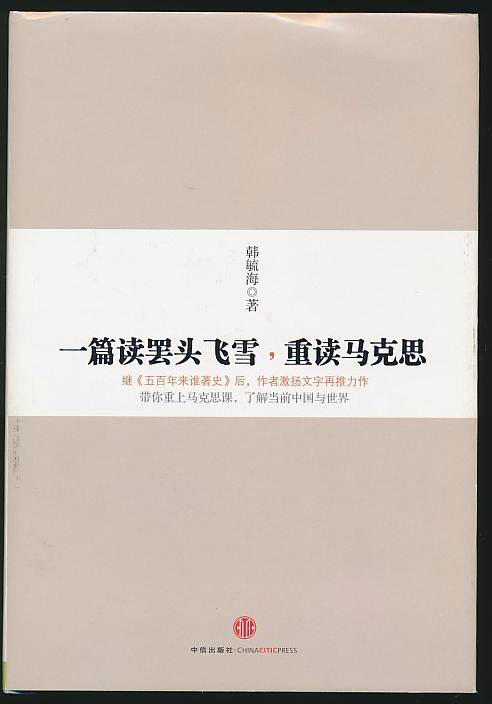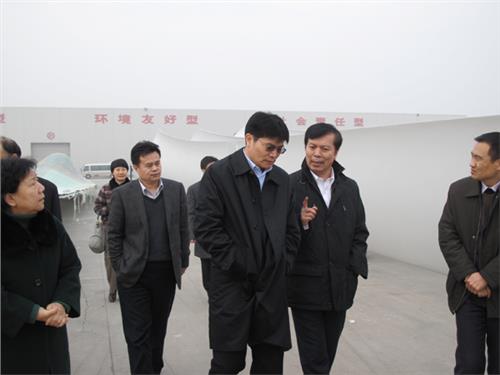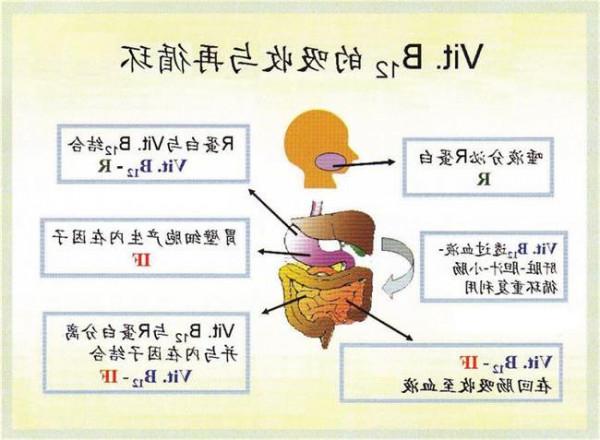韩毓海重读马克思 韩毓海:《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自序
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却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也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
“多难兴邦”这种话虽绝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马克思,确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记得北大中关园宿舍门外的一树梨花,岁岁都开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树下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自家门前便有这样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旧书店,有一日,我踱进去,只见店主一个人在躺椅上睡觉,阳光扑面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倒也正应了那句滥俗的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装,一共是50卷,便顺口问了价钱。
听到有人,开店的却连眼也懒得睁开,只是懒懒地应着:“一百”。
“什么!”——我大吃了一惊。
店主显然会错了意:“唔——,八十块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这就帮你捆好了,用自行车推你家去,反正放在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梦未醒的小店主,便乐陶陶地推着一车马克思的书,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持着,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如今想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间喜剧。
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常独自在这树下坐着望蓝天,怀里捧着一本黑皮精装的马克思著作,四周一片静谧,感觉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诗句:“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而现实逼迫着我,不得不结束了“开莫名其妙的会、见莫名其妙的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四处胡行野走、狼狈不堪的日子。时代的机缘,使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史诗狭路相逢。
四十岁之后方才知道:面对我自己所关注的课题——从长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论做基础,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进益的。
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禛(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乃至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
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
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金融制度相联系的国家科层官僚制度、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做“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便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
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
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依靠改革上层和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京都史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氏,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十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19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九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氏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百万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
“人皆有不忍之心”,而这就是“仁”,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如果把话说回来,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之改革所主攻的一个目标,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策”。
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依靠海外进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货币政策”一变而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国家的发展便总是会缺钱。
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够在16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彼此预付”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而这一切,都是由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为经济交换方式的革命准备了基础,在此之上,方才竖立起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马克思最懂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最懂得富强之道,而这一点,确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如马克思对于金融和资本的研究,是有经济学以来的各路经济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一样。不过,我们更需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不王道之富强”罢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照走不误,一切“后发国家”不仅不能实现“富强”,而且还会陷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丛林法则,其结果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更是“亡天下”。
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要把富强与王道统一起来,要克服富强与王道的之间的矛盾,仅凭“改革”、仅凭改造上层、发动精英增加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因为这需要动员全社会、需要发动人民群众——简而言之,这需要革命。
马克思极懂富强之理,马克思深谙金融和资本之道,这有《资本论》为证;但马克思更深明革命天演的法则,因而他赞成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这也有他一生的奔走呼号为证。
今天看来,无论求富强还是求王道,我们都离不开“西方圣人”马克思,因为仅靠我们祖宗的遗产,确实解决不了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2008年,我在纽约与廖子光老谈,廖老曾有言:晚清以来,中国举凡财政金融、军事、科技均落后于西方,不仅陷入国家民族的大劫难,而且陷入了文明的大劫难,要寻求富强之道,什么办法都尝试尽了,结论则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历史的翻盘。
直到湘潭毛润之先生出来,方才能够逐步集合中华文明的真谛,一举扭转了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因为毛先生很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近代中国除“人心”之外,再便无富强之“资本”。中国已经一穷二白,欲在如此山穷水尽的条件下求富强,只能依靠“行王道”,舍此再无它法,而毛先生“发财的资本”,靠的就是唤起四万万人的同心同德、空前团结一心,来打败了西方在军事、科技和财政金融方面的优势,他有两只手:一手是理学和心学的“大同”思想,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康有为、孙中山,毛润之先生是集大成者;一只手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这后一只手,能把“王道”与“富强”在现代条件下统一起来。
所以,毛先生缔造的新中国就不叫民族国家,而叫“人民国家”,他的战争便不叫“国家战争”而叫“人民战争”,他的科学教育不叫“精英教育”,而唤作“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教育,他的金融叫人民金融,而人民金融则是建立在人民的信任的基础上的,这是极为高明的设计。
毛先生把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个东方大国里做了实践,中国最终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他开辟了在“王道”基础上实现“富强”的新道路,他的一些实践、一些做法,固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自有其不成功的地方,但在大方向上,乃是完全正确的,而今天的中国学者的问题却是,对美国和西方霸权和霸道之实质既了解不深,对王道传统兴趣又不大、记忆几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长,习人之强,反难免两头皆失之虞,此乃是最可担忧之事。
无论如何,只有走“王道富强”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强”的东西,与中国“最好”的东西成功结合起来,中国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复活官二代、封建主义、买办资本、腐败、两极分化这些东西,正如历史上的中国,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国,若只求富强,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强。
廖老一直把毛泽东主席称为“毛润之先生”,因为廖氏一族,举凡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一半国民党元老,一半共产党元勋。廖老一生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作为纽约杰出的金融家,他始终关怀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2005年,廖老便提出中国以“货币互换”抑制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以及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待遇、面向内需、面向中西部谋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人,他的博大智慧令我如沐春风,至今记忆尤新。
关于“王道”与“富强”这个话题,我还记得上世纪末墨子刻(Tomas a Metzger)教授来北大讲学时,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我向他请教本杰明·史华茨(Benjamin I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他曾经这样说:我们西方实行的是“霸道”,你们中国坚持的则是“王道”,1840年我们打败了你们的“王道”,可是西方的“霸道”终究也不能长久,现在要看看你们中国,究竟有没有办法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了。
与其说将来世界上都要看中国,还不如说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相冲突这个难题。
墨子刻教授对清代制度,特别是《大清会典》有着精深研究,他更继承了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观——而更重要的是,用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他是少数“真正懂毛泽东思想的人”。
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果然能够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从而为人类发展开出一条新路吗?
2011年6月,在世界讲坛上,李稻葵教授曾经面对着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的西方政要这样坚定地说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会重复西方霸权主义的老路,因为我们要复兴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文明,这种文明的核心是“王道”——而这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富裕”。
中国的现代变革“始于170年前开始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国的失败造成了深重的文明灾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屈辱,这种屈辱的记忆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仍然在学习这些教训。那次屈辱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应,包括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应对这次屈辱的一个绝决的回应。”
“我的文明教会了我,不要去压迫别人,不要强加于人,而是要与人合作,我的文明教会了我,经济学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应是掠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
稻葵先生的话,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当时舌战群儒的形象:君子威而不猛。
“屡仆又屡兴,慷慨期致远。道逢同心人,万里互可勉”。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为了争取一个文明、进步和平等的新世界而前赴后继、挖山不止。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我们的去路,就没有什么大山是挖不平的。
或许,我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写完《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之后,我本想一鼓作气,把《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写完的,但是,随着写作和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认识到:如果不能抓住现代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如果不能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发生“大分流”背后的因缘,无论下多少功夫都是白费的,而要抓住这样的动力、追求这样的视野,那就必须掌握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方法。
我从今年九月初至今一直在生病,家人警告我说,倘若再这么捧着马克思的书不放,恐怕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此虽系笑谈,而我心自知,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别的东西吗?不做亏心事,何惧鬼叫门。何况我们的许多前人,例如写出了《封建论》的柳宗元,恰在我这个年龄就死掉了,而像马克思一样,他即使在放逐中,却毕竟也没有低下过自己的头。
本书得以顺利面世,实有赖于多方的全力帮助,今特申明三事:胡鞍钢教授命我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师生讲授此稿,由于鞍钢教授在讨论中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本书的观点更加具有了现实针对性。李玲教授慨然为序,其辞恳切,令我动容;作为前辈师长,他们的恩义于我,诚可谓是“动心于无情之地,施惠于难报之人,古烈尚难,况在今日”;而北京大学支持我这样一个中文系的教书先生为全校研究生开设“马克思著作精读”课,也凸显了北大学术自由的传统,故清华与北大——此应感谢者一;大名鼎鼎的中信出版社为出版此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此应感谢者二;我的研究生贾嘉、陈澹宁通过录音记录,反复斟酌,把我的讲稿整理出来,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此应感谢者三。
马克思于1883年病逝于伦敦,于今130年矣。而今天的我们,却正处于他所预言并深刻分析了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中,而这按照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尤生。”
希望这本小书,能为广大读者带来真正的思想与知识的乐趣。而那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