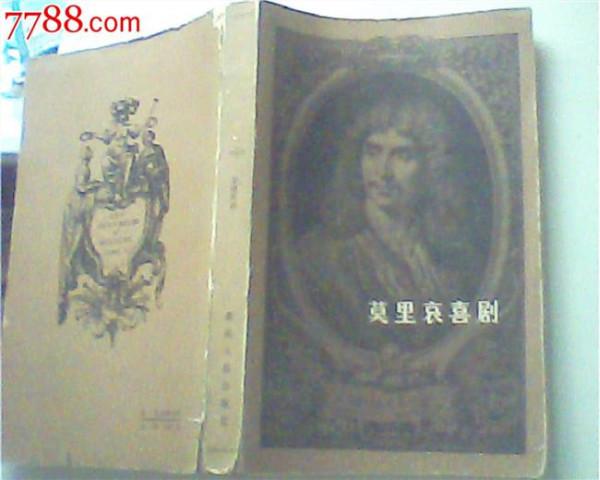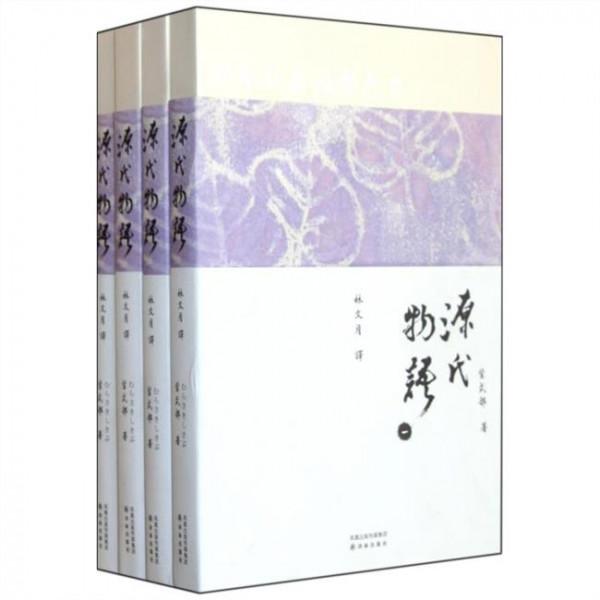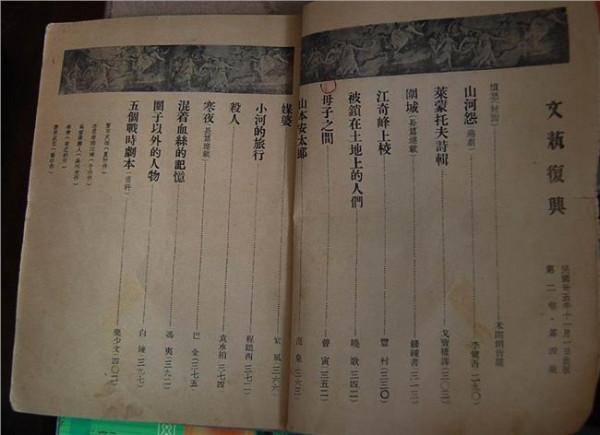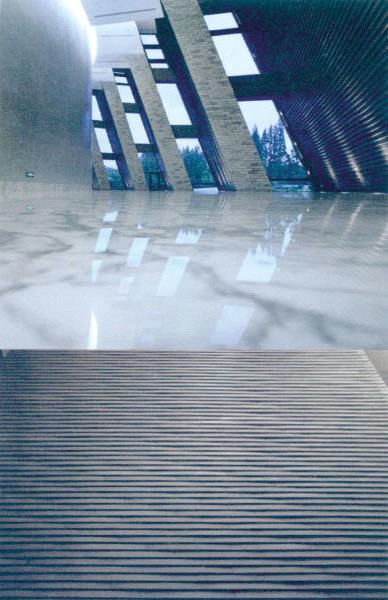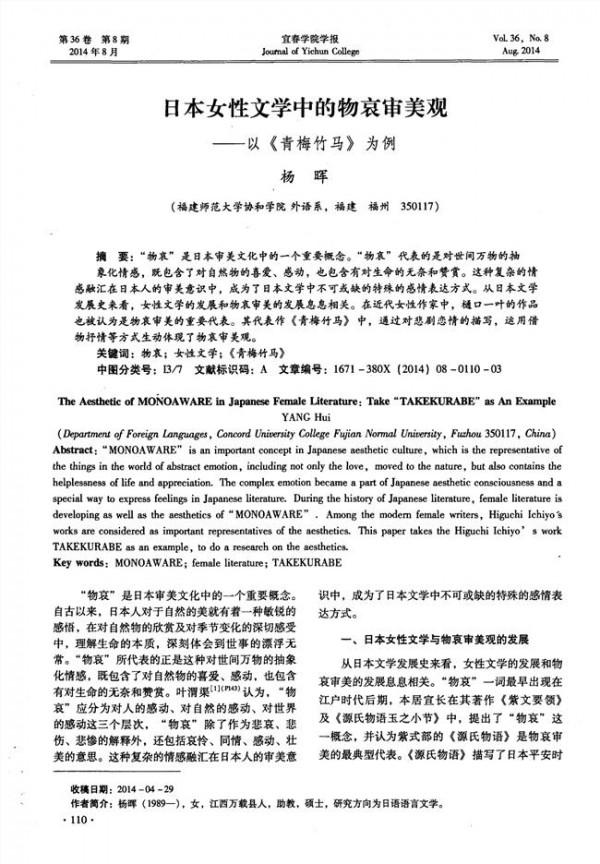李健吾莫里哀 论李健吾与莫里哀喜剧的精神联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莫里哀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戏剧家之一,而我国对莫里哀喜剧译介、研究最为用力的则当推李健吾。李健吾的喜剧创作也明显受到了莫里哀喜剧的影响,大体遵守“三一律”的创作原则、喜剧中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性因素、注重人物性格刻画和世态描写,是李健吾喜剧与莫里哀喜剧精神联系的三个主要方面:
关键词:李健吾;莫里哀;喜剧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 6101( 2013) - 03 - 0020 -8
一、李健吾:莫里哀的中国学生
在喜剧世界里,莫里哀无疑是一个最响亮的名字。巴尔扎克就曾认为,在各时代的喜剧作家中,莫里哀应坐“第一把交椅”[1:43]。在中国,1920 - 30年代的戏剧家对莫里哀已经很熟悉,焦菊隐当年曾说:“差不多在我们的意识中他已经成了喜剧的代表符号一样,一提起‘莫里哀’三字,即会想到‘喜剧’二字。
”[1:38]虽然法国人称莫里哀是“无法模仿的”,但他的喜剧一方面为各国戏剧家树起了学习的范本和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活跃在各国的戏剧舞台,引来众多的追随者,“法国的伏尔泰和博马舍,英国的德莱顿和谢立丹,德国的莱辛和歌德,意大利的哥尔多尼以及西班牙的莫拉丁,都是他的崇拜者和学生。”[2:160]
莫里哀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戏剧家之一,1920 - 30年代,他的主要剧作都得以介绍,而后来对莫里哀喜剧译介、研究最为用力的则当推李健吾。
谈到莫里哀的影响,李健吾曾说:“他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欧洲,建立现实主义喜剧的写作和演出的传统,同时他的杰作也成为欧洲各国的喜剧作家衡量自己创作的尺度。而欧洲每一位喜剧作家,也只有竭尽智能,表现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国家,充满进步意义的时候,才被尊为本国的‘莫里哀’”[3:284],“在他以后的喜剧作家,不分国别,几乎没有一个不向他的作品学习的。
”[3:88]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李健吾就是中国的莫里哀,但他无疑是莫里哀在中国最忠实的信徒和最优秀的学生。
李健吾很早就计划翻译莫里哀的喜剧,1940年代末译出8种,由开明书店出版;1950 - 60年代不仅发表了长篇论文《莫里哀的喜剧》和《试谈导演莫里哀的喜剧》,而且出版了《莫里哀喜剧六种》,并写有长篇序言;1980年代初又推出了《莫里哀喜剧》(共4册,收喜剧27种),发表了《莫里哀的喜剧艺术》等论文。
他还曾多次应邀在北京、上海、辽宁、甘肃等地讲授莫里哀喜剧,为在中国广泛传播喜剧的种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努力,不仅为人们全面了解莫里哀提供了可能,也反映出现当代中国文人的心理、价值取向。
李健吾是在创作了大量悲剧之后开始喜剧创作的。大致说来,1934年前,李健吾创作的剧本都是悲剧,这与他不幸的身世、苦难的童年和多病的学生时代等人生经历有关。1934年后,李健吾则以喜剧创作为主,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法国文学尤其是莫里哀对他的影响。
李健吾于1931年赴法留学,两年的留学生涯使他成为莫里哀的崇拜者,并在此后的戏剧生涯中,将大量精力倾注于莫里哀喜剧的翻译和研究。流溢着欢乐,闪烁着智慧,具有明丽、峭拔、辛辣的讽刺风格的莫里哀喜剧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健吾创作的喜剧共10种,其中5种写于1930 - 40年代,它们是:《这不过是青春》、《以身作则》、《新学究》、《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青春》。就个性、气质、审美情趣来说,李健吾是倾向于喜剧的;就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贡献和影响来看,他的喜剧更值得重视。他的喜剧理论研究、喜剧文学翻译和他的喜剧创作相得益彰。李健吾将作为一位具有深厚的戏剧文学素养并独具个性的世态喜剧大家而永载史册。
二、对“三一律”原则的遵守与突破
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李健吾对莫里哀译介的热衷反映了他们主客体间强烈的心灵吸引,同样,李健吾自身的早期戏剧创作也反映出二者契合的近亲心理机制”[4:63]。李健吾的喜剧大都遵守着“三一律”的创作原则,这是他与莫里哀喜剧精神联系的第一个方面。
《这不过是春天》、《以身作则》、《新学究》都是三幕剧,时间集中,《这不过是春天》为三天内,后二剧均是一天内;地点集中,三剧的地点分别为:北平、华北某县城内、某大学附近。
具体地说,《这不过是春天》的情节发生在北平警察厅厅长的公馆里,实际上,它的场景只有一个:厅长公馆里的内客室。《以身作则》的情节发生在徐家,第一幕发生在徐家大门外,第二、三幕发生在徐家的厅房。三剧的戏剧冲突也非常集中:革命者冯允平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从南方来到北平警察厅长的公馆,厅长夫人竭力要留住昔日的恋人以叙旧情,而警察厅长和他手下的密探正在奉命搜捕这位革命者。
剧作在情节高潮的边缘切入,冲突集中,行动单一,从而构成了《这不过是春天》引人人胜的剧情;《以身作则》里的徐守清拼命维护封建礼教和道学传统,剧作却让一位暂住当地的年轻营长和他的马弁想方设法打入徐家,并赢得了徐家仅有的两位女性(徐女玉贞和女佣张妈)的爱情,徐守清不仅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局,而且出尽洋相,那道学先生的形象也在人们的笑声中倒塌;《新学究》则以大学教授康如水对女性的狂热追求为情节贯穿线,结局是连他的恋人也认清了他性格的漂浮和思想的空虚,弃他而去。
李健吾的喜剧在结构上是符合“三一律”的。而我们知道,莫里哀作为17世纪古典主义喜剧的杰出代表,他的喜剧遵循的正是这一原则。李健吾特别推崇《达尔杜弗》的结构,认为它“仿佛水晶,透明而又坚定”[3:145]。
当然,莫里哀一方面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另一方面,他也绝不是一位墨守成规者。李健吾评价说:“莫里哀尽可能遵守三一律,但是在题旨本身需要另一种安排的时候,就象处理《堂-璜》一样,他决不勉强自己。
”又说:“他遵守三一律所下的功力,不在遵守本身,而在遵守的时候,还要气势自然。为了自然,他宁可破坏法则。”[3:137]莫里哀并不反对艺术法则,只是认为,法则作为一种“观察心得”,应当和创造有机结合起来。
李健吾的喜剧创作也逐步由对莫里哀的借鉴、模仿走向了对中西戏剧艺术的融合与创造。柯灵对此曾有过中肯的评价:“它们给人的印象是技巧圆熟,在同时代的剧作家中有他独特的风格。这些戏一律是布局谨严、骨肉停匀的三幕,时间集中(不超过一、二天),地点集中(不超过一、二个场景),戏剧冲突集中在高潮边缘——正如箭在弦上,所谓‘包孕最丰富的片刻’。
这些特点表明作者对欧洲戏剧艺术传统的造诣;语言的凝练生动,富有弹性,又显示作者锻炼祖国文字的功力。”[5: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