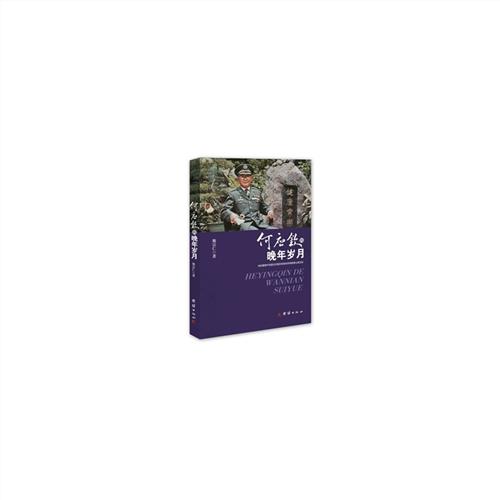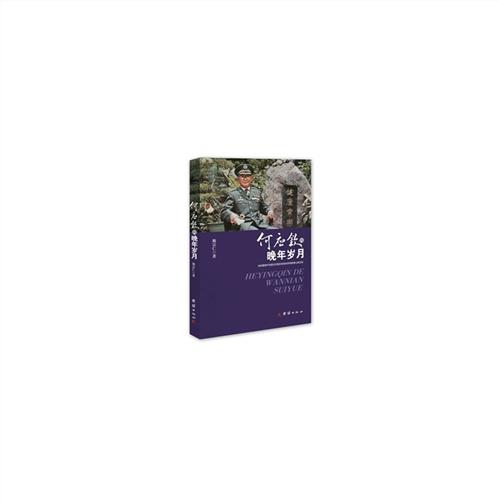何应钦的晚年岁月
1949年4月1日lO时半,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团离开南京飞往北平。3个小时后,南京当局指使反动军警特务对给这个代表团送行的要求真正和平的6000爱国学生行凶。据国民党中央社消息,迄2日黄昏止,学生已死1人、伤11人、轻伤88人。而另据法新社2日报道,学生死2人,12名濒于死亡,55名重伤,50余人失踪,并有数名学生被捆起来投入河中。
南京惨案这血写的事实,把何应钦等人骗人的和谈“诚意”冲刷得一干二净。4月3日,新华社在《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的社论中指出,南京惨案更进一步说明了李宗仁、何应钦政府的和平“诚意”是什么。
自这届政府上台以来,“做了一件确实有利于和平谈判的事情没有呢?没有,一件也没有”。李宗仁、何应钦等人,“一个战争罪犯的毫毛也没有损伤过,但是逮捕和屠杀争取真正和平的人民的事情,却仍然在全国民党统治区层出不穷,南京惨案达到了这一时期公开残杀人民的顶点”。
在和谈问题上,何应钦与李宗仁是略有区别的。李宗仁对和谈的“诚意”似乎比何应钦要多一些。但他把心思和努力集中到如何“划江而治”和寻求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援助上,以便真正取蒋而代之。
诚如张治中所言:“实在说,李的主和虽然目的在倒蒋,要是不问动机如何,他到底是想和的;可惜溺于一派一系的私利和个人的权位,无定见,无担当,到了重要关头,不能作出勇敢果断的行动。”而何应钦的“诚意”并不止于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而是要想在“划江而治”的基础上,恢复昔日国民党对全国的一统天下。
蒋介石虽在溪口,貌似野鹤闲云,但却有7部电台与外问保持密切联系。他可以越过李宗仁、何应钦任意撤调封疆大吏;参谋总长顾祝同要调一兵一卒,都得向溪口请示。对蒋介石这种垂帘听政的太后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往往“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
但何应钦心头口头虽然不满,却不敢在行动上有丝毫拂逆蒋意。
一旦他冷静之后,而李宗仁还在大骂蒋介石,何应钦反来劝说李宗仁,说:“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不知道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对何应钦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矛盾言行,李宗仁深感诧异。
但何应钦私下据实告诉李宗仁说:“他在南京早有特务跟踪,他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①!”说得李宗仁也不寒而栗。因为有人也曾经警告过他,就是你这代总统身边的侍卫,也全是蒋先生的人;只要蒋先生需要,随时可置你于死地。
何应钦、李宗仁认为,要避免蒋介石在背后掣肘,唯一的办法是动员他出国。他们曾经请张治中等人委婉相劝,晓以利弊,都是白费口舌。因此只能听之任之,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国民政府原本就没有诚意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而何应钦充当了国民政府内以蒋介石为首的那股特别顽固的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言人。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何应钦又一次为了蒋介石集团和个人的私利,甘受举国口诛笔伐的历史罪责。
4月20日,已经是国民政府表明态度的最后期限了。以李宗仁、何应钦为首的“和谈最高指导委员会”最后集会通过答复中共中央的电文,并由力主拒绝的何应钦向立法院“分析”中共代表团所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报告答复中共电文之内容。
何应钦认为,“此项和平协定方案,充满了征服与接收的姿态,毫无对等谈判意味”。他向立法院所作的“分析”,可概括为六点:“第一,这个共方所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根本不是一个和平协定,而是一个‘军事管理方案”’;“第二,就精神上说,根本不是和平的精神,更不是双方平等协商的精神。
如果说是降书,比我们当年向日本提出的受降文件苛刻得多”;第三,对国民政府理所当然要承担的破坏政协决议、停战协定和发动全面内战的责任,何应钦认为,“就政府的负担说,实在也担当不下来”;第四,对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对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管制、军事独占是对付征服异族的方式、“报复的方式”,因而“不能接受”;第五,“关于军队的改编,当然十分严重……共军不仅一点儿也不改编,同时政府所属陆、海、空、宪警、地方武力,以及一切军事机构、学校、工厂、后勤单位,均一律改编为‘共军…;“第六,所谓由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我政府也是毫无地位……政府在未来政治上,可以说丝毫没有地位。
”
何应钦与李宗仁两人联名致国民政府代表团并转中共代表团的电文中,对《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极尽诬蔑、歪曲之能事,全盘否定。该电文说:“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势,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为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企图再度延缓解放军的渡江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