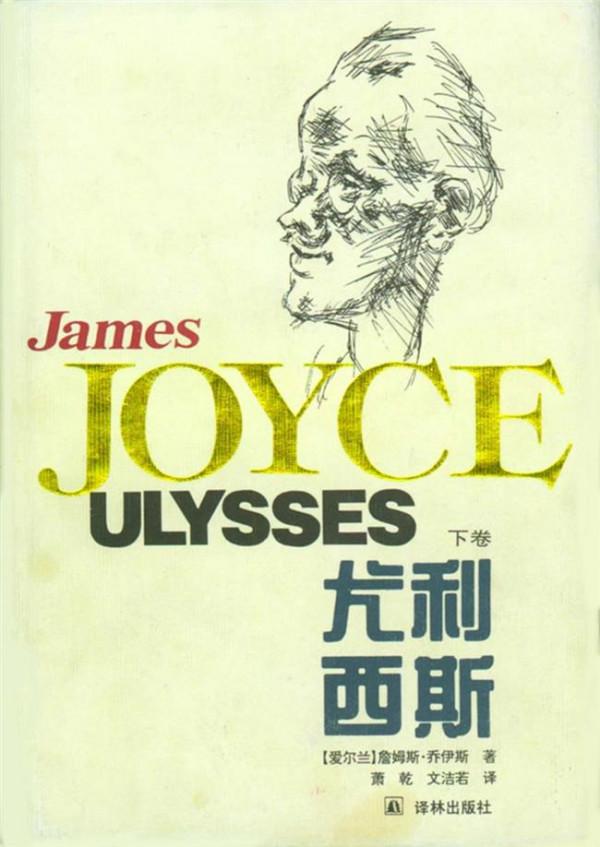黄碧云访谈 谈王安忆、朱天心、黄碧云的小说
文学出版放大镜---城市是现实的镜子◎吴亿伟记录.整理谈王安忆、朱天心、黄碧云的小说时间:十月六日下午两点地点:台北市徐州路官邸艺文沙龙演讲厅座谈者:南方朔、蔡诗萍、骆以军(上)南方朔:近年来,全球文学已出现若干微妙的变化。
从一九六○年代到八○年代的小说形式创新,已有涸竭之势,当形式的变化逐渐倦怠,小说的故事情节、叙事风格等传统小说的基本面遂再度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在这个小说发展出现转折的时刻,来评估中台港三位重要的女作家-王安忆、朱天心、黄碧云,不但饶富兴味,也应有启发。
要论近代的女作家,几乎都不可避免的要谈到张爱玲。她是近代中国文学里最大的天才,她不但创造了自己,也创造了传统,後来的许多女作家都在她的笼罩下成长,而如何与张爱玲决裂,则成了她们的最大考验。
首先说王安忆,我最早从《菁山之恋》接触到她的作品。她生命体验丰富,能够驾御的题材广泛,因而她以写实主义所呈现出来的作品,使得她成为一九八○年代大陆顶级作家之一。
然而,值得注意的,乃是大陆改革开放後,不但文学的欧风美雨大量涌入,长期在大陆上被略而不提的张爱玲也重新复活。而许多文学评论工作者也以这两种新的取向当做评价文学的重要指标。於是,王安忆遂有了《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这两部被文论家称赞。
理论先行反而显出作者的局限《长恨歌》是一部文论家称为「向张爱玲致敬」的作品,但能充分驾御写实技巧的王安忆,她其实很难有足够的体验去叙述只有张爱玲始有可能去掌握的衰败、虚无、沧桑等课题。
因而《长恨歌》在刻意求工下,反而显露出作者的限制。《长恨歌》是王安忆穿了一件不适合她的衣服。评论家的称赞,则是他们「爱张及王」心结下所造成的「过度解释」同样受到评论家称赞的《纪实与虚构》则是媚文论之俗的作品。
这部小说为了文论里纪实与虚构这两橛硬是生邦邦的在形式优先的考量下写成。以虚实并呈的对比手法写作家族史小说,拉丁美洲文学已蔚为传统,《纪实与虚构》不是优秀的作品。
不过,王安忆终究绝顶聪明,我认为她的《处女蛋》就她的写作生涯而言,乃是重要的转捩点。这部作品显示出她对随波逐流的反省。她此後的作品又回到她自己以及她所处的时代,而《富萍》能掌握新与旧的变化,并重新定义生命力,它能获得大陆最高的「茅盾奖」,不是没道理的。
台湾的朱天心则是我一向推崇的作家。她的原创性之高,在近代文学里少有人能比,嘲讽、百科全书式的叙述模式,同性恋文学,以及耽美的感觉主义手法,波特莱尔及班雅明式的碎片漫游,她都有开创之功。
而她那种举岛滔滔皆向政治正确低头,唯我坚持政治不正确的胆识,也确实让人佩服。而这也使得她成了当今台湾一切都讲究权力竞逐时,文学这个领域里的主要争论对象。
难免有些不怎么够资格的评论者,会用泛政治的观点来解释她的文学。泛政治的解释把文字搞成政治的结果,只会出现滥政治,还有滥文学。它两种误读同时触犯。不过,作者与时代不断互动,难免也被时代所扰乱。由《漫游者》似乎已可看出朱天心已被她所处的时代所扰乱了。
这本书有许多私容性,而在不私容的部份则有太多情见予辞的愤惫。我认为她的先生谢材俊说她「焦虑」,乃是最准确的描述。她焦虑於时代变化转折时的浑沌倒错,焦虑於别人不友善的眼神。
而我相信,她终究有一天会察觉到这种焦虑其实并无必要。文学的价值从来即不是政治所能决定,如果文学工作者能将焦虑升华为悲怜,在悲怜中重新检视一切,更锐利开阔的作品即会出现。台湾的文字需要在许多课题上沈淀出更深刻的东西。
至於香港的黄碧云,台湾读者不是那么熟悉。她聪慧多才,熟悉多国语文。由於关切众生,後来进修取得律师资格,主要经办穷人及平民的刑事案件,因而她对下阶层的女性以及社会现象面有著极为广泛的理解。
她的文字不太受华人文字圈的影响,直接与当代西方作品挂钩。她早年的作品有张爱玲的影子,但很快就被扬弃。黄碧云的作品大体上可分两阶段,从早期到《七宗罪》基本上都以写实为主,故事性仍强;但《烈女图》、《媚行者》和《无爱纪》却风格丕变,有些甚至难以卒读。
这其实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人们的叙述,经常都由许多逻辑、思维方式,以及感觉、联想与认知的模型所建构而成。这些後来即成为我们习惯了的感知和叙述系统。
但文字和艺术上,却经常会有人想要打破这样的条框,用另外的方式来叙述他的感知与联想,由於他的叙述与想像方式与我们的习惯不合,读起来即难免相当吃力-我们的感知模板与他想要传送的信息间有著极大的落差。
阅读吃力缘於作者到底要写什么?为什么要这要写?蔡诗萍:这三位小说家的作品,每个阶段都有很明显的特质,这些特质使我们能深入挖掘她们写作的内在心路历程与外在呼应环境的线索。她们的近作,都有一个相近的特色,阅读起来十分吃力,这些吃力的因素包括了,作者到底要写什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写?这三位作家处於二十世纪末,对写实主义的传统产生怀疑及反动,很正常。
早期三人作品风格皆倾向写实主义,有许多不错且易读的作品。
她们的近作,企图呼应反写实潮流,都有开拓一个新方向的企图。她们的作品中,都有一颗不安、漂浮的灵魂在里头,这跟她们所置身的城市身世,有很大的关联。黄碧云比较幸运,香港文学较无包袱。王安忆则不然,出生上海的女作家,甚至包括台湾的朱家三姊妹、张爱玲都是她们精神上很大的指引,也是很大的包袱。
可是朱天心在《漫游者》里呈现出的不安及飘流,却走出这包袱,直接对台北、对台湾当下的身分认同氛围表达疑惑。相对的,黄碧云就很自由的以个人的角度任意穿透女人置身的香港历史。
而王安忆除了要超越自己的写作成绩,还要走出「张迷」对她不断的检视,找到一个当代上海作家的定位。从《长恨歌》中可以看出她企图用一个女作家的角度去思索上海的历史。
反观朱天心,在一个漂浮和不安的时代里头,在岛屿文学主流趋向注重族群身分的正当性及写作意图,以及对写作成就下褒贬的政治正确性庞大论述压力下,她采用一种移动的姿态(要注意这不等於逃避),去思索像她这样的作家置身的时代。
在一个动辄用简单二分法画分主流非主流的环境里,她选择这样的方式去寻找自由的空间,像漫游者一样。《漫游者》中,性别角色非常薄弱,这跟王安忆及黄碧云仍用女性的视野去回应所处城市的历史、自我身分及其中的生命情境,是非常不同的趋向。
三座城市的当代课题,给了女性作家不同的生命情境,但台北,过於政治化的氛围,则让朱天心挺身跳出来,提出了超性别的「自由人」的思维。骆以军:李欧梵谈到张艺谋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说:「张的乡村教养使他无力胜任一个关於老上海的大都市题材」,似乎张艺谋也意识到他拍城市的力不从心,所以在里面穿插了一段又长又离题的乡村片段。
其实王安忆写的剧本《风月》也有这个问题,王安忆并不是一个清楚的海派作家出身,一开始的出手不是张爱玲式的,而是被归纳进八○年代中後期的「知青文学」。
戴锦华说,「知青文学」不同於昆德拉指六十年代东欧文化界「一代人清算自己的青春」,这群大陆知青,反而是从历史的灾难、劫掠与罪恶中救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他们绝望地尝试将自己的青春记忆从关於历史的话语中剥离出来,在这样的语境背景里,上海作为一座「被凝视的单一城市」而浮现,便显得吃力而轮廓紊散。
(下)当今全球文学有涸竭之势,而在涸竭中则有新的探索,作者必须重新寻回说故事的传统。骆以军:王安忆的叙事朝上海挪近所做的功课,及超越张爱玲的动作,是在《处女蛋》《忧伤的年代》之後,她一直在处理一个悬而未决青春忧伤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王安忆的叙事就有问题。
王安忆曾描写在一个叫「榆林」的小镇,那里的年轻人都到便宜的舞池学跳舞,「大家跳得认真而勤勉」,他们对女孩文雅又害羞,但又有随地吐痰和弹菸灰在池上的农民习惯,但他们的舞蹈比赛的评审「如电视台歌舞比赛一般一一亮分,然後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将他们从各种渠道得来的知识运用得很充分」。
这种对土气的幽默和包容和张爱玲的上海人已相距千里。
我认为《富萍》是王安忆至今最精采的作品。其中两个主角的双结构:一个是有老上海弄堂记忆的奶奶,就是张爱玲常小说中替人帮佣的少女小艾或阿小,在上海打盹的半个世纪後,已经是个老人了,还怀带著旧时代的道德标准、势利、品味。
这是王安忆在经历〈长恨歌〉向张爱玲致敬後,回溯老上海的泼辣、世故;但是王安忆厉害之处在於创造另一个角色,为王安忆自我的青春造型-富萍,她怎样从上海的边缘卫星城市,一步步走到上海的边界,钻进上海的街道、弄堂,甚至後来走到苏州河畔。
此时,王安忆的「异乡人」镜头已经和张爱玲的封闭剧场完全不同了。至於朱天心最早期的叙事腔调便已和少女张爱玲挑衅了,张爱玲会营造那种「第一炉香」、「茉莉香片」的女说书人气氛,朱天心则像城市上空短波频率的DJ。
当王安忆在感叹「城市无传奇」时,朱天心的小说,对於城市空间的剧场想像,早已脱离了张爱玲式的公寓框架。当我试著想说这或就是朱天心所素描的「台北人的忧郁」时,我先引卢卡奇的一段话,「小说是成熟期的形式:它的作者失去了诗人那种青年人的光焰照人的信仰。
他需要将一切文学的基本信条向生活提出,这种提出越不寻常,越痛苦,他就越清楚体会:这仅仅是一个要求,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小说有一个可怕的孪生兄弟,就是消遣小说,它清楚的预设好都会人的阅读情境,把这些东西代谢消耗。朱天心在这三位作家当中,最像卡尔维诺、徐四金这些说故事人,她会去找出城市支撑的元素,比如城市与符号、城市与记忆。
在〈去年在马伦巴〉里,她的人物是像碎纸机咀嚼吞咽了整座城人们共同的垃圾资讯、流行成一只梦游时间的爬虫类。(这或是为何王安忆总在「进城」,朱天心总在「漫游」)。《古都》里她玩气味,玩死亡证明、玩跨国资本主义的品牌……,其实是最早有意识地用另外一座城市、建立在这座潮汐沙滩的城市上。
那像川端《雪国》的开场:黄昏时夜车上的人瞪著窗外,外头流动的田野篝火、叠印在玻璃上中年男子的疲惫衰老的脸,但同时看见一张美绝伦的少女的脸……。
到了《漫游者》,朱天心已在描绘一张「不存在的地图」,她从班雅明的那个在时间风暴倒走的天使,变成了温德斯的「如要找到马戏团秋千上的女孩,就得交出翅翼」的天使。
那里触及一个「死亡交换」的命题:永恒的静止或瞬间的记忆,无意义的感伤,最後变忆的独白或颜色气味,挤在人群里的安全感?南方朔:近代所谓的「女性书写」,其实也就是正在尝试及发展中的叙述样态。许多女作家试著要叙述女性的生命经验,有些人以为将女性生活里的各种细微末节堆叠而出,即是「女性书写」,而这种毫无爬梳清理的叙述方式可能是失败的,因为它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琐碎书写」。
黄碧云的後期作品之所以难读,也在於她试图创造出一种她认为「女性书写」样态,它有著高度无关系联想的特性。
她显然希望藉此来晕染,突出角色的作用,但经常难免主客错置。使故事在漫漶里不知所终。文学一如工业,总是有一个部门在那里进行研究发展,新产品出现前,实验室的仓库里一定早已堆满各种尚不完整的实验品,但比较这些实验品,却可察觉它意图的发明方向。
黄碧云现阶段的作品,乃是正在研究发展,当我们读她的作品,不妨从这样的角度切入,以揣摩她风格演练的路径。
当今全球文学有涸竭之势,而在涸竭中则有新的探索,作者必须重新寻回说故事的传统,而在说故事时,不但要有新的关心,更要活学活用及消化已完成的创新技巧,俾创造出新的风格,中台港三位秀异作者的故事,所提示的可能也是这样的轨迹。
蔡诗萍:二十世纪之後的作家,对作品抱持较大的警惕,她们对自己的东西能不能实践写实主义作家信心满满的信念,有较大的反省空间。这三位作家,她们并不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达成社会革命及革新,而是为了达到自我的救赎及心灵的升华。
是否要像写实主义一样要强烈表达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也是我们阅读时感到困惑的,在讯息上,不易懂她们要讲什么,在叙述上,她们也更细致。当然这三位作家在这条新光谱上,选择了不同的位置。
但她们都想透过作品,告诉你一个写作者面对大的时代丢出来的难题时她们所做的回应。这样的回应模式,并不希望得到别人的感召,只是要说一个「故事」而已。因为她们是小说家,回应的方式便是透过小说的虚构,去表达整个时代。
写实主义作家有一个强烈特质,写作的念头及作品具有高昂的信心及战斗意识。朱天心漫游者式的创作者风格,漂浮不安,就像台北这座城市在台湾这块岛屿历史及现实的定位一样奇特,有人说台北人不懂台湾,或不懂中南部的台湾,因为这样社会现实论述,使得台北风格的作家变得更漂流、更焦虑,我想朱天心在某种程度上,点出了「台北作家」的尴尬,他们较国际化,却远离本土;他们对中国较亲近,变得「很不台湾」。
相反的,香港至今还很吻合传统女性隐喻,殖民与回归,都改变不了强权下的宿命角色,论述的调子主要还是大中国风味。黄碧云在这样的文学角色里,包袱较少,女性战斗意识强。而《长恨歌》里过於简单化的隐喻可以看出,政治对於王安忆的干扰并不大,王安忆轻易接受的政治解读逻辑,经由小说来见证一个城市的命运,有时是很危险的。
这一点,朱天心比她深刻。骆以军:张爱玲一九四三年写的小说《封锁》中,空袭使电车在封锁中停止了,「当这个城市随著时间经验的无意识节奏被悬置、变更和凝固起来,一个现代性的寓言诞生了」:当上海这座城市打盹时,一个伟大的女作家如何溜进它的潜意识里,查看它的睡梦。
这个抒情性隐喻恰可作为今天这个主题的双重变奏,一是上海的停顿(上海中断了半个世纪的,卡尔维诺所说的:『同一个名字的城市下,其实住的是彼此完全没有关连的另一批子民,原来那座城市的神只早已离去』),以及李欧梵在《上海摩登》里所说的,「上海作为香港的她者」或「上海作为台北的他者」,在一座城市的里面拟造另一座城市的象徵性缩影。
二是张爱玲的停顿-今天谈王安忆、朱天心、黄碧云在小说美学的选择及对於对位城市的知识性理解,她们是站在怎样的位置去修复?重新拼装张爱玲那只停掉的表,让它续走,并对时到她们自己的城市时刻? 噩梦如魇 清凉一夏 水欲泽之 爱欲来时 四季百合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