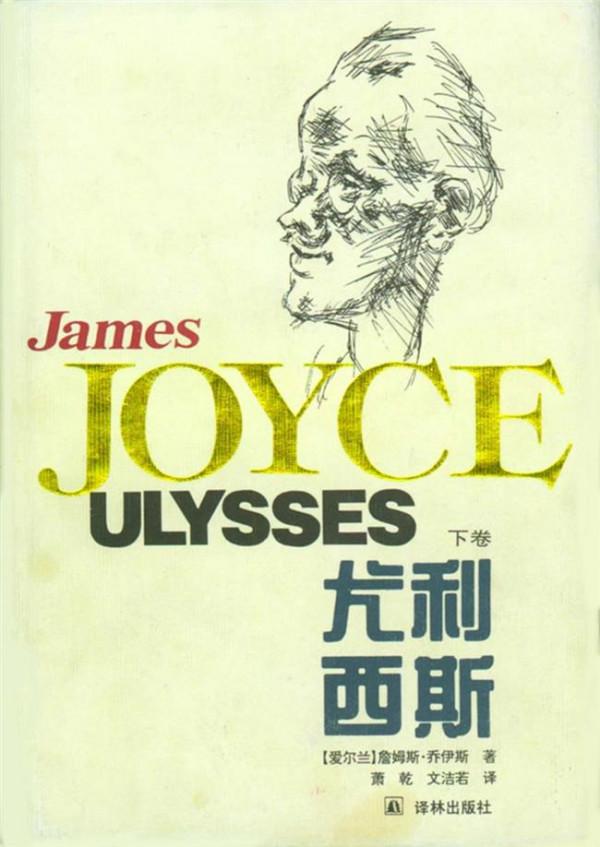黄碧云的书 一个女子的尤利西斯——黄碧云小说中的行旅想象与
一个女子的尤利西斯——黄碧云小说中的行旅想象与精神家园 只有在黑暗里才可以感觉空间。我以为世界有多大,总想一直的走下去;但原来一个人的脚步只有脚步那么大;无论我走得有多远,我带着的还是我自己的脚步。——黄碧云《沉默。
暗哑。微小。》 一、 香港作家黄碧云(1961—)个人的行旅经验不算浅,自八十年代步入文坛开始,黄碧云的作品就与她个人的行旅踪迹密切相关,甚至此一旅程至今仍在进行中。 她的首部短篇小说结集《其后》(1994)甫出版即引来论者的注意,其中较早期的两篇评论不约而同提到小说中人物的「飘泊感」以及以异地作为背景的特色。
诚然黄碧云的《其后》与《温柔与暴烈》(1995)两部小说集的异地背景与人物行旅情节之频繁,很难为读者所错过。
单以上述两部小说为例,其中所涉城市包括法国巴黎、荷兰阿姆斯特丹、英国伯明翰、美国纽约、日本别府、北京、广州、台湾、孟加拉国达卡、越南西贡,当然还有香港。不过论者对此一行旅飘泊和地域特色的评价不能算高,郭恩慈在〈《其后》的刻意人物〉中认为「在异国的时空中,小说人物可以依照他/们的方式来生活,用有异于家乡的方式去接触生、老、病、死。
黄碧云笔下的人物也不例外,借助在异国的陌生空间中,她/他们都十分刻意地去寻取一种不平衡的生活。
」 颜纯钧则认为《其后》与《温柔与暴烈》「虽然从地域上看是满世界跑,视野似乎比任何一个香港作家都开阔,从时间上看也忘不了当代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但时空的延展并没有进入人物的灵魂。
」 要言之,黄碧云这两部早期作品在两位论者眼中失诸「刻意」和表面化。重读其中片段,的确发现她的小说经常出现对异国城市本质主义式的理解,例如〈花城说〉写巴黎︰「或许在巴黎,一切都会自由愉快一些」、「欧洲天气,永远的寒冷与阴雨,把人的性情也磨练得决绝些。
」 〈爱在纽约〉又写纽约道︰「我想,在这变幻多端的城市,一切都会狠毒些。」 在这些相近的句式中,我们看到地域的决定论,以及人物对地域预设的单向理解。
然而这一系列作品的地域元素果真只为了让小说有一个「愉快些」、「决绝些」或「狠毒些」的背景,让主人公可以「寻取一种不平衡的生活」吗?在这些发生于不同地域的故事中,可有共通的意义模式?在相对简化的地域文化理解和公式化的旅程行进模式中,又有何文类的意义,并与日后行旅主题互相发明?以上问题不妨由黄碧云颇具代表性的一篇少作谈起︰〈怀乡——一个跳舞女子的尤滋里斯〉。
二、 〈怀乡——一个跳舞女子的尤滋里斯〉(1988)(以下简称〈怀乡〉)是黄碧云以个人行旅为题材的最早一篇短篇小说。
题目中的「尤滋里斯」即Ulysses,小说初刊的时候有编者按语︰「尤滋里斯(Ulysses)源出于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木马屠城记〉,是故事中的英雄。
而英国作家乔哀思(James Joyce)也有同名的小说,书中以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而闻名。」 无论是荷马的《奥德修纪》(Odyssey)或是乔哀思的《尤利西斯》(Ulysses),是尤利西斯海上十年飘泊还是布卢姆在都柏林一天的活动,黄碧云以Ulysses为题,即见这篇小说与旅程(voyage)的重大关系。
《奥德修纪》分为三部份,包括第一部「帖雷马科」讲述尤利西斯独子帖雷马科寻问父亲下落;第二部「尤利西斯的漂泊」讲述尤利西斯海上归程中各种蒙难与试练;第三部「回家」讲述尤利西斯排除万难,终与妻子团圆。
寻问先辈之下落或生之根源,羁旅漂泊,然后踏上归程,俨然成为黄碧云日后行旅书写的三部曲。
〈怀乡〉内容讲述二十六岁的陈玉放弃如日方中的舞蹈事业,到陌生的阿姆斯特丹游历的经过。在水城中的风貌、教堂、艺术、以至路人之间,叙述者开始回溯个人的事业与家庭的经历,包括艺术事业的虚妄与不真实,以及与母亲生前一段互相折磨的痛苦回忆,继而得出生命如幻觉的感叹。
黄碧云小说中一向对异国无事惊心,历尽沧桑的叙事声音与〈怀乡〉中强化地域陌生感构成对照。
荷兰成为一个让叙事者洗涤过去,清白身心的地方。 小说刻意把旅游书般的资料与个人私密经验比照,将陌生的风景与陈玉个人与母亲、情人以及舞蹈事业一再重复的命运交错呈现。 其中一次又一次击退母亲的阴影与象征童年梦魇的灵体,与尤利西利在海上抵挡赛伦(Siren)歌声或风神等各种妖怪的情节可堪比拟。
最后,一切的骚动由母亲的死亡与阿姆斯特丹的随意和堕落总结︰ 大白正午,强烈的阳光,在世界的角落,一个堕落无由的欧洲城市,我不过是暂时的血肉之身,〔……〕或许我会回去,继续我的舞台事业,而且比以前做得更好,又或许我会继续我的旅程,佛罗伦萨、伦敦、巴萨隆那……。
〈怀乡〉与同期以行旅的主人公为题材的小说大致不离这个行旅想象模式︰「回叙—试练—顿悟(还精神之乡)」,往往又以末段写得最为动人,由激烈的试练回到现世风景,再引出可能的顿悟及还乡的心情。
另一篇比〈怀乡〉更早的〈流落巴黎的一个中国女子〉, 亦曾写出定居巴黎的陈玉在目睹纵情的叶细细异乡自杀后,迎着巴黎清晨的雾想到返回香港的心思︰ 出得地面来,太阳经已升起,雾气隐退,淡淡有暖意。
鸽子觅食,停在我脚前,我一举步,一群的飞走。我抬头,见得树头有新绿,扫叶的阿拉伯人,跟我Bonjour。
〔……〕人的存在,也不外如是。我突然很想回香港,我已经六年没想过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狭小嘈杂,很多人七手八脚你推我挤的生长……因为小,人的存在也切实些。我就下了决定,明天去探听一下机票价钱。
以上例子可见黄碧云具行旅背景的小说表面上为现代女性写出独行外向写照,实则小说最终往往载满辗转思归的心情。所归何处,并不需要一个肯定的归属点,有时只是一个希望落实的想法,一个走下去的愿望。
而行旅期间对世界的想象与定义,也并不具必然性,巴黎的决绝、纽约的激烈或阿姆斯特丹的陌生,最终只是诱发顿悟的一系列异域性,让主人公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得到心灵的一刻舒解。这种地域与个体精神上的随意(arbitrary)安排、情节模式的外露以及顿悟转折的轻省,很可能就是黄碧云早期异国书写为诟病的地方。
然而若结合黄碧云个人情非得已的飘泊经历及原乡欲望,阅读她小说中的行旅情节就会多了一层自传式的复杂性,解释黄碧云对人生如旅的执迷。
黄碧云在游记散文集《我们如此很好》中有〈我与机场的忘年恋〉一文,当中提到往纽约时在机场与兄长送别的情况︰ 我要飞纽约。我的长兄要来送我,或许怕不能再见到我了。我还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快要进入入境台了,便忽然说, “就像要去死似的。” 他已经双眼发红了。我心一难过,忽然便流下泪来,其实眼泪时常都白流,是因为不够聪慧通透。有甚么好流泪的呢,连最不喜欢的人都会再碰面,更何况是有心相见的人呢。
只怕相见时,人面全非,见总会再见的,除非死了。死了,已成定局,流泪就更白流的了。只是当时不明白。 刘绍铭曾指出上述引文中黄碧云变本加厉,在情感上伤人自伤的残酷。 事实上黄碧云的确反复叙写这一段由至亲送别的情节,并在不同小说中变奏重现,难舍难离。
早期具行旅背景的小说还有〈七姊妹〉(1988)、〈爱在纽约〉(1989)以及〈其后〉(1990),三篇小说在篇末有长兄或姊姊送行的描写,虽然远行在即,但思归不舍的意味更为强烈,当中情感的重负更见于兄姊交付的「信物」︰ 我将衣服穿起来,在口袋里却摸到了一个小白包。
掏出来,软绵绵,大概是空的。然而摊开只是半绺发,是母亲的半绺发。到达伦敦,已经入黑。
我钻入地底。伦敦地铁,陈旧而疲乏,不见天日。便不感到夜,只感到口袋里半绺死人头发的沉重,竟也难以举步,就立在深黑的地底之下,地车呼啸来回,我的脸孔冰凉而热刺,如此这般,由血肉相连的痛楚,想起了,七姊妹。
〔〈七姊妹〉〕 等待起飞时,我在机舱困着了觉。克明临别前塞我一迭厚厚的美元,还在我口袋里辛苦的坠着。〔……〕然而风尘阅历,到头来,甚么也没有。纽约已经消失在晴朗的空气之中。洛杉矶又怎样呢,又会有怎样的历险与爱情呢,怎样的痛楚,伤害,软弱,疲乏呢?生命在我面前无穷的开展。
我只是嫌它太长了。 〔〈爱在纽约〉〕 我坐在窗旁等火车开动,远远见得一人,一拐一拐的向月台跑来。我眼里一热,挥手招他︰「大哥。
」他拿着一个大包包,跑起来很吃力。火车鸣笛,他上气不接下气,挨着窗,推给我那个大包包。我不禁紧紧握着他的手。〔……〕打开包包,里面是一套和服、一双白袜、两条内裤、两件白内衣、一双木屐以及一只小木鸟,那是我儿时沉迷的玩具。
我紧紧握着小木鸟,包包在我膝上很重。〔……〕旧金山、德萨斯、东京、医院的长廊及清洁的药味。我的白袍,一生如此掠过。 〔〈其后〉〕 在以上三个片段之中,小说主人公来到故事的尾声,旅程的终结,都在车站或机场与至亲经历了生离死别,临行均收到叫人感觉沉重的信物,并在手握信物之际,匆匆检视了过往的一段人生旅程,结果感伤而迷蒙。
自此旅程竟为了承受血脉至亲的寄托,完成疚歉的人生。行旅的内省意味,至此最为内在而本质。
这些主人公往后的旅程,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最激烈的人生试练,或仇恨、嫉妒、丧母;或爱、被爱与被遗弃;或罹患绝症、丧妻与丧妹,已经在之前体切地经验过了,「其后」的人生,已是另一个故事。
就其相近者而观之,黄碧云这种执一母题,累篇发挥的写法,难免予人重复之感。加上其中自传的成份,更显出难以跳出窠臼,行行重行行的自怜自伤。这都是合理的批评,但我更认为黄碧云早年这一系列行旅作品的独特性,正正在于展示行旅漂泊的终止,以作为对爱她的与她所爱的人的补赎。
不论经历多少身心伤害,时空游荡之间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主人公在故事结尾都不约而同静极思归,以至还带着代表着家人、亲族或童年记忆的贴身之物,重重如铅锚一样尝试固定未来浮萍一样的人生。
甚至可以说,小说中的漂泊练历越是创痛酷烈,「其后」的回归与静止越能表示作者对其缺憾人生的疚歉与补赎。正如黄碧云在《其后》的后记中所言︰「因为对生命种种严峻而浪漫的要求,我不能够做一个快乐正常的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失败与欠缺,我无法表达对我长兄的歉意。
我的写作沉聚了这些对生活的追求,我希望这可以成为一点点无用的补偿。」 因此黄碧云小说中的漂泊一开始就不是一般女子行游作品的外在体验或征服,反而是写其体验之不欲得,起步即是归程,熬过最痛即能获得救赎的愿望。
其后的故事,真的并不重要,黄碧云亦没有马上写出这些疲倦行旅者往后的故事,起码在十年以后(就如尤利西斯在海上漂泊的时光),她才开始动笔搜寻笔下尤利西斯的下落。
三、 黄碧云在《媚行者》(2000)中这样说︰「《媚行者》也是一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小说——如果将过去重新活一次——如果再到十年前到过的城市——如果十年前的小说人物,她们还活着,没有自杀,还活得……她们对她们的所谓人生,有什么感悟?」 《媚行者》因黄碧云在1997年8月膝盖受伤而起,半年后复元,对行动的自由亦有新的体悟,遂于1998年展开南美之旅,最后写成《媚行者》。
作者认定《媚行者》是一本关于自由的小说,行旅与自由往往是一体两面的事,因此可以想象《媚行者》是一部如何开阔、外向与流动不居的小说。事实上,全书六个章节从多角度探寻自由的意义,从南美洲之旅、飞行员断脚重生的故事、阿姆斯特丹狂欢节、巴尔干半岛自由之战、吉卜塞人与客家人的放逐之旅,到最后古巴革命女子坦妮亚的追寻;而小说的主人公依次不断丧失︰丧父、丧失肢体、丧失记忆、丧失土地、丧失家国到最后丧失所追寻的传奇与偶像。
本文无意在有限的篇幅开展关于此书在自由主题上的复杂结构,只想指出这部明显以行旅为题的小说并不如表面所言的媚行放任。某些评论集中讨论《媚行者》「向前走」放逐情结, 但细探各章主题,仍有强烈反行旅的回归意识,但此一回归并非地域上托以终身的某一地方,而是要回归到过去。
整部作品的时光行旅与空间行旅同样复杂。重写作品的意图更令行旅有复调的意味。其中第一章与第三章可与前述《其后》时期的作品对读,理解真正属于「其后」的世界。
十年后的黄碧云在《媚行者》里显出对行旅主题越加深刻的反思。一方面她是反浪漫与反乌托邦的,南美洲古巴也好、东欧罗马尼亚也好,这些异国文化不再是人生问题的答案,甚至连问题也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所象征的文化特质已为小说中的章节之间互相消解了。
但另一方面,小说主人公对行旅的必然性却是前所未有的肯定。全书在在透露自由之不可得,但同样是一则对行旅人生终极的宣言︰即使失去家园、失去肢体、失去记忆、失去土地、失去先辈、失去理想,人生的真相层层剥落,我必不轻言放弃。
就如书中最末一句话︰「一定是我的心,不知在何方,不是问,但又充满困惑——你渴望自由与完整的心情,是否始终如一。
」 这个美丽又焦虑的自我诘问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 让我们发现,步入理智之年以后的黄碧云,对行旅的要求反而最为严峻,不为现世的亲人情感上的救赎,更是人生最基本自由的体现,尽管自由的内涵总是充满吊诡。
黄碧云小说之痛苦来自个人急剧的转变与成长,又正如〈怀乡〉篇末所言,她的小说往往是「为人所能有的委屈与希望而写」。在委屈与希望之间,就是媚行的步迹。 四、 从《其后》到《媚行者》,大抵可以总结黄碧云的行旅的两大阶段︰行旅的思归终止以及行旅的出发再生。
当然黄碧云还有其它与行旅有关却不同形态的作品,包括以《温柔与暴烈》为代表,叙写第三世界坚韧生命力的〈温柔与暴烈〉、〈双世女子维洛烈嘉〉及〈突然我记起你的脸〉等;其次是以中国和香港为背景,写主人公为政治或生活所迫,继而移民或逃走,另觅生存的地方,如〈失城〉、〈双城月〉、〈丰盛与悲哀〉及后期的〈心经〉和〈山鬼〉等。
这一类作品与之前讨论的作品最大分别在于主体与客体的位置。
前述《其后》与《媚行者》的例子的主体都放在行旅者的身上,对行旅的意义、方向、开始与结束都有自觉的把握。但后者的行旅者只是小说的客体,为不同原因所迫而转换方向,因此也可以说,主动参与行旅的是作者而非小说的主人公。
本文的兴趣仍在主体性较强的作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较客体化的行旅小说中,其行旅的方向仍是面向归途的尤利西斯式回归。即使表面疯狂诡异的〈失城〉,最终身陷囹圄的陈路远还是有一种托身得所的宁静,把世界留给更疯狂的詹克明及其痴呆儿。
此外〈温柔与暴烈〉、〈双城月〉、〈一念之地狱〉、〈捕蝶者〉、〈江城子〉,主人公无不在残酷的试练以后得到暂且的平静,基调仍与〈怀乡〉相近。
整理黄碧云多年间创作的小说人物之行旅踪迹,不难发现其中经历地域转移的占大多数,而且地域分布甚广,不少更具自觉的行旅意识,亦与作者真实人生的行旅息息相关。其实打从《其后》开始,黄碧云的作品的异域性与本土性几乎是一个不断此消彼长的循环,顺时序来看︰《其后》(1994,异地)——《温柔与暴烈》(1995,异地/香港)——《七种静默》(1997,香港为主)——《烈女图》(1999,香港)——《媚行者》(2000,异地)——《无爱纪》(2001,香港)——《血卡门》(2002,异地)——《沉默。
暗哑。微小。》(2004,香港)。每一次远途的行旅书写,彷佛为下一次回归的创作凝聚迫力,就如写过奔放的《血卡门》以后,紧接而来就是写回港后在湾仔律师行上班幻灭与苦闷的《沉默。
暗哑。微小》,当中前作与近作对比和张力亦愈来愈强。近年黄碧云经常旅居他国,来回英国、西班牙与香港之间,其间又短访南美洲、巴尔干半岛及罗马尼亚与匈牙利等。
本文执笔之时,正值黄碧云在西班牙学习佛兰明高的第三年,并在思考回港还是继续旅居生涯的问题之中。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令到一个作家长期在外漂泊又辗转思归?这里当然有十分个人的理由,然而世界之大,最后却竟容不下作者「对生命种种严峻而浪漫的要求」,而逼使要上下求索,定然与在香港极其严峻的写作环境有关。
不过这肯定是另一个故事了,走笔至此,我只是不能忘怀黄碧云在最近的小说〈微小姿势〉所写对巴黎的幻灭,以及对整个真实人生的误会。
黄碧云刻下追寻的显然是一个精神家园、理想之国。作为读者,自会发现她在一次又一次方向转换的途中展现越趋深刻的文字世界;作为她的长期读者,我们偶尔也会希望她在广袤的世界中,寻找到一个不那么痛苦的位置,像海上漂泊十年的尤利西斯,终有回到精神家园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