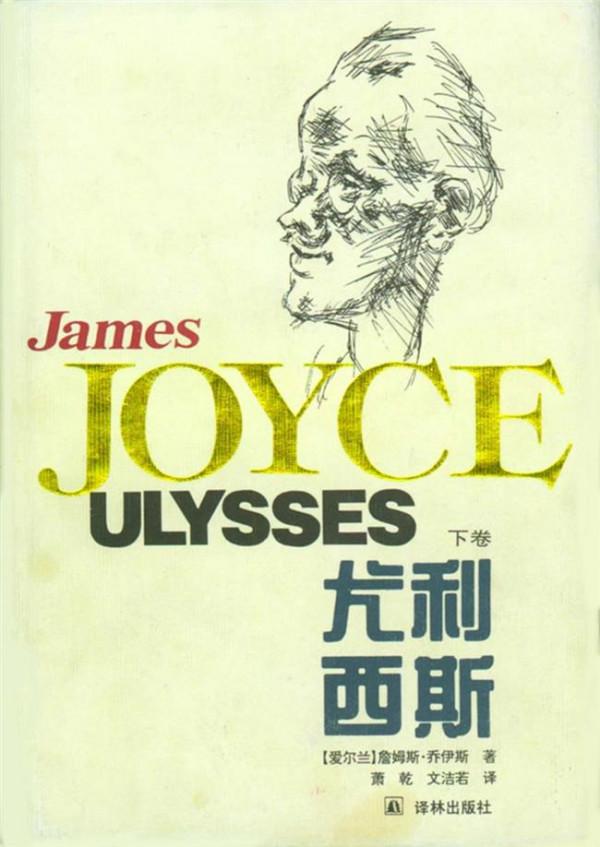黄碧云短文 爱丁堡 一个明媚的早晨 (文/黄碧云)
◎黄碧云 (20061102) 我曾经以为是-------。後来我沉默不语。当海鸥如同凶恶的鸽子。每个早上起来空气总是凛烈。天空是撕裂的蓝。人说的断崖与城堡。我们经过。有时会听到低音大提琴偶然的:Da-得;Da-得;我无法分辨黎明的蓝与黄;我说黎明比较蓝一点,而终结的时候总是闹亮的黄。
他们无法明白,也没有兴趣明白,语言最终原来是那么的自说自。我在厨房冲一杯奶茶,英国厨房及奶茶,银匙敲在崩裂的旧茶杯之上,那样清脆灵巧寂寞的声音;我对食物从来没有热情,但我总怀疑归宿就在一个没有食物香气的厨房,坐下来,我说,让我静静的坐下来,我想喝一杯早餐奶茶。
当节日如同血之泻地。我如何明白一个节日呢,好像与时间有关,重复重复,但人已经不一样。
那年我来到这个节日,爱丁堡的夏天,我记得只是飒飒的寒,我在一个红色电话亭,擦著双脚抖著身子打一个电话。我说原来八月那么冷。我没有想过我会再来。再来的时候原来我还记得城堡。
我们吃油热的炸鱼薯条。一条长长的斜路,有人午夜在玩火把。如果想来,那条斜路一定是那条我每天行走奔跑无数次的高街。有人问我:你知道高街吗?我拖长声音说,我---记----得。那个问路的人,没有等我的答案,便离开了。
谁会想知道你记得些甚么。 我们明白雨。(你怎样明白,阳光与雨的些微分别?)打开窗还是小剧场的灯亮起,总在提示雨。每天都经过雨。提著极重的箱子,推著鼓架,背著我的舞鞋和鱼尾裙,电脑,大背包一堆永远派不完的宣传单张,我们去拿宣传物品的时候,小伙子说,you are screwed。
我失神的大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在剧场与艺穗节办公室来回奔跑,或者那个难忘的午夜三时的技术排演,我们总会遇到雨。
苏格兰的雨,黑色。或许是我的心的缘故,我从来没有那么苍老过,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天微亮。从的士看出去,天微亮。提琴手说,总有那么多事情,不见了就是不见了。他说你知道我并不是说钱包。那些像钱包的事情,提琴手遗下了他的提琴,好像关於爱,天微亮的时候寻寻觅觅,你知道的,说理解,我们从不理解,无论我们可以有多理性有多节制,甚至知道天使的话语,或者苦苦思索真理,你问你知道那个青铜像吗,高街的David Hume,他也说关於理解,一街的笑声与绝望,年轻女子说请你拿一张宣传单张好吗,我想回家了;年轻的肆意是从来不需要理解,鼓手夜半回来说哦你偷了我的白磨茹,很甜的白磨茹,我说我买回给你吧但原来我们愿意理解的事情是那么不一样。
我以为是关於音乐而她想的是白磨茹。 我们都误会了。在我人生里面总因为误会而伤心。而我以为我不会再误会。他说我不希望你会觉得难过但我说我已经觉得难过了。这真是间美丽的房子,美丽的苏格兰老房子,很高很高的旧水晶灯,摇摇晃晃的木楼梯,恍惚一定是肉体感觉而无其他,我时常是第一个,打开房子的门,他们出去看表演,游览,我很不合时宜的在厨房倒一杯麦芽威士忌,几乎是预咒,无人的剧场,後来我老做一个重复的噩梦,表演开始了但没有观众,也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一个,我想是不是表演改时间地点了但没有人通知我,六时半开的场,梦中是六时半开的场真实的是下午一时,七时还没有人到,我在做一个没有人来看的表演。
其後我一生都会做著同样的噩梦。 街就是节日 在人头涌涌的艺穗节办公室,我听到一个美国女子在跟人说,前天我们进场的人还不错,但昨天没有人来,现在我很害怕。当时我想,会不会是我。那天星期天,虽然是唯一的一天,街上有巡游,那天没有人来。
我们做了一个给拍照的表演。真是惨烈。我还有甚么好说。默默的收拾著,还有甚么好说。想起那个美国女子,不禁苦笑起来。以後真的每天都很惊。 就是说:没有一个命运是独一无二的。
连失败也不会。既然命运互相呼应,为甚么我们无法互相理解。「我得到了我一生最差的评论。真是活该。」「没有甚么好解释。只能说自己学艺不精。」「不知道她在做甚么。」「笨拙。口齿不清。可以不理。」奇怪有观众给我留下了字条:「很有兴趣知道WBW 写的其他是甚么。
跟另一个观众谈起,她也很喜欢这个表演。」是不是我自己想像出来的安慰奖。但字条我留在我的档案里,字很潦草,看不清楚。 走在那条可怖的高街上,街就是节日,我买了银戒指依莎贝又编了彩色小辫子;节日的意思就是事情在你意想之外发生。
最後表演那天,我和依莎贝和练拖著一大堆杂物在场地外等计程车,有一对老夫妇走过,我说:这不是 Sir David Wilson 吗。
其实他是Lord Wilson。他当港督时是sir。那时我当记者,习惯了就像我现在还叫那些局做branch。殖民地时期的称呼。卫奕信我在伦敦时找过他做过一个资料搜集的访问,其後甚么也没有写,没有当记者後最大的骄傲是,我可以选择甚么也不写。
後来就写了一个小说,部份做了这次表演的剧本,没有写他所以也没有想到他。但碰到他,就闲话著,不知道他是否记得我,我只说我们从香港来,他说,你们表演吗,我说,是呀,今天最後,已经完了。
他去我们的场地看他的学生表演,剑桥的学生。他说了近况,就像碰到旧人一样。也实在是。我说真巧呀,我跟他们说我们的旧总督就在爱丁堡住,他说,现在有时住伦敦,有时住剑桥,有时住爱丁堡。
来到苏格兰见到山就想到他。香港的山头和苏格兰的有一点像。小路叫卫奕信径。我们的旧总督喜欢行山。 譬如说也没想到碰到机场大混乱。我笑说你们要去希斯路难民营。他们先走,我留下和家人走走。後来我也在希斯路滞留仓,打开电脑,写某一个早晨开始写的。
断断续续,後来我写或不,或我的人生,总是断断续续。事情还是不要再想。最後的那一个晚上,他们出去吃饭,我收拾了行李,独自坐在渐暗的大客厅里,桌面清理了堆起的节目表,他们写的节目评论,烟头我倒了,但空气还有香烟的气味,依莎贝的工作桌,还有她的胶纸,箱头笔,她写的告示,她和他们出去了,最後的几天她挺不住呕了,做完表演我们去吃午餐,她吃了一个牛扒又一个牛扒,体力劳动过量,我们吃量都变牛,平日我不大吃肉居然变得很嗜肉,她吃完就呕,流汗,抽搐,我们叫了救护车。
没甚么事,护士说,要睡觉休息。她很有劲的跑跑跑,我苦著脸在後面跟,原来我比她噤捱,她呕完最後那个晚上,我午夜突然大腿抽搐,痛得尖叫坐起,吓得我姊按著我。
原来广东话是对的,做到你呕做到你抽筋。 忧伤的早晨,愈来愈轻 艺穗的意思是冒险。这个我明白。但原来也是乜都自己做。十分钟入台五分钟拆台走人。来到爱丁堡後我去看表演就有职业病,看人家怎样五分钟拆台。
後来看,他们都很有经验,一块布一个手风琴一个小提琴,挟起就走,那像我们像管弦乐团那么笨重,个个担担抬抬,身水身汗,还付出昂贵的租赁费用。韩国人,好团结,一堆人租一架车,到处做宣传,又送扇又做街骚,我们也做街骚,但声势差一大截,对面有做吹袋笛,袋笛好大声,我们完全无法对撼,阿涂走去叫他,移开一点好不好。
我说你倒够胆。对方答,你来多久?我在这里多久?你叫我走?不久他走了,但我们也捱不久,都走了。
他们没甚么兴头,我倒喜欢做街骚,很自由,随便跳,後来赚了一镑半。有个人,拿著一镑半,很尴尬,因为找不到打开的琴盒,所以就将零钱放在谱架上。当初我还以为是阿涂买三文治找回来的碎钱。
剧场里面就很拘谨。我不喜欢我自己的表演。没办法,自己也不喜欢,没有办法说服人。我弄错了,我误会了,我以为关於音乐与文学,我只是极其笨拙。这个事情我不要想。 排练的时候时常在湾仔街头。上一份工作在湾仔。
转了一个圈,又回来湾仔。除了年纪及其显现,没有承载得更多。想去爱丁堡,排除万难的去了,所得的不过是几张纸几个字,几个笨拙的姿势,愈来愈轻,一个忧伤的早晨,愈来愈轻。去爱丁堡部份费用是由香港特区政府资助,感到很难向纳税人交待,走远一步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无尽的杂务,都是那么难。
一个地方或一件事情从来不可以答应些甚么,我只能说,无论那么小那么笨,一步只能是上一步的廷续。依莎贝是个比较会生活的女子,她说,好辛苦好辛苦,这次的经历我一生难忘,我学会了很多。
我不知我学会多少。表演完了我在高街拍了点照片,又和我姊和练在草巿街的旧衣店西港街的旧书店打转。书店的旧地牢一整个房间都是音乐的旧书,来的时候我在读萨依德和巴拉保音乐和文学的对话,也在读大江健三郎和小泽征尔,在旧书店找到了华格纳的自传,一九一一年出版,书里有藏书票,买的人签了自己的名字,写下了买书的日期是一九一二年。
我想差不多一百年。书很轻,因为纸张很旧。
卖三镑半。卖书人和练在说那本在马可孛罗之前的《城巿之光》,或《光州》。卖书的人都懂书。卖旧衣的女子白蒂,说维多利亚女子的披肩,她母亲结婚时那一件旧狐皮。她说苏格兰人很会保留旧东西。我想起我们住的那间老房子,租给人,很残很旧,热水时热时冷,依莎贝在洗澡时大叫救命,烧开水的壼又漏水,但厨房还留在一整套有印记的纯银餐具。
我在爱丁堡知道的,不是我以为的音乐和文学,或理解,而是节日的艰难。和时间。苍老。这个我必然会学得谦卑。端坐在书桌前,打开一本百年前的华格纳。安静阅读。甚么也不要想。 【中时人间副刊2006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