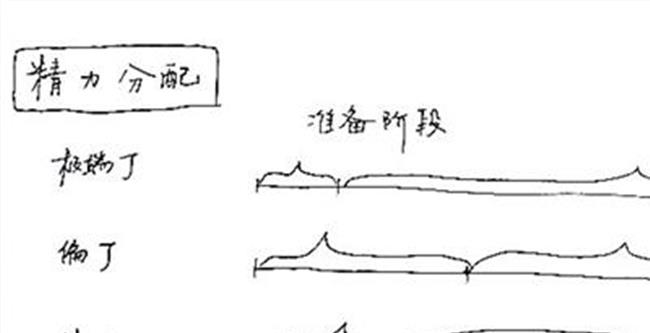扬眉女子黄碧云 扬眉女子──感觉黄碧云
那次和朋友逛香港上环的老街,在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从四壁发黄的流行小说里,忽然发现黄碧云的散文集《扬眉女子》,如找到了宝贝似的拣出,花了十四块港币买下。回来后,先寄给北京一位写文章的朋友急用。那包书到如今有了两年多,尚不知还在何处浪游。
别的书都无所谓,就可惜这本《扬眉女子》。想象中,黄碧云就是一位散荡的、满世界周游的扬眉女子。从未见过她,但从她的书中知道她的情形。
黄碧云新出的第二本散文集《我们如此很好》(香港,青文书屋,1996年5月初版)全是她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的笔记。出入于东方和西方,南韩的金浦机场、巴黎奥里机场、雅典的奥林匹克机场、印度的德里机场、纽约的拿加地亚机场,北京机场……
所以无所谓生离死别,如果伤心,可能只因为寂寞。我要飞纽约。我的长兄要来送我,或许怕不能再见到我了。我还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快要进入入境柜台了,便忽然说,“就像要去死似的。”他已经双眼发红了。我心一难过,忽然便流下泪来,其实眼泪时常都白流,是因为不够聪慧通透。
有什么好流泪的呢,连最不喜欢的人都会再碰面,更何况是有心相见的人呢。只怕相见时,人面全非,见总会再见的,除非死了。死了,已成定局,流泪就更白流了。只是当时不明白。(《我与机场的忘年恋》)
一段话,是独自上路的女子、过来人的体验。到过很多地方,黄碧云笔下的异地带着她的心性和想象的素质,深刻、琐碎而平常。人物、景物融在旅行的心境里:“我在想故事大纲,他们的啤酒、足球、大麻,我的写作,意义似乎都一样,是短暂的快乐。
”(《说城·故事数则》)平常我们说:以心相见,其实写起字来不容易做到,因为太多的写作的程式,厚重地覆盖了文体。不过这对于黄碧云不是问题,她说的是心的触觉,像散漫地讲故事,又比写小说时的她温婉。
一些联想、某些影象和书本、现世的经历和偶然遇见的什么叠杂,心里受到触动的片刻。“一个人内心的晦暗是难以言喻的,因此我与神父接近,但什么也不说,亦不动感情。”她给朋友的信,似真似幻,因为那收信人,分明是她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又不止一个人物叫细细。她又翻写《布拉格之恋》。城市就是这样,你到布拉格,怎么能不想萨宾娜、特利莎。黄碧云的语言在香港作家里是少有的,朴素、简单:
“我在埃及,想起你来。”(《日焚。开罗月亮》)
“这个古老帝国的城市,依旧壮观华美,人在其中的沉闷,中古的乡村性格,黯晦困乏,并不见得明明可知。因此听得非常静,沉下去,沉下去,欧洲陆沉了,而我又婉转难言,一如日蚀,一如安东尼奥。”(《开放罗马城》)
耐读的句子,渐渐有哀愁浸出,如水,丰盛。黄碧云出过三个小说集《其后》(1991)、《温柔与暴烈》(1994)、《七种静默》(1997),都是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可见她写得不多,在我看来,这是挺专业的态度。“天地”的编辑部主任颜纯钩是内行,可能第一眼就“惊艳”了。他的一段文字,犹如傅雷读张爱玲的《传奇》。
《其后》是黄碧云的第一部小说集。如此年轻,如此才情横溢,却又如此酸楚凄凉,这“扬眉女子”也算是世纪末香港的独特产物了。在她的小说中,生命都是漂泊无依的,在外部世界纠缠,在内心世界煎熬,总是互相纠缠煎熬着,一起沉沦、失落、只有过去,没有将来。
小小的欢喜,沉重无边的痛苦,生命便是以巨大的痛苦换取微不足道的喜悦。到最后连喜悦也不是所求的了,只剩下对于死亡的期待。在她的世界里,死亡并非人世巨创,而只是一种淡淡的忧伤,或者一个苍白委婉的手势,好象有个人漫步走进浓雾,渐渐就不见──他见不到别人,别人也见不到他。人天暌违,也不过像他在浓雾深处轻叹了一声,如此而已。
友情会过去,亲情也会,爱也是一点一点在消逝的东西,甚至恨也是。只有死亡,是最终要走上去的生命祭坛。其后,便什么也没有了。(见《其后》封底)
黄碧云以《温柔与暴烈》获1995年市政局“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奖项。比较起来,《其后》的故事就显得轻和单纯。《温柔与暴烈》的风格如书名,强烈地对立,血腥和暴力的气息扑过来,生命中的好多悸动、痛楚堆结着。而这些,就是爱;虚无莫过于此吧。
读《其后》,有时要想到张爱玲,但《温柔与暴烈》就不了。黄碧云故事中的男女,在东南亚的丛林间挣扎、在加州或者巴黎流浪,她又写罪案和政治;这异国情调、人物故事的芜杂和她以心理感觉作为叙事线索的方式,都不似张爱玲。
她写那些芜杂世事里人心的简约求索,如“温柔的生”,如一点点真爱。但在污浊和狂暴的现世,显得好笑。而人依然活下去,如此不堪,也苟且,也坦荡面对。站在泥泞、黑暗和罪恶的渊薮里,黄碧云善写这些芜杂的心理,绝望、无忧、温柔,相克相生。
这个女子,六十年代初生于香港、长于太平盛世、留学于巴黎;干过六年新闻工作,其间曾多次踏足越南、泰北、孟加拉、老挝,在泰缅边境等地区采访和旅游。“长期接触这些战地边缘,也增加了反思暴力的机会。
”她说:“而到了最后,便可以带入,很宽阔的感觉,就如自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灵魂,在许多地方存活着。”(见黄念欣、董启章:《讲话文章──访问、阅读十位香港作家》,香港,三人出版,1996年8月,第39页)
《双世女子维洛列嘉》来自这个集子,是九个故事中最短的一篇,好象也是唯一没有暴力的一篇。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越南女子的三段相遇,结构清晰。我欣赏作者那种单纯与辽阔的对照。惊却的维洛列嘉、革命敬礼的维洛列嘉、潇洒随意的维洛列嘉,三张照片,祭奠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开始和终结。
男人也活过了自己的三世,身份和政治都是变化的布景。黄碧云看人,那些背景甚无道理可言,所以她很少道德评判,生命意志,在她的笔下,惊心动魄,是为“美丽强壮的女子”。
《突然,我记起你的脸》,是她新出的小说集《七种静默》首篇。一句话,像一句谶语,奇异、神秘地重复;一直看下去,有很多物品形象,令人目眩。这些物品联系人物的故事,集中了强悍的爱情、死亡、残酷和衰老。
我觉得黄碧云是凭感觉讲故事的,那种感觉,带有诗意的突兀和心理的幽冥,她可能着迷于这些东西,于破破烂烂的现世人生中,凭着感觉和物象的线索,她发掘出的故事绮丽和凄惨。这篇小说换了好几个叙事人,每句“我突然记起……”的话突兀地把叙事人弹出来,第一个是个中年单身汉,捷克人,在伦敦开了一家叫“波西米亚”的旧物店;第二个是曼谷红灯区的老板娘,久经风尘,管了一群舞女,酒吧也叫“波西米亚”;第三个是墨尔本的牧师。
由他们来讲说出这句谶语的人:圣诞夜一跤跌死的典当老人、与杀人犯缔结爱的舞女,来教堂忏悔的盲人。
交织在里面的是所谓“奥加的金杖”、宝石发簪、“希望钻石”……一件件珠光宝器,在人世流转。可是,物犹可辨,唯人事变幻莫测。谁是奥加?阳光灿烂的女杀手?脸孔像地狱的太太?或者也包括看清了幻觉的店主?在这个作品里,通过流转的饰物,黄碧云找到激发想象的焦点,她也利用饰物隐含寓意的方式,在物品内重叠罗列遥远的时空,令情节花枝招展。
这种想象是她旅行生活里具体经验的伸延,如她所说:“不同的地域最起码也帮我吸收了很多词汇,不是书本上学来的,而是源自生活的词汇:沙里、银扣、咖喱、丝绸、泥土、达卡城……是一种对意象的吸收,感染了处境和气氛。
但这些都是很技巧的东西,……”(《讲话文章》第38页)很技巧地传达人物的性格──刚烈又优柔的细细娘、了又未了的移民情怀、又或者是对尘世的如缕眷恋:“世上的华美,情欲的触感,让我们爱与痛,因为生命的短暂无由,我怎忍将你毁灭──那一定是魔鬼的诱惑。
”很技巧地写着小说,像“含在喉咙里的一枚金戒指”,记得黄碧云在什么地方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