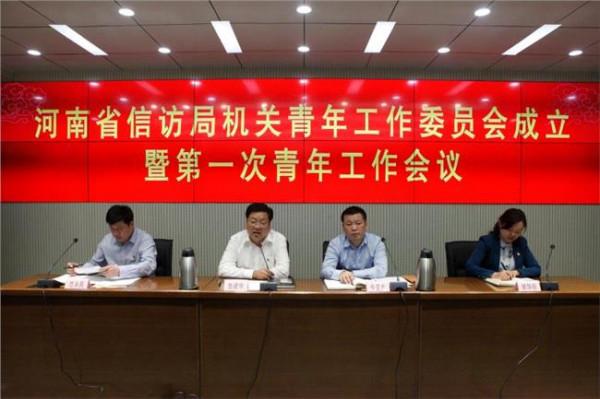王稼祥四十 特稿:访王稼祥的孙子、十一届民盟河南省委委员王光龙(图)
王稼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1925年参加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因其关键的一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旗帜鲜明地反对成立人民公社;在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他就我国的外交政策大胆建言,被康生等人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遭批斗和关押。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闻知“批林批孔”运动即将开始,忧心国民的王稼祥心力交瘁,当晚溘然而逝。
祖父的词典里没有“妥协”二字——访王稼祥的孙子王光龙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王光龙除了民盟河南省委委员这个“政治身份”之外,与许许多多的大学教授一样,平易质朴中带有岁月涵养出的书卷气,除此之外,并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至于他的另一个“身份”——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王稼祥的孙子,却一直鲜为人知。
也许正是他的这种低调,使得我们的采访并不顺利,几次电话沟通,他均表示事务繁忙,暂不能接受采访。直到半年后的一天,他才打电话给我们。
2012年盛夏,河南郑州。正在参加民盟河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郑州大学教授、十一届民盟河南省委委员王光龙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见到我们,谈起延宕至今的采访,刚刚卸任民盟河南省委委员的王光龙说:我现在可以心无挂碍地面对媒体讲一讲我的祖父王稼祥了。怕我们不解,又言:祖父是一个低调的人,我们多年来没有面对媒体谈他,是不希望别人以为我们在拿祖父沽名钓誉。
现在我不再担任民盟省委委员,而且也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是时候讲讲我祖父了。言谈之间,记者发现,他的相貌与祖父王稼祥很像:一样瘦高的身材,一样清癯的面庞,甚至在沉默的时候,脸部的神情都与照片上的王稼祥有几分神似。
话题打开,他坦言道,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祖父一生经受过无数政治斗争的磨砺和生死考验,但他对人生起伏的淡定,对理想信念的执著,对错误决策的不妥协,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世人所理解。他说,我愿意用我的所见所闻,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王稼祥。
面对满屋的大字报,祖父淡定而认真地阅读
出生于1951年的王光龙,尽管青少年时代是在祖父王稼祥的身边度过的,但当时的他并不了解祖父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一切。原因一是他年纪小,二是祖父从不跟他们提及自己的事情。
在他的记忆里,祖父沉默寡言,偶尔会问一问他和哥哥的学习情况,也会跟他们玩耍一会儿,但话很少。以至于多年后,当王光龙了解到祖父的过往的时候,他甚至对记忆中的祖父产生了误读:那些事情真的发生在祖父身上了吗?然而历史确实是这样书写的:
——1935年1月15日,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旨在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这便是“遵义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一味强调失败的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红军“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回避自己在指挥方针上的错误;毛泽东则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以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并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更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一时间,两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起身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改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这样,王稼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使得正确意见迅速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上风。最终,会议成功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
从此,中国革命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事后,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这样说道:“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1958年 “大跃进”时,王稼祥提醒大家注意苏联公社垮台的前车之鉴。但此时,人民公社已一夜之间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在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的人民公社”有意见后,毛泽东批评他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1962年,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针对当时的外交政策,王稼祥又泼了一盆“冷水”。
他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信说,应争取时间渡过难关,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
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同时还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一次,王稼祥被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大帽子,遭到批斗。其政治生命由此走到尽头。
对祖父的解读,是王光龙成年后经常做的功课。从不理解到理解,王光龙说他读出了外表沉默的祖父内心的执著与强大。
《名人传记》:从您出生到祖父去世,跟祖父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王光龙: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刚从苏联回来,正在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时我们就住在中联部,和祖父在一起生活。1956年年底祖父任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候家就搬进了中南海怀仁堂的东三院。
那时我已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平时和父亲住在人民大学的宿舍里,星期天回家和祖父团聚。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们全家从中南海搬到北海后门的一个小院子。那里原来是蒙古的使馆,隔壁是郭沫若家。
两院之间的墙不高,在二楼可以看到郭家,我发现郭沫若的家很大,至少比我们的家大一倍,院中还有假山和亭阁。1968年年底,我和哥哥到山西汾阳插队,从此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祖父。
《名人传记》:在您的记忆中,祖父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留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王光龙:祖父不爱说话,面部表情也不丰富,很少会喜形于色或怒形于色。所以多年后我看到有人写祖父时,用到“悲痛万分”或“兴高采烈”这样的词句,感到很可笑,那可能是一种文学化的想象吧。事实上,我们很少能通过祖父的面部表情来获知他内心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
当我和哥哥年纪很小的时候,有时会缠着祖父说这说那,祖父总是耐心地听我们讲,从不会打断我们的话,但他很少主动与我们交流。从小祖父最疼爱我,用母亲的话说,我等于家里的老大,哥哥只能排在我后边。
记得有段时间他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在院子里散步半个小时,每次都由我陪着。散步的时候,我看到或听到什么新鲜事就向他一一讲述,也会提出一些问题。他总是静静地倾听,需要回答时给出的答案也非常简洁明确。在我的印象中,祖父常常处于思考状态中,尽管话很少,但看得出他的大脑从来没有停歇过。
“文革”开始后,祖父因为之前说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受到冲击。那是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祖父给中央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正确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
孰料因言获罪,祖父由此被定为“走修正主义路线”,并被批斗。当然,这些事情对于年幼的我来说是很难弄明白的,只是不断看到中联部的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我家,才在恐惧中感到祖父出事了。
那个情景我终生难忘。记得当中联部的造反派将批判祖父的大字报送到家的时候,祖父显得异常平静。大字报将我家客厅的四面墙壁贴得一点空隙都不留。祖父竟然站在大字报前仔仔细细地看上边的内容,一边看一边思考,那份平静与认真,就像平日里阅读文件,又好像战时在军用地图前研究军情,一连几天都是如此。
那时的我并不理解这一切,不知道祖父这样做需要怎样的信念和勇气,但我看到了祖父的淡定。
《名人传记》:对于祖父在“文革”中的遭遇,今天回过头去看,您有什么感想?能理解吗?
王光龙:人们都说性格决定人生,我觉得这句话放在我祖父的身上非常合适。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祖父没有被很多声音所左右,当众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为毛泽东说话,用决定性的一票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
在当时,祖父那样做是很不容易的,是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大跃进”中,在无数人为人民公社的成立欢呼雀跃的时候,他又对人民公社投了反对票;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祖父提出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事实上,在当时国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祖父建议对外援助务实一点,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一点,是非常必要的,结果却被批为“三和一少”。
祖父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为什么不能与主流声音保持一致,从而为自己和儿孙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呢?对于这些我是渐渐才明白和理解的。祖父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不合时宜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但他就是那样的性格,淡定中有执著。为了信念和真理而不屈于权威,不会因为任何变故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温饱足矣,祖父对生活的要求是低标准
王稼祥对生活的要求标准很低。王光龙对祖父的睡衣之破旧是眼见为实的:睡衣穿久了,布料就不结实了,有洞或裂缝的地方,都补着补丁,而且补丁越补越多。这件睡衣在王光龙的眼里始终如此,看久了反而觉得祖父的睡衣就应该是这样的。
睡衣只是一个细节,在王光龙少时的记忆中,家里的生活质量并不比普通老百姓高许多,祖父的一些特殊待遇家里的其他人是不能享受的。这样的生活经历,培养了王光龙的平民意识,也为他日后经受生活的考验打下了基础。
《名人传记》:您出生的时候,祖父正身居要职,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在一般老百姓看来,应该是养尊处优的,您当时有没有一种优越感?
王光龙: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有司机和警卫,但那都是为祖父服务的,和我们无关。我每天上学放学,和班里的其他同学一样步行往返。所以不管是在心理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我都没有感觉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也谈不上有什么优越感。
我在人大附中上学的时候,学校离家比较远。记得有一天早上我起晚了,担心坐公交车上学会迟到,母亲犹豫再三找到祖父的司机,问能不能用祖父的那辆吉姆车送我到学校。司机不假思索就拒绝了,他说,首长规定不许自己家人用公车,我们绝对不敢违背他的意思。在我的记忆中,这辆车从来没有为家人办过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