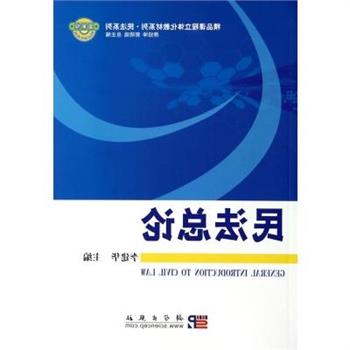郭明瑞的老婆 郭明瑞:关于民法总则中时效制度立法的思考
时效制度的构建不仅要注意各种时效之间的协调、衔接,还要注意各时效制度内的各项规则的协调。
从各国立法看,无论在总则中如何构建时效制度,诉讼时效(消灭时效)制度都是立法的重点。诉讼时效制度如何构建既涉及其适用范围,也涉及时效期间的计算等各项规则。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既涉及何时开始计算时效期间的开始,又涉及时效期间开始计算后发生障碍时如何处置。
就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而言,现行《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该条规定的起算日期,学者中就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该日期为权利人之救济请求权产生之日;另一种理解是该日期为权利人之救济权可行使之日。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理解上的不同,与该规则的设计不够明确不无关系。《民法总则草案》对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规则作了修正,在第181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开始计算。
”这一规定显然是以权利之救济请求权可行使之日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这就可避免发生不同的解释结果。
现在的草案中还对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作了特别规定,如第18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算。
”第184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算。”这些规定不仅使诉讼时效制度与监护制度相协调、衔接,而且使时效期间的起算与诉讼时效的价值相协调。值得肯定。同时,笔者认为,在诉讼时效制度内部规则的协调上至少还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后,在时效进行过程中会发生一些法定的事由,致使时效不能按期完成。此在理论上称为诉讼时效进行中的障碍,包括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
所谓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在有法定事由发生时,此前已计算的时效期间全归无效,待中断事由消灭后时效期间重新计算。[12]依王利明教授的看法,诉讼时效中断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时效的中断使已经进行的时效期间从法定事由发生之日起重新起算。
”[13]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现行《民法通则》规定为三项,《民法总则草案》第188条规定为4项,即:(1)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2)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3)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4)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草案的这一规定与他国的立法规定以及传统的理论观点基本一致。但是,这些事由是否都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并不无疑问。一项事由能否将其归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关健在于发生该事由时时效期间可否会重新计算以及能确定从何时重新起算。
《日本民法典》第157条规定,“(1)中断的时效,自其中断的事由终止时起,重新开始进行。(2)因裁判上请求而中断的时效,自裁判确定时起,重新开始进行。
”关于因起诉而中断时效的起算,我国学者的表述虽有不同,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例如,王利明教授认为,一旦提起诉讼便发生时效的中断,但由于诉讼本身有一个过程,时效中断后,诉讼过程都就被视为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持续状态,所以,因起诉引起时效中断,新的时效期间应从诉讼过程结束时重新计算。
[14]梁慧星教授指出,属于提起诉讼、提起仲裁、申请调解或向有关机构或机关要求保护民事权利等原因而致中断的,应从判决、裁定、裁决或调解协议生效或有关机构或机关作出决定之时起,重新计算时效期间的。
[15]笔者也一直是持同样观点的,认为“因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而中断诉讼时效的诉讼时效应自诉讼终结或者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裁决之日重新计算”。
[16]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并不准确。马俊驹教授曾指出,在法院作出裁判之后,当事人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行起诉,而只有所谓的强制执行期限问题。
[17]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审结后即会进入执行程序。《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该法第23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这些规定表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而进入诉讼程序或者仲裁程序后,则不会发生诉讼时效期间的重新开始计算,而只会发生申请执行期间的计算,尽管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但也正说明申请执行时效是与诉讼时效是不同的时效。
由此可见,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虽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但若诉讼申请或仲裁申请经受理而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的,则不会有诉讼时效期间的重新开始,诉讼时效不是发生中断,而是终结。
所以,笔者建议,在《民法总则草案》第188条中应增加一款,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经受理而进入诉讼程序或者仲裁程序的,诉讼时效期间终结。”
诉讼时效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确定其适用范围,即诉讼时效适用于何种权利,不能适用于何种权利。
关于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也称为诉讼时效的客体,学者中通常表示为请求权。但如前所述,依现行《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草案》的规定,笼统地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并不准确。我国民法上的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请求保护的权利。这种请求权为救济请求权,它与德国法中的请求权及日本法中的债权和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的含义及范围并不完全相同。
依我国法,权利人请求保护其权利的请求权受诉讼时效限制,但由此认定凡权利保护的请求权都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是不合适的。权利的属性不同,法律对其保护也应相应不同,因此,对于某些权利救济请求权是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即权利人请求权利救济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民法总则草案》第190条对于不适用诉讼时效情形的作了规定。依该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1)请求停止侵害、排除障碍、消除危险;(2)登记的物权人请求返还财产;(3)请求支付赡养费、抚养费或者扶养费;(4)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关于前三项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正当性,王轶教授有较详细阐述[18],可值赞同。对于第四项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应包括哪些呢?法律在规定某项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时应如何考量呢?这值得研究。
笔者认为,首先,对于人身权的保护则不应有时间限制,因为人身利益不应因时间的推移而丧失,且如若人身利益受时效的限制而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他人通常也并不会因此而取得该人身利益。
[19]所以,笔者曾提出法律应明确规定,权利人请求保护人身权的权利(包括在知识产权中享有的人身权利)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除外。
因此,笔者建议民法总则草案第190条在不适用诉讼时效请求权中应增加 一项“请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及赔礼道歉”。其次,权利人请求权利保护关乎其基本生存权利的,该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草案中规定的支付赡养费、抚养费或者扶养费的请求权,即属于这类请求权。
此外,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请求权也属于此性质的请求权,也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再次,权利人请求保护权利,涉及对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该项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
例如,交付物业费的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因为这一权利的行使涉及其他业主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物业管理公司的事情。笔者认为,对于这三项请求权,有必要在草案第190条的例外规定中予以明确,而不应交由(四)项这一兜底性条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