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臣单口相声 张寿臣传统单口相声《渭水河》文本
那位说:“你们久干这个的还能说忘了,说错了?”这可保不齐。无非是我们说相声儿的要说忘了不老显的。为什么哪?相声原来是招笑儿的,忘了哇,观众们不说是忘啦,说这个:“哈哈,张寿臣哪,为招大伙儿一乐,他成心装的。”其实倒是真忘啦。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推一辈子小车儿没有不翻车的。变一辈子戏法儿碰巧也许变露啦,上台表演的时候撒手不由人。说这手戏法儿是功夫,今儿赶巧了啊,一抽筋儿,就许错了,这可保不齐!”
唱大鼓哪?唱大鼓也有忘了的时候呀。说:“我们常听大鼓,没听见他忘过啊?”他忘了啊您不理会。我告诉您这地方儿您注意,一有这种地方儿,那就是忘啦:他唱完一个“甩板儿”,就是行腔儿,行完了腔儿呀,.
弦子弹过门儿,打鼓,把这鼓套子打完了,张嘴就唱,那是没忘。有这时候儿:这鼓套子打完了哇还接着打,那就是忘啦。打两回鼓套子,有这俩鼓套子的工夫想词儿,就想起来啦。有这时候儿:只要忘了词儿就着急呀,一着急脑袋就大啦,就更想不起来啦,要再连着打鼓套子,打仨,观众们就听出来啦,要一叫倒好儿多寒碜哪?这时候就得弹弦儿的帮助他。
他已经打了俩鼓套子啦,还要打,这弹弦儿的就不能让他再往下打啦。
这弹弦儿的跟他说话可不成,怎么?小声儿说他听不见---脑袋都大啦;大声儿说,他倒听见啦,可观众也听见啦,这么一来,倒给泄了气啦。那么怎么办呢?弹弦的一听已经打俩鼓套子啦,这弹弦儿的手指头一使劲儿就行啦,就帮他的忙啦。
怎么呢?手指头一使劲儿,奔儿!弦就断啦,弦一断就不能唱啦,他得接弦呀。他这一接弦,唱的人放下了鼓板,喝口水,松快松快,脑筋去点儿负担,一低头,俩人一嘀咕,这就成啦。
唱大戏也常有忘词儿的时候。大戏里头有些不通的词儿,有错了的词儿。这种词儿有打原本儿上就错了的,这不能怨演员,得怨编戏的人。这怎么回事呀?旧社会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唱戏的人多半儿是文盲,打七八岁就进科班儿,他哪儿有工夫念书啊?本子上的词儿抄得太糙,里头有不少错字,教戏的也是演员出身哪,文化水平太低呀,也就按错的念,一辈传一辈,就那么传下来啦。
戏里常有这句词儿---“阳世三间”,这是大错。
“阳世三间”怎么讲啊?!“阳世”俩字有讲儿,阴间阳间嘛!这“三间”哪?这“阳世”上就“三间房”,连三间半都没有?那么多人往哪儿住哇?!
那么是怎么回事呀?抄本子的时候快,那个人一边说词儿他一边儿抄,是“阳世之间”,那个“之”字呀连着笔下来啦。
等到别人再念这个词儿呀,他不认得这是连笔写的“之”,就念成“三”啦,把“阳世之间”念成“阳世三间”,就这么传下来啦。
《乌龙院》,阎婆惜给她妈妈做红鞋穿,宋江问她为什么做
红的?“马二娘的生日。”阎婆儿她不姓马呀,阎婆借怎么叫她马二娘哪?那是那个“妈”字儿,也许当时写得快,没写“女”字旁儿.也许当时写了“女”字旁儿,后来念本子的人不认得,就念成“马”啦!这句话原本是“妈妈娘的生日”。“妈妈娘”头一个“妈”字本来就不清楚,这个“妈”字底下点了两点儿,是“妈:娘”,这位教戏的教师不认得,就认为是
“马二娘”啦!
这些个错儿呀不是演员的错儿,这是抄剧本的和教师的错儿。
唱戏的演员哪,精神不集中就出错。有这个事吗?我亲眼见过几档子,咱不必提他的名儿,就提这件事吧。这件事出在北京,这天演《问樵闹府·打棍出箱》这出戏,有这么个演员给唱错啦,还是个名角儿呀。哪点儿错啦?范仲禹一出场,唱:
“适才樵哥对我论,那老贼名叫葛登云。”
“适才樵哥对我论”,这句唱得挺好,“那老贼名叫”这几个字也唱出来啦,到“葛登云”忘啦,把这个人名儿给忘啦!这接不下来呀,怎么办呢?他会让听戏的听不出来。怎么呢?忘是忘了,可脑筋清楚,心里头明白,在台上掉了能捡。一出门儿:“适才樵哥对我论,那老贼......”
忘啦!怎么办哪?心里头清楚,他这仨手指头这么一凑合,听戏的不知道,内行都知道,这叫“掐”,鼓也不打啦,.弦儿全都不动啦。他这儿哪?加两句道白。原本这儿就是唱没有白呀,他加了两句白:“……那老贼……呜呼呀,适才那樵哥对我言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老贼的名字,怎么一时之间我想他---不起!”
你忘了嘛,你还想得起来!他倒说实话!
到这儿一投袖,投袖干吗呀?又把家伙叫起来啦。叫什么家伙哪?叫“乱锤”,呛呛呛......就这个点儿。这干吗呀?他在台上低头摸脑袋,想这个人的名字。
“这......”在台上转弯儿。转了半个过场,跟这打鼓的接近啦,问打鼓的:“叫什么来着?”
这位打鼓的跟他玩笑,拿着鼓槌儿:“哎呀,我也想不起啦!”
“哎呀,不凑巧哇!”
转了四个弯儿:“嗬嗬,想起来了哇!”
那还想不起来!转了五分钟啦还想不起来!仗着当时机灵快,没让人听出来。
还有这么档子事,别人在台上闹笑话儿,他给找回来啦。谁呀?杨小楼。这出戏呀配角唱错了,他把这错儿给找回来啦。什么戏呀?在北京第一舞台演《青石山》,杨小楼去关平,钱金福去周仓。钱金福那天有点儿事情,告假。临时一告假怎么办哪?就叫别的花脸替啦。这位唱花脸的呀,早晨给人家出份子去啦,喝了好些酒。一听钱老先生告假,后台老板说:“你来这个啊!”别的戏他不能唱啦,他得陪杨小楼唱这出《青石山》哪,在后台呀,他老早就把脸儿勾上啦,扮好了装,靠大衣箱往墙上一倚,先眯个吨儿。他眯吨儿的时候可没戴着胡子---周仓戴那个叫“黑扎”呀,他没戴。心说:“等上台再戴吧。”他这一睡睡着啦,大伙儿也没叫他,容他睡到演这出戏的时候才叫他:
“哎,上台啦,上台啦!”
“哎,哎!”
醒啦,迷里迷瞪就上台啦,还是没戴胡子。
他没戴胡子,后台没瞧见,看戏的也没瞧见。观众怎么也没瞧见哪?那阵儿唱《青石山》台上有个大幕,王老道捉妖请神仙在幕外头。幕后头是摆场子—摆的这场子正跟老爷庙一样,中间是关公,这边儿是周仓,这边儿是关平,还有四个武行扮的马童儿,没拉开幕这些人得在那儿准备着,各人站到各人的地位上;等到一把送神火,王老道一喊:“开山!”把幕一扯,观众一瞧正是老爷庙---“开山!”幕一拉,听戏的都往台上看。
“哎!什么戏呀?”
旁边那位说:“《青石山》哪!”
“《青石山》?不对呀!这是谁呀?”
“周仓啊!”
“周仓怎么刮脸啦?!”
大伙儿都瞧。
杨小楼捧着印往那边儿一瞧:坏啦,他没戴胡子!头里一起哄,一叫倒好儿怎么办!杨小楼灵机一动---原本这戏里没有这句,他给加了句词儿:
“呔!对面站的何人?”
周仓这儿扶着刀,心说:“这什么词儿呀这是?戏里头没有这句呀,你怎么添这个呀?再说你忘了题啦,你怎么不认得我,让我通名哪?咱俩人是伙伴儿呀,周仓、关平啊,老爷庙这儿就咱们仨人哪?天天脸对脸儿站着,你怎么不认得我呀?我是周仓啊!到这儿说“我是周仓”不行,得摆身段,戏台上嘛!摆身段的时候儿拿手捋胡子:
“俺是周仓......”他这么一捋呀,没逮着,这才明白:哎
哟,没戴着!可已经把周仓说出来啦,再说别的也不成啊,他的灵机也快,一攥拳头:“......的儿子!”
杨小楼那儿:“嗐,要你无用,赶紧下去,唤你爸爸前来!”
“领法旨!”
周仓下去戴好了胡子,又上来啦。
出这种错儿,哪儿都有。那年哪我在河南---这话民国十来年---在河南开封听河南梆子,河南梆子闹错儿啦。什么戏呀?这出戏叫《黄河阵》。咱们这地方不常唱这个戏。《黄河阵》是怎么个剧情哪?是武王伐纣,姜子牙带着八百诸侯走到半道儿,出来一个赵公明。赵公明摆了一个阵,挡着武王的大队不让过去,这阵叫“黄河阵”,很厉害。姜子牙打不开,正着急娜,燃灯道人来啦。燃灯道人跟赵公明俩人是道友,一见面儿哪,劝劝。赵公明不说理,说什么我得摆这个阵,你来啦,你打打我这个阵。俩人越说越戗啊,打起来啦,就这工夫儿,唱错啦!
原来俩人都是朋友嘛,都下了脚力---就是骑的牲口。赵公明骑黑虎,燃灯道人骑梅花鹿,赵公明把马鞭儿放下,好比这是黑虎;那边燃灯道人把马鞭放下,好比下了梅花鹿啦。俩人说着说着打起来啦,一打,他得上自己的脚力呀,这儿有两句唱词儿,唱词是什么哪?这边儿:“赵公明把黑虎跨”;那边儿哪:“燃灯道人上梅花”,俩人打起来啦。
这赵公明闹错啦,头一句他唱:“赵公明,骑梅花。”
他把梅花鹿骑上啦!回头燃灯道人再骑梅花鹿?就俩梅花鹿!燃灯道人没词儿唱啦,他给来了这么一句,一指赵公明;“你骑梅花我骑啥?”
你骑梅花鹿,我骑什么哪?
赵公明不错,还算有词儿:
“我的老虎你骑吧!”
俩人换换!燃灯道人唱:“我骑老虎我害怕。”
那这出戏还怎么唱啊!
我二十来岁那年哪,在北京,梆子正时兴,金钢钻儿,小香
水儿呀,他们在三庆戏院表演。谁闹错儿呀?开场戏。可不是名角儿。哪出戏?《渭水河》。这位演姜子牙的闹错儿啦。原词儿是这么几句:“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叫飞熊”,这么个词儿。他呀,把“道号叫飞熊”忘啦!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唱到这儿忘
啦!落不下腔儿来,这儿也不能行腔儿呀,没词儿呀。没词儿怎么办?还重这句:“字子牙......”
胡胡儿,“冬龙根儿龙。”还想不起来:“字子牙......”
唱了五六句,台头里一听:“怎么回事啊?”有位挨着台的观众给他来个倒好儿:“好!”
这一叫倒好儿哇,他跟这位一对眼睛:“你别叫倒好哇,我想一想啊。”他嘴里可不能住,老这句呀;“字子牙......”胡胡儿:“冬龙根儿龙。”又一位观众:“好!”
“字子牙......”
“字子牙......”
谁叫好儿,他冲谁“字子牙”,来了二十多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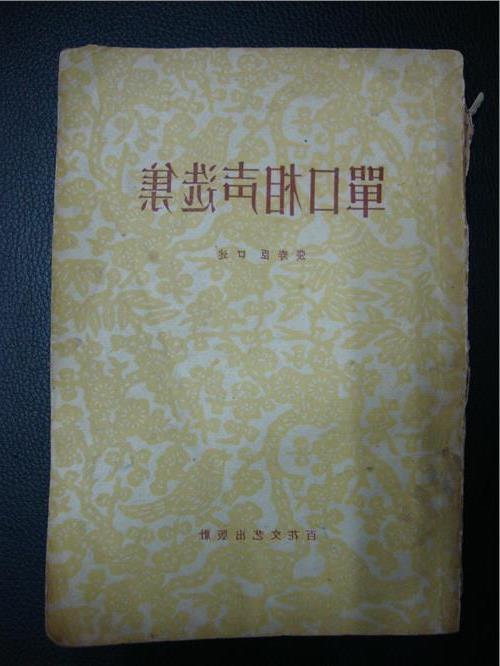



















![>张寿臣]张寿臣单口相声全集](https://pic.bilezu.com/upload/3/31/331b1bcb1ee644f38ad73a0143262d01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