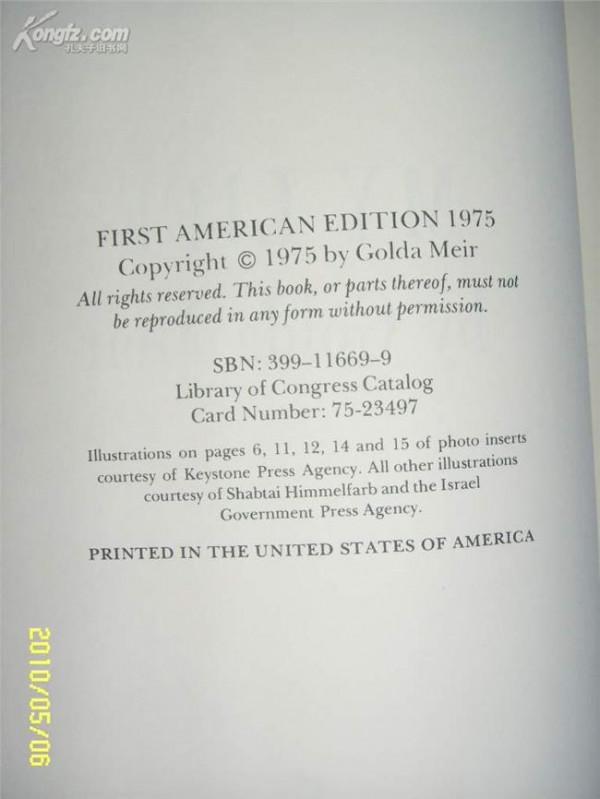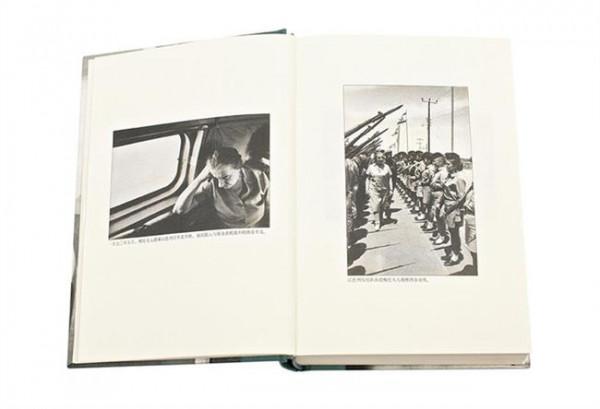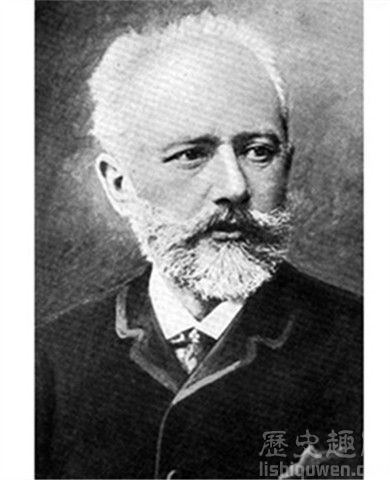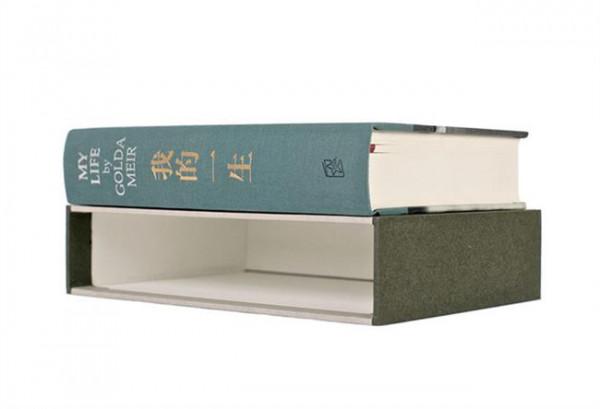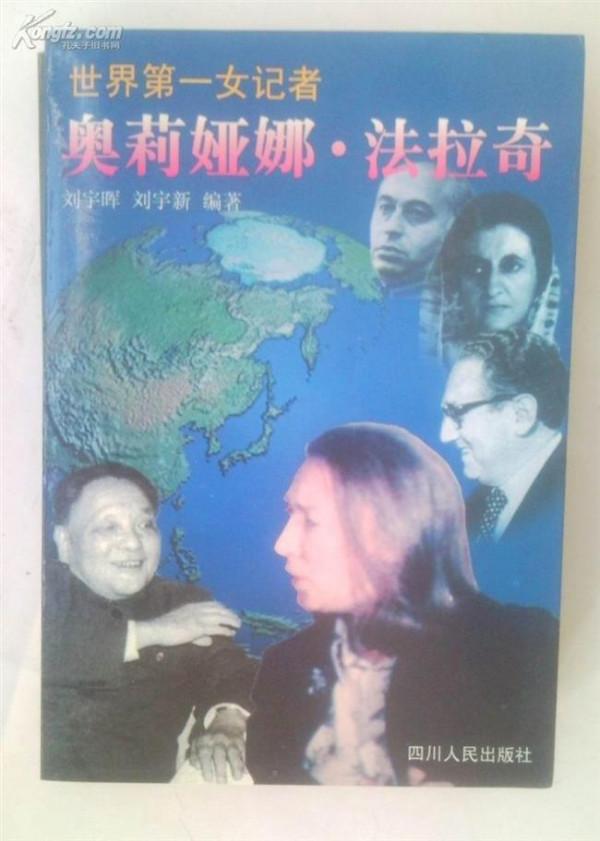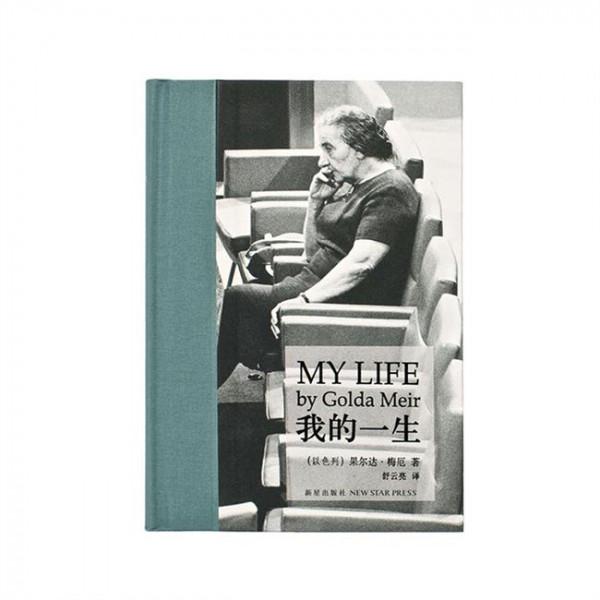我的一生:梅厄夫人自传(精装)
这本书里提及的所有事件,没有哪件像一九七三年十月的赎罪日战争那样使我难以下笔。但战争发生了,所以它是这本书的一部分,但不是作为一篇军事记录——那我留给别人去写,而是作为我亲身的经历并将永远伴随着我的一个近似灾难和噩梦的记忆。在国家的最紧急关头,我感觉自己肩负着无限重大的责任。
即使是作为个人的经历,也有许多东西是不能透露的,而我写下来的东西也远远不是确定无疑的。但这是我在战争过程中的真实感受和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这是建国二十五年以来第五次强加给以色列的一场战争。
有两点我必须马上说明。第一点,我们打胜了赎罪日战争,我深信,在叙利亚和埃及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尽管初期他们有些斩获,但最终又被打败了。另一点是,全世界,尤其是以色列的敌人,都应该明白,使两千五百名以色列人在赎罪日战争中阵亡的情况,将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战争是十月六日开始的,但现在回顾这场战争时,我的思绪追溯到五月份,当时我们接到情报说,叙利亚和埃及在边境地区大量增兵。我们的情报人员认为,不大可能爆发战争,但我们还是决定认真对待此事。那时候,我还亲自去了一趟国防军总司令部。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和总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全国上下都知道他的外号叫“护墙板”)就全国武装力量的备战情况向我做了简单的汇报,我深信,部队已经能够应付任何紧急情况,即使是全面战争。对于充分和及时的预警问题,我也感到放心。然后不管怎么说,紧张的气氛缓和了。
九月,我开始接到有关叙利亚军队在戈兰高地集结的情报,九月十三日,我们与叙利亚发生了一场空战,结果叙利亚的十三架米格战机被击落。尽管如此,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是很自信。他们说,叙利亚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应。但这次的紧张气氛继续存在,而且扩散到了埃及人那里。
我们情报人员对局势的评估依然如旧。他们解释说,叙利亚继续增兵,是由于叙利亚人害怕我们会发动攻击,于是整个九月份,包括我去欧洲的前夕,对叙利亚军队动态的这种解释一再重复着。
十月一日星期一,不管部长伊斯雷尔·加利利打电话到斯特拉斯堡找我,说完别的事情之后,他告诉我他已经与达扬谈过了,他们都认为等我回来后要马上讨论戈兰高地的局势。我告诉他说,我第二天就回来,第三天我们可以碰头。
星期三快中午时,我会见了达扬、阿隆、加利利、空军司令和埃拉扎尔,还有军事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因为情报局局长当天生病,国防部长达扬主持会议,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两条战线的情况。他们都为某些情况而感到不安,但军事分析还是认为,我们不会面临叙利亚和埃及联合进攻的危险,而且叙利亚不大可能单独进攻我们。
南方的埃及军队的集结和运动,很可能是每年那个时候举行的军事演习;在北方,部队的增兵和重新布置还是如同之前的解释。
几支叙利亚部队一星期前从叙利亚一约旦边境转移,则被解释为两个国家之间最近的一种缓和,也是叙利亚对约旦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会上没人提出有必要动员预备役军人,没人认为战争正在逼近。但会议决定,在星期天举行的内阁会议议程中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星期四,与往常一样,我去了特拉维夫。多年来,周四和周五我一直是在特拉维夫办公室工作的,周六是在拉马特维夫的家里,然后是周六晚上或周日一早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周似乎没有理由要改变这种模式。实际上,这个星期很短,因为赎罪日要在周五的晚上开始,以色列的大多数人要度过一个较长的周末。
我想,部分是由于这场战争,即使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赎罪日的非犹太人,现在也知道这是犹太日历中最庄严和最神圣的日子。一年中的这一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即使不是很虔诚的,都会以某种仪式聚集在一起。虔诚的犹太人是完全不吃不喝不工作的,并在犹太教堂里度过赎罪日(像安息日和犹太教的所有节日一样,赎罪日是从当天晚上到第二天晚上结束的),进行祈祷并赎回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可能犯下的罪过。
其他的犹太人,包括实际上并不守斋戒的犹太人,则常常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纪念赎罪日,他们不工作,不在公众场合吃东西,在赎罪日前夕去犹太教堂,即使只有一两个小时,去听祈祷开始时的大提琴和管弦乐演奏《一切誓约》,或去欣赏标志着节食结束而吹响的羊角号。
但对于各地的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不管他们如何遵守习俗,赎罪日是不同于其他任何日子的。
在以色列,这一天全国的活动几乎都停顿了。对犹太人来说,这一天没有报纸,没有电视广播,没有公共交通,所有的学校、商店、饭店、咖啡馆和办公楼都关门二十四小时。然而,在犹太人看来,即使赎罪日也没有生命本身更为重要,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因此,所有的公用设施都是照常运转的,虽然许多单位在那二十四小时里只安排了最低人数的值班人员。
不幸的是,以色列最基本的公共事业是军队,但这天军队也给尽可能多的战士放假,让他们回去与家人团聚。
十月五日星期五,我们收到的一份报告使我开始担忧。叙利亚苏联顾问团的家属在收拾行李仓促离去。这使我想起六日战争前夕发生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消息。为什么这么仓促?苏联人的家属知道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他们是不是在疏散?在送进我办公室所有的杂乱情报中,这个小小的细节在我的脑海里扎了根,怎么也摆脱不了。
但由于我身边的人似乎都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我也尽量不去多想。此外,直觉是很微妙的,有时候应据此立即采取行动,但另有时候这只是一种焦虑的症状,那就会给人以很大的误导。
我去问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情报局长,他们是否认为这份情报很重要。不,这丝毫没有改变他们对局势的评估。我得到保证,如果有真正的麻烦,我们是会得到适当的预警的。而且不管怎么样,足够的增援部队正开赴前线,以便在必要时开展堵截行动。
一切必要的备战工作都已经完成,军队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是空军和装甲兵部队。情报局长离开我之后,在廊道上遇到了卢·卡达尔。后来卢告诉我,他拍了拍她的肩膀,微笑着说: “别担心。
不会有战争的。”可我还是担心,而且我不理解他对一切平安无事那么肯定。如果他错了怎么办?如果有一点点战争的可能性,我们至少应该征召预备役兵员。不管怎么说,我想至少要召集那些在特拉维夫过赎罪日周末的内阁部长来开一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