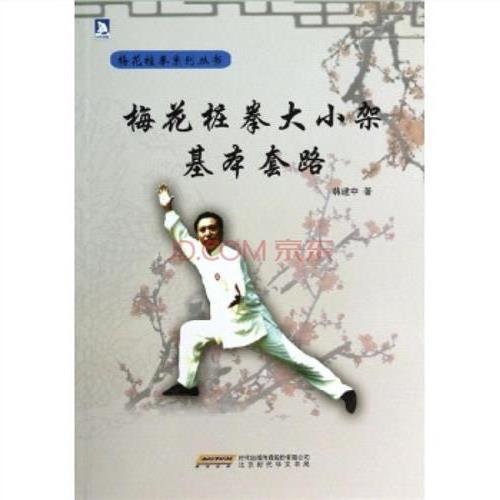惠英红:走到现在,是我不幸中的有幸!
首先恭喜红姐凭借《幸运是我》拿下第三个香港金像奖影后...
半年前,《幸运是我》公映,橘子君幸运的和红姐聊了1个多小时,坦白来讲,那是橘子君做的最舒服的一次访问,聊到最后,记者对红姐说:“我看过电影(《幸运是我》)了,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准备明年金像影后的获奖感言了。”红姐笑着摇摇手:“不了,不了,我已经很幸运走到现在了。”但又小声的补了一句:“真的能拿吗?”。
红姐的故事太长,这篇采访只能碎片化的给你讲惠英红的故事,比起电影,她的前半生可难多了...
以下是采访原文:
“你好,我是惠英红。”
头发简单的扎起来,妆容极其清淡,白色刺绣的短裤,显得她格外娇小,她怕冷,走路有点僵直,采访过程中,明明记者都已经感到采访间很热了,惠英红仍把一个毯子盖住双腿,手里捧着一个热水瓶,“这是老病根了,因为我腿的关节不是很好,不能受凉。”这是武打演员的通病,治疗了好几年,已经算“好多了”。
虽说是两届香港金像奖影后,但惠英红不会让你产生任何距离感,见到记者,惠英红主动问好:“你好,我是惠英红”,当她向你微笑时,你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女侠的感染力与气魄。
聊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开始进行采访,由于采访过程中要拍照,惠英红自己拿起化妆镜,开始化妆,这让记者极其意外:“你没有化妆师吗?都是自己画吗?”
“又不是多难的事情,为什么要麻烦别人呢。”惠英红淡淡的说。只见她直接上粉底,打阴影,画眉毛和眼线。接着,把头发从发根一绺一绺别后面,最后检查一遍,确保灯光下不会出现一点毛躁。
化完妆,56岁的惠英红放下化妆镜。瞬间,一个精力充沛和表情饱满的惠英红出现在记者的眼前,这和记者当年透过电视看到的她别无二致。
这次惠英红带着新作品《幸运是我》来内地宣传,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惠英红有可能第三次问鼎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之作。再此之前,惠英红拿过第一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29年后,又第二次拿下金像影后,之后,她还拿过一次香港金像奖女配和金马奖女配。
当谈起自己的成功,惠英红把这一切都归结到自己的“苦难”。
“他们都觉得我太可怜了,也愿意给我钱”
惠英红1960年出生在山东一个家底颇为殷实的家庭,惠家有8个子女,惠英红排行第五。文革时处境危急,惠英红的父亲带着妻妾子女迁居香港,刚开始,家里经济条件还不错,后来惠英红的父亲迷上赌博,把家底几乎都输光了。
家道中落后,家里还发生了一场大火,姐姐为救出她和妹妹,遭到毁容并且失明,排行第五的惠英红就成了长女,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晚上,惠英红的妈妈带着孩子们到酒楼拿剩菜回去吃,白天,惠英红要去湾仔区乞讨,“当时打越战,很多美国水兵、英国水兵会来香港度假,我妈就让我去那里,把一些纪念品、口香糖、扑克牌和筷子,卖给那些水兵。一般来说,水兵通常都会买的,有时他们也不需要这些,买是因为觉得我很可怜。”
乞讨的时候,惠英红学会一种伎俩,为了能赚到更多,只要在路边见到外国水兵,她会一个健步跑过去,直接坐在地上抱着水兵的大腿,但这样做会有一个误区,她经常被打,会被一脚踹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时间长了,惠英红明白:“美国水兵比较有钱,会很大方,所以不要去抱英国水兵”,这让惠英红从小就有了察言观色的能力。
在惠英红的记忆里,湾仔有时会像一个天堂,有时会像一个地狱。“我曾经在这条街上认识一个非常好的Bar girl ,她每次看到我,都会叫她身边的老外给我很多小费,因为大家都很苦,她也很懂我,但她吸毒,吸白粉,有一次我站在街角对面和她打招呼,结果她就突然死在我的面前,像个木偶一样倒下了,没有家人收拾她的尸体,警察就直接把拽着她的胳膊,把她拖走了。”
这是惠英红第一次感受到生死,那一年,惠英红才6岁。
“我为什么要当打女,因为没有人做打女”
在湾仔乞讨的时候,惠英红看到电影院外张贴的明星海报,就立志要做明星,在她的意识里:“明星可是人上人!”离开湾仔之后,惠英红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夜总会跳中国舞,“因为我知道当时女演员很多都是在夜总会被星探发现的。”这一点,她十分确信。
可到了夜总会后,惠英红发现自己必须要做上领舞,才有可能让更多人看见自己。“一场节目只有一个领舞,20个多演员,每个演员都想当领舞,这怎么办,那你就要拼,要吃苦,这样你才能走到前面来!”
但总吃苦是没有用的,还要有门路。惠英红记得,当年大家都喜欢看报纸,报纸上经常会有招演员,正好李翰祥导演的《红楼梦》在招演员,惠英红去影楼照了几张照片,花了5块钱,这对当时的惠英红来说已是天价,照片洗出来之后,惠英红根据地址又写了一封信寄了出去,但没有任何人回复她。
过了一段时间,午马导演无意中看到正在台上表演的惠英红,就跑到后台问惠英红的主管能不能让她去演戏。“我当然愿意了!”惠英红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其实,导演是要找江南七怪里面的梅超风,但试镜后,导演让我演了穆念慈,那可是女二。”
第一场戏是穆念慈的爸爸被抓进监狱去,惠英红哭得像个泪人,这让导演张彻十分意外,“他以为我拍过很多戏,还问我:‘你拍过很多戏吗?’我说‘不是啊’。他没想到我能做到说哭就哭,要多惨就多惨,其实,这些我都经历过。”
在当时,武打片是主流,而武打片基本以男性为主,“打女”是没有的,所以,惠英红不得不去做打女。
“我为什么能一开始做第一女主角,因为她们怕痛,我不怕。拍《烂头何》的时候,女主角都被打跑了,导演就想起我,就说找那个女孩来吧。”
那场戏是讲一个不会任何功夫的妓女,刘家辉在后面控制这个妓女,显得好像打得很厉害一样,但是拍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是真的要被人打,没有任何保护的。”
这场戏NG很多次,原因是惠英红被打到一半,就要求导演给她几分钟,跑出去吐,吐完回来坚持再拍,再打,因为不断NG,“大概打到好像30多拳,导演突然发觉了,就问副导演有没有给我肚子做保护,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护垫,什么都没有的,副导演说好像没有,导演就随手把他的剧本给了副导演:‘给她垫到前面吧。’就垫在我前面,打了40的拳,就拍完了。”
惠英红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走,如果不熬过这一关,我就没机会了。我要成为明星,家里才能有好的生活。同期有几个一起的,比我漂亮,我必须比她们更努力,更拼命!”
于是,惠英红选择了一种非常笨的方式“肉搏”去获得更多的机会,惠英红的拼命自然赢得了很多导演的好感,有时候,她在戏里不是绝对的女主角,但导演会在剧情之外为惠英红在武打时多加了很多镜头,到了最后,这让惠英红和女主的戏份看起来相差的也就没那么多了。“你看《乾隆下江南》《乾隆下扬州》一系列的戏,他们都找我来当女主角。”
惠英红觉得自己从不是一个机遇特别好的人,“今天摔了一个跟头就一下子捡到100块钱,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没有人找我演戏”
入行后,惠英红很快签约邵氏。1982年,她获得了第一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那一年,惠英红刚满21岁!
第一届金像奖还没有形成影响力。“我拿奖时还是500元一个月,我跳舞还能每月赚1500块,当时觉得,那个奖如果是金子做的就好了,我妈那时候不同意我做演员,但我和我妈说,我一定能红,我一定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后来刘家良导演知道惠英红家里真的很穷,亲自跑去要求邵氏给她涨薪,升为每部戏5万元。
拿到5万块的惠英红非常高兴,这笔钱一分都没有留,她全给了母亲,“那你母亲拿到钱之后,会留下一小部分给买衣服吗?因为女明星,造型和服装都是很重要的。”记者问道。
“买那么多衣服,拿来干嘛?衣服又不能吃,这我妈和我说的话。”所以在惠英红的意识里,即时出名后,生存也是第一位的。
拿奖之后,惠英红逐渐成为邵氏当家的武打明星。不过,惠英红不想一直打下去。“我不甘于每一天打到全身伤,打戏很让人崩溃,你想我每天睁眼就是打,第二天还打,要不就是被打,你永远都不清楚我什么时候不打,没有尽头!
惠英红一直希望自己能打开戏路,多拍不同类型的片子。对于她的尝试,邵氏并不允许。“他们觉得我是动作演员,很卖座,不可以去改变。因为怕我拍完之后,我打女的形象没有了,他们觉得如果我转了型,换了第二个形象出来,未必会成功,会影响票房,不会卖座。”
“那时候的香港电影,动作片已经开始没落了,文艺片开始起来,但无奈,你是动作演员,只能让人觉得你是老粗,和艺术沾不到边,但机会始终不是我的。我曾试拍过两部文艺片,第一部就是《男与女》,就是钟楚红后来拍的那个电影。”
“我拍了一天,邵老板就马上叫助手把我拉出来,不要让我演,他说,你演武打那么成功,那么红,突然之间演一个《男与女》,还有一点暴露的,会破坏财富,所以给了钟楚红拍,钟楚红就红了。
后来没人拍动作片,市场也抛弃了惠英红。
当时导演找惠英红,大多数是让她出演一些配角,“说实话,我都是主角的,但找我的都是第三、第四主角,我整个人开始疯了,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当时就在心里面骂,为什么找我演这种啊?为什么这样?那时候,我的情绪开始出现问题,出现问题我自己还不知道,然后,越来越不愿意见人,越来越封闭自己,越来越讨厌自己,我那段时间基本上好像有一两年的时间没看镜子,每次一看镜子就很害怕,觉得很丑,自己没有用,废物,真的对自己那种负面情绪非常厉害”
90年代末期成了惠英红人生中的低谷。由于不能接受这种失落,她得了抑郁症,甚至一度吃安眠药自杀,幸好被姐姐及时发现,救了回来。
“我这一辈子是别人的两辈子”
经历自杀之后,惠英红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曾经问过自己很多遍,是香港电影环境所变,还是我自己的情绪的问题,后来,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作为一个演员是什么要计较角色的大小呢?另一方面,我也是拗不过这个电影市场的。”
加上亲友们的鼓励,惠英红振作起来。2003年,惠英红低调复出拍片,同时加入了TVB,不再计较角色,重新再来。和当初一样,惠英红问她认识的每个人:“需不需要我,有什么角色吗?我其实特别感谢那时候帮我的那些人,比如TVB的梅小青、李添胜。”惠英红记得他们每一个名字。
“那当时我在拍梅小青的《宫心计》,拍完《宫心计》,我跟《心魔》的导演说我还差一段时间我才可以拍完,我说我拍完之后我才过来,然后我就跟梅小青监制说,你能不能最快先拍我的部分,没想到她说OK,然后,也非常顺利的去到马来西亚,开工第一天,导演见到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等了你三年,我才知道三年前他找过我,原来还是《心魔》,其实如果一般人,你三年前不拍戏了,其实不会再找你,对不对?他很坚持,所以我也非常感恩,感觉上天给我准备好了,再给我一个机会。”
2010年,惠英红凭借《心魔》里母亲这个角色再获金像影后。
在登台之前,惠英红吃了镇静剂,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她担心自己会晕倒。但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会拿奖,“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拍东西,以及《心魔》是小本制作。我知道在那个过程里有很多人帮我,他们当我是朋友。其实从第一届到第三十届,虽然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发生,如果细想的话,应该说是一个很丢脸的过程,你第一到第二十九,这三十年里面中间你是没有任何成绩的,所以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失败的那种感觉,可是总比没有的好,我真的很努力的走过来。”
采访到最后,记者问了她一个问题:“我知道你特别想要一个自己的家庭,但为什么不会选择生小孩呢?”
惠英红听了,停顿了几秒:“我没想过,从来没想过。”
“为什么?”
“因为小时候,我曾住在孤儿院。其实,我不是孤儿,是警察觉得我家里面太穷,我母亲把我放在街上去要饭,好像认为我母亲是没资格去养这个孩子,要法官来判定我到底去孤儿院还是回到家,中间有三个月就把我放到孤儿院评核我的家庭,这三个月我就和其他的孤儿住在一起。”
惠英红回忆起这样一个场景:“每次钟一响,所有的孤儿都会挤到门口等着吃饭,每周还要站一排,会有人来,看谁比较顺眼就会领养,那我自己会觉得我的路很苦,我不知道我生的孩子他的人生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太悲观了,那你连试都不想试吗?”记者再次问道。
“其实,很多人都和我说过这件事,我觉得和我小时候有关,我真觉得我小时候太苦了,我的一辈子是别人的两辈子,加上我的性格,不是我不能走别的路,是我本身的性格走不出别的路!”
“但我已经很幸运了,不是吗?”惠英红又补了一句,脸上发着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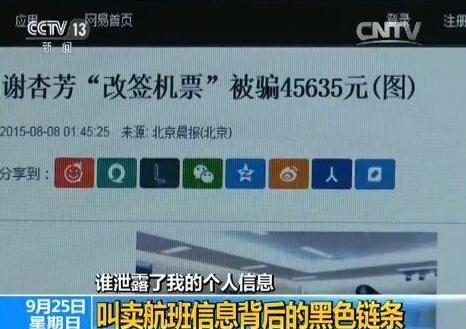




![【走在冷风中 ([刘思涵] 彤子)】](https://pic.bilezu.com/upload/0/f4/0f4ff3af0a0f1b95e87a557ae11e13fa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