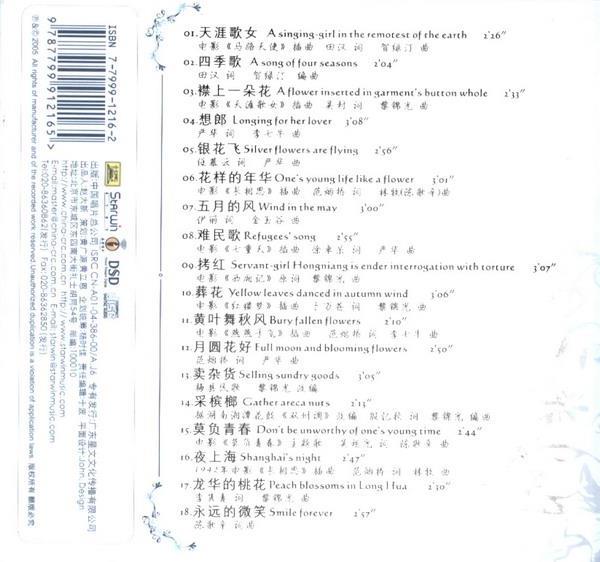黄宗英访谈录:我所了解的周旋和赵丹
接着,她便陷入了往事的回忆中:“大约是在1935年还是在1936年吧(笔者注:应是1937年),我记不准确了。赵丹和周璇一起拍《马路天使》,那时周璇还是一个小姑娘,她在片场拍戏,休息的时候,还趴在地上和别的小朋友打弹子,是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赵丹和她,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小孩,没什么来往的。
我呢,在上个世纪40年代,大概在1946年1947年间,在上海金都大戏院演话剧《甜姐儿》(笔者注:这部话剧几年里连演数百场,使“甜姐儿”黄宗英驰名上海滩)。一天演两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中间从傍晚5点到7点是周璇的独唱音乐会,这样就碰到、认识她了,但也没有什么深交。
上海解放不久,周而复出面组织成立了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我担任了这个协会妇委会下的福利部部长。福利部为了解决演员的后顾之忧办了一个托儿所,我担任了理事长。”
“大约在1951年吧,有一天,有人匆匆赶来说:快、快,周璇在枕流公寓的家里,精神病发作了,在房间里烧东西,要把小孩从窗口摔出去。我便和黄晨(笔者注: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夫人,也是剧影协会妇委会成员)、吴茵等人赶到枕流公寓周璇的住处。
到了那里,见周璇的房间里一片混乱,她在烧什么东西看不出来。我赶紧安抚精神紊乱、烦躁不安的周璇,黄晨便抱起周民,把他送到朱茂琴的剧影第二托儿所去。剧影协会的张立德、老凌也赶来了,还有在场的居委会干部,我们商量下来,决定要把周璇送进精神病院。
我们当即叫来刘琼和韩非,让他们俩把周璇哄出去,说带她外出散心,其实是把她送往精神病医院。”
“就这样,周民离开了他的亲生母亲周璇,剧影第二托儿所成了他的栖身之地。第二年冬天,上海麻疹流行得很厉害,理事会决定把剧影第二托儿所停办。理事会在开会时提出,吴茵年纪比较大有经验,就由她把周民领回去吧。
上午决定了这件事,到下午,我下班回家吃晚饭时,忽然见门厅里有一张小床,一看这是周民睡的小床嘛。说好送到吴茵那里去的,怎么送到我这儿来了?再看,民民这个小鬼头和赵青、赵矛爬在地上,三个人滚在一起玩得起劲。
我就问,周民怎么到我们家来了?家里人说,吴茵的婆婆死活不肯要。开始我想去问个明白,但看看眼前这三个小孩玩得很好,我就犹豫了。
这时,赵丹的父亲就说了:宗英啊,我们没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自己就来了,这是老天爷的意思,老天爷把他送来的,我们就收下来吧。
这样,民民就成了我们家的孩子。赵丹顶喜欢和小孩玩,赵青、赵矛那两个孩子大了,十几岁了,周民才1岁多,赵丹特别喜欢逗他玩。”
“1957年的夏天,周璇突然生病了。那年夏天上海流行急性脑炎,蛮厉害的。她感染上了,被紧急送到华山医院治疗。
当时我正怀孕,产前,我曾到医院探望过她。有一件事,我很受感动。那年夏天,上海的天气很热,当时又没有空调,我见到她的病房里摆满了巨大的冰块。
周旋在华山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终于没能挽回她的生命。我们又把周民安排到荣毅仁的妹妹荣素珍开的上海第一妇婴托儿所,这是当时上海最好的托儿所了。
为了照顾好这个特殊的儿子,我特意把剧影协会第二托儿所的炊事员洪雪珍接到我们家里来,专门照料周民。因为周民从小是洪雪珍带大的,和她熟悉,和她有感情。”
笔者提到,周璇病故后,海外陆续有善款到国内来,据说折合人民币有40多万元,后来被有关部门退了回去。笔者问:“这件事您知道吗?”
黄宗英答:“这件事我不清楚,那个年代,我们不会对组织上提这种问题。”她说:“大约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银行有人找我,对我说周璇在海外有一笔遗产,你抚养周民,是他法定的监护人,只要你签个字,就可以把这笔款子转到国内来。
我说,我们不要这笔钱。中国银行的人说,这不是你们要不要的问题,国家需要这一笔宝贵的外汇。这样,我就签了字。具体有多少数目,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记得,我们只取过1000元港币,后来这笔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什么都要凭票,我记得取了这一笔外汇后,还给了一大堆布票,我买了布,请裁缝到家给周民做了几套新衣服。
民民从小头就长得大,小时候外面买的现成衣服都套不进去,要请裁缝到家里专门为他做。赵丹和我,还有他的弟弟、妹妹都叫他大头。我们家里经常唱上海流行过的那一首童谣: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从小赵丹就特别喜欢民民,经常把他扛在肩上,带他去吃西餐,带他到文化俱乐部去玩。在家吃饭的时候,赵丹总要说:‘来,大头,坐到我旁边。’有一段时间,赵丹很迷信,外面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要出席一个什么会议,总要在小纸片上写几个字,吉还是凶,好还是不好,去还是不去等等,诸如此类的占卜语。他每次占卜的时候,总是会把民民叫到身边:‘来,大头,你来给我抓阄。’仿佛只有这个大头抓的阄,才会给他带来好运似的。”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写大字报:‘赵丹是反革命’,民民在大字报旁边写:‘赵丹是革命的’。当时大字报贴到了我家门口、走廊上,周民就去撕大字报,用毛笔去改大字报,用纸去覆盖大字报。他带着弟弟妹妹赵桔、赵左、赵劲,到处撕赵丹和我的大字报。
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冲到我们家,抄家、抢东西,还用皮带抽打赵丹,他就跳出来、冲上去和红卫兵撕打,被家里人拉开,他们继续殴打赵丹,周民护住赵丹,他扑在赵丹身上,对红卫兵说:‘不准打我爸爸!’他们就打了民民。事后,我就对他说:‘民民啊,我求求你,你走吧,你和赵丹、黄宗英没关系,你和我们脱离了关系,人家不会寻到你的,你走吧……你再这样下去,要被人家敲死掉的。’但他不肯,他不吭声。”
“赵丹‘解放’后,第一个就想到周民,想方设法把周民从农村调到省城。那次他到江西的一个剧组去,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周民。他见到当时江西的第一书记江渭清,又和管文教的省委书记黄知真讲了,最后黄书记把周民安排到了省文联。
后来赵丹去世,根据政策,可以调一个孩子回来。当时我有三个小孩在农村。我们就先把周民调回上海,进了《萌芽》编辑部。
那时候,只有我的女儿赵桔还在外地,她是先去插队,后考进了当地的师范学院。作为一个母亲,我心里也是很矛盾很为难的,世道险恶,一个女孩子在外地很不安全。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写信来要帮助我女儿出国。我想,先把她办出去也好,将来回来可以不受户籍的限制,也可以回上海。”
“赵丹特别相信民民,文革结束后,赵丹补发工资,大概是两万元。赵丹讲这都是血汗钱啊!上影厂来电话要家里人去取钱,他就让民民去拿。取了钱,民民直接存到静安寺那家工商银行,那里是日夜银行,将来取起来方便,当时给每个孩子和亲戚账户上都存了1000元。
后来,搬到新康花园,也是民民到电影局去跑,才解决的。
1980年,赵丹追悼会上,捧骨灰盒的也是民民。
所谓遗产官司,那些钱,最后也是民民出面到外省去办来的。我不要,一分也不要,我给民民的多。
人是要凭良心的。”
笔者问:“那么周民的生父究竟是谁呢?”
黄宗英答:“最后都不能肯定。朱怀德不承认,解放后他害怕人民政府,我们让他一个月送48元周民的托儿所费,他乖乖地送来,就是不承认。我们都有这个怀疑:就是生父另有其人,谁呢?那是周璇在香港的事(笔者注:指怀孕),难说,周璇不说,谁也说不清。都没有根据。有一位社会名流说像XXX,但也没有医学根据。当然,现在都不在世了,反正有这个怀疑,还是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笔者又问到了唐棣。
黄宗英答:“不太了解这个人,上世纪50年代,领着个孩子跑东跑西,到处要钱,要知道周璇是个精神病人啊,怎么受得了!他到我们家,给了他100元钱,文革中又到湖南路来,我们那时也没有钱,都领生活费,就没给。
反正我和吴茵、黄晨几个到周璇家去时,见到周璇大橱里有许多东西,名贵裘皮大衣什么的,后来她疯了,送精神病院后,再去看,就什么也没有了。许多人都说是他串通女佣人,做了手脚。这件事,听法院的,按法律办事,当年,静安区法院不是判了吗?从来就没有撤消过嘛,这就是根据,有什么意见,找政府,找法院去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