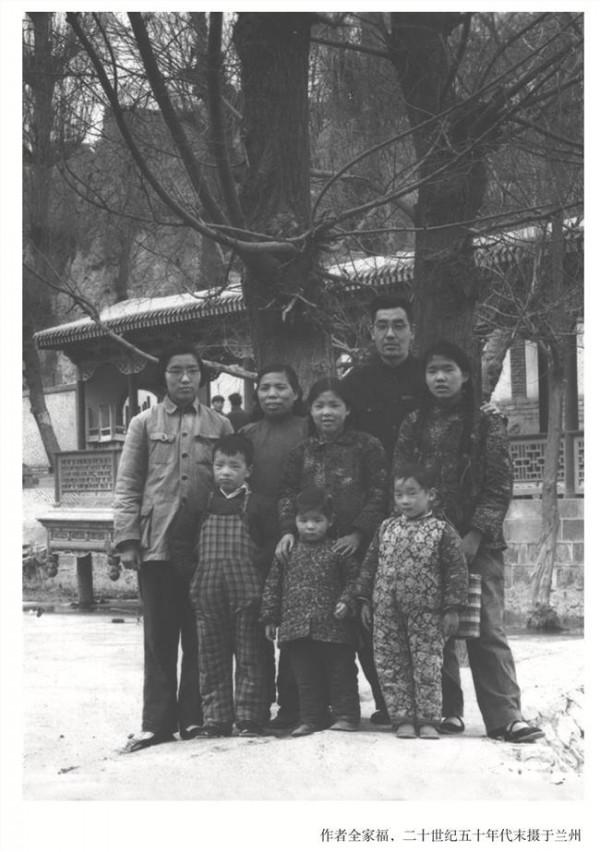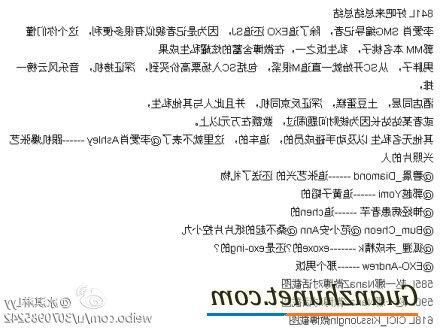秦晖赵俪生 秦晖: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
赵先生蒙难后,研究被迫中断,上述专题未能深入下去。但此后几十年间这些话题又不断地引起讨论。1980年代先生复出史坛后,其研究方向主要转向土 地制度史等。但他一直关注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动态,不满这个领域的萧条,希望看到新的突破。
1990年代我关于关中土改的一些研究发表后,先生曾来信极表鼓 励。继承新史学的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继续推进对“民变”现象这个认识中国历史的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仍是我们作为后学的责任。
具有汉学功底的宋学家
赵先生属于五四以后的新史学家,但与那个时代许多人文底蕴深厚的学者一样有着扎实的国学功底。他以重视理论著称,但对于史料也非常认真。他在 1940年代开始治史学时是从做《王山史年谱》起步的,初期以明清之际诸学者的事迹与学术思想考证为主,曾经得到过胡适、傅斯年的好评。
当初他作为一个自 学者(先生在清华读的是外语系,而且未毕业就投身革命与抗战,并非历史学科班出身)被河南大学聘为副教授,就是胡傅二先生推荐的。
晚年的赵先生又回到了学 术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只看赵先生书的人或许不会想到,赵先生当年给我们开的头一节课,讲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与章太炎的《自述学术次第》,后来他还 给我们讲过《汉书o艺文志》和《隋书o经籍志》。
在许多领域赵先生不仅有整理史实、解释因由、归纳演绎的功夫,而且还是不少关键性史料的首次发掘者。例如 赵先生的桑梓先贤明清之际的丁耀亢所著《出劫纪略》一书,当初海内仅有数抄本,极罕见,连晚明文献专家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在1964年增订前也未 著录。
1950年代赵先生根据其家藏抄本公布了其中记载李自成政权在当地处理财产的关键记载,后来成为言明末农战者必引的首要文献。但是在1980年代该 书铅印出版前其实没什么人见过原书,大家都是辗转相沿自赵先生,但当时却都不注转引。
赵先生对“旧学”有看法,他常说他既不喜欢汉学的琐屑,也不喜欢宋学的空疏。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我们把“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作广义的引申的话,我觉得先生的风格可以说是个“具有汉学功底的宋学家”。
“小问题越做越大,大问题越做越小”
赵先生平生之学涉猎极广,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有人则认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实在我看来,赵先生平生 治学一出于“爱智求真”的纯粹兴趣,二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热情与责任感,至于要在某特定领域成为“名家”的目标,他是不在乎的。
这样治学当然是有得有失。不 过我认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没人能成为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以有限的精力有限的信息处理量治同样严谨的学问,还是可以有不同做法。
事实上不要说“百 科”,今天一个学科内的上百分支乃至“二级”“三级”分支,也不是那个学科的某专家能全面掌握的。仅以中国史的断代分支论,明清史专家未必懂魏晋,甚至明 清政治史专家未必懂明清经济,就是搞明清经济,研究农业的未必懂工商业,研究江南经济的未必懂辽东。
一个学者其实一生不过能够研究若干“问题”而已。但是 如果永远只在一个问题上钻牛角尖,虽然也能出成果,毕竟眼界狭窄,难成大器。所以事实上成大家者往往都关注过许多“问题”。
区别只在于有些人研究的这许多 问题集中在一个学科乃至一个分支,有些人的“问题”则分散在各处。但不管是聚是散,就单个问题而言都有严谨与否之分,甚至很难讲怎样做更有信息集中的优 势。
一个研究明清政治问题的人可能对明清美术无甚兴趣,但却对其他朝代乃至其他国家的政治问题有兴趣,而这样做的局限也并不见得就比在明清范围内既注意政 治也注意美术更大--只是从功利的角度讲,人们会说后者是“明清史专家”,而前者就说不清是什么“家”,于是有人或许就会妄自褒贬而已。
其实赵先生不是不知道这些。他就曾说过:“兴趣不可过多,多所鹜则少有成。一个主兴趣,配几个副兴趣,一辈子也就够了。例如,主兴趣油画,副兴趣国 画和漫画。……总要求其互相邻近,以免浪费精力,且可配套成龙,一艺多技。
主兴趣是最要害的。人一辈子成就大小,关键在此。除非万不得已,不可轻易'跳槽 '。”但他自己却不是这样。众所周知,赵先生一生多次大幅度改变学问方向。他早年就读清华外语系,青年时代热心文学创作与翻译,后来治史,也是先以考据法 治明清学术史,后转农民战争史(基本是通史),再转土地史(侧重晚唐以前),以及思想文化史(又侧重明清),期间还研究过西北史地之学与先秦子学等等。
赵 先生的天分、精力与信息处理能力都是出众的。
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的认真。生当一个特殊历史时代,具有丰富的社会关怀和求知欲,赵先生关注的“问题”就很 分散。但这不难理解,他既然当年能够投笔从戎,又能卸甲读书,如此大的人生转折他可以拿得起、放得下,又何怪他一旦认为某个新“问题”对于时代、社会具有 重大意义而自己又有条件研究时,会打破畛域,迸发新的研究兴趣。
虽然在这些“问题”所在的各大学科他也未必都被看成一流专家。但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本 身他都有研究的激情,而且很认真,因此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同样是一流的。
赵先生未必是整个思想史领域的权威,但他无疑是顾炎武研究的权威;他未必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但无疑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权威。加上他对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这些重点领域的较全面的把握,为学而能如此,成就应该说是很大 了。
赵先生对晚辈和学生的治学倾向持十分开明的态度,从不要求他们在风格上领域上更不用说观点上追随自己。即便同样治 史学的先生的一子一女一孙,其学与先生也完全不同。我自己在1990年后也关注过不同领域的许多“问题”,有人因此说这是受赵先生的影响。
但其实从 1978年我师从赵先生直到1989年,我做的基本上是“钻牛角尖”的学问。后来的变化是时代风云与个人选择的结果,与先生并无直接关系。但先生的求知 欲、责任感和认真态度,是我愿终身师法的。
当年我“钻牛角尖”于明清鼎革之际,赵先生对此是鼓励的。但他也曾担心我的眼界太窄,他曾对我说:每个人的兴趣 不同,研究的“问题”有大有小,但有志的研究者“大问题要越做越小,小问题要越做越大”。他自己是这样做的,他对我们这些后学的影响,也将垂于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