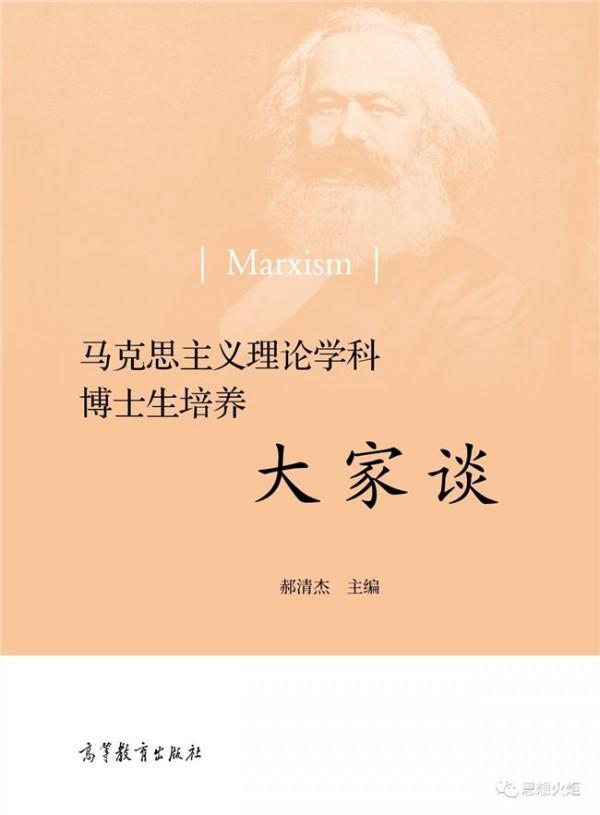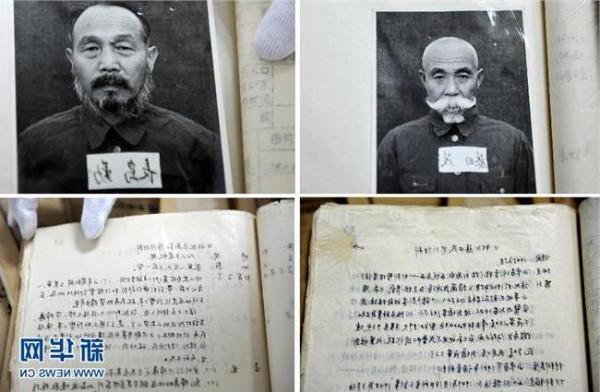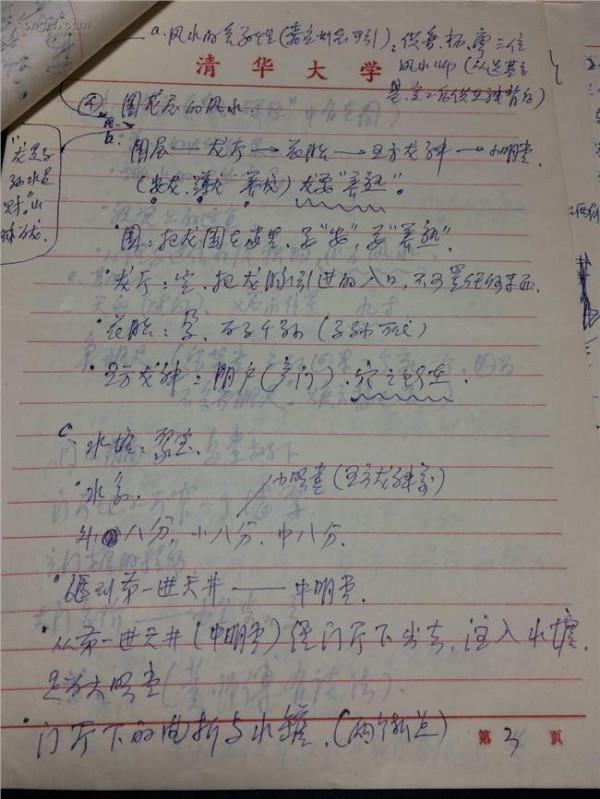悼念陈炎 悼念 | 山东大学陈炎教授《文明与文化》
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文化是多元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
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正是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文明总量的过程;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也正是人类文明不断减少其外在的文化差异的过程。因此,如何在增加人类“文明”总量的同时尽量保持“文化”的多样化,便成为当今人类的重要课题。
无论是在中文还是在西语中,“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都属于使用频率极高而又极为模糊的概念。有时候它们可以混用,有时又有严格的区别。但若问混用的理由在何处?区别的根据在哪里?不仅百姓日用而不知,就连学者也未必说得清楚。
在当今世界上,尽管以“文明”、“文化”为题目的论文、著作、学术刊物和研究机构不计其数,但对于这两个概念及其内在关系,却始终未能达成一种广泛的共识。在前些年“文化热”的讨论中有人统计,仅“文化”一词就有140多种不同的界定方式,最近又有学者指出,“英语中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据说是英语词汇中意义最丰富的二、三个词之一” 。
这种现象必然会带来三重疑问:第一,造成这种歧义的原因何在呢?第二,这种歧义能否取消呢?第三,如果歧义不能取消,是否还有必要界定下去呢?
我们知道,语言中的词作为一种“能指”,其“所指”对象越抽象、越丰富,就越难以解释清楚。而无论“文明”还是“文化”,都不像“桌子”或“电脑”那样,指称某种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恰恰相反,它们力求包含人类创造这些具体事物的总体成就和不同样态,因而其本身就与言说者看待整个“人化自然”的文明立场和文化态度有关。
于是,这里面所潜藏着的“解释学的循环”势必会导致歧义的出现。而且从逻辑上讲,这种歧义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
但是,尽管分歧是难以避免的,讨论和界定这些概念却不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在哲学领域中,每一种对世界本质问题的独特解释都有可能引发出一种独特的哲学观念、甚至哲学体系一样;在文化领域中,每一种对文明或文化概念的独特理解都有可能引发出一种独特的文明观念或文化理论。
不同的是,哲学中的元范畴是用经验中的“能指”来指称超验中的“所指”,因而带有形而上学之嫌;文化中的元范畴则是用经验中的“能指”来指称经验中的“所指”,因而可以避免独断论之弊。
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对文明或文化问题进行认真、系统地研究,都不能不从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和反思入手。当然了,本文中的界定和反思也只代表笔者的一孔之见,它既不同于施宾格勒,也不同于汤因比,并且也不急于寻求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度来协调群体关系,借助宗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基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在我看来,人作为一种“类存在”,至少具有使用和制造工具(包括一切科技手段)、依赖和凭借社会关系(包括一切社会制度)、渴望和追求情感慰藉(包括一切精神享受)这三个基本特征。
唯其如此,人类才可能有对真的探索、对善的追求、对美的创作。
反过来说,只有在对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创造之中,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在这一点上,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种族的人类群体概莫能外。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类文明有着统一的价值标准。
换言之,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就必须进行真的探索、善的追求、美的创造。人类要进行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和创造,就必然会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重重矛盾,而所谓文明,就是人类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进度。
当我们说“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程度高于封建时代的文明程度”这句话时,既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能力高于封建时代,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组织形式较之封建时代更能焕发人类群体改造世界的总体能力,还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精神产品及其享受形式比封建时代更加丰富多彩。
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文明的尺度,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综合尺度。
所谓“文化”,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在协调群体关系、在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由于人类文明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中分别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风格和样式。
我们知道,考古学家对“文化”一词的经典使用方式,就是从不同地域的出土文物在建筑、工具、器皿的风格和样式上入手的。由于旧石器时代不同地域出土的器物中尚无风格和样式上的差别,因而“文化”一词只有在新石器时代以后才被使用,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
例如龙山文化的发现即是由一片黑陶引起的,由于这种黑陶器皿与仰韶文化的彩陶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样式,从而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不仅龙山的黑陶不同于仰韶的彩陶,而且良渚的玉器不同于大汶口的石器、红山的陶俑不同于马家窑的人像……,正是这种风格和样式的千差万别,才使得同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华夏文明表现出五彩缤纷的文化形态。华夏文明如此,整个人类文明更是如此。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民族样式,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将会显得多么的单调乏味。
若就这些不同风格、样式、特征的文化产品对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对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及历史水准而言,这些文化产品所包含的文明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但就这些风格、样式、特征与其所属的民族、地域、时代之间的关系而论,文化本身并无贵贱之别。
譬如穿衣,我们穿的衣料能否取暖、是否舒适、可否满足人类自身的基本需要,这其间有着一个文明的问题;至于是穿西服还是穿和服、是穿旗袍还是穿超短裙,这其间又有着一个文化的问题。
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衣衫褴褛是不文明的表现;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却不能说穿中山装是没有文化的标志。譬如吃饭,我们吃的食物能否果腹、有无营养、是否卫生,这其间有着一个文明的问题;至于是吃西餐还是吃中餐,是吃法国大菜还是吃日本料理,这其间又有着一个文化的问题。
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茹毛饮血是不文明的表现;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却不能说吃美国快餐是没有文化的标志。譬如工具,我们用的器皿会不会渗水、是不是坚固,这其间有一个文明的问题;至于是用石器还是用玉器,是用彩陶还是用黑陶,这其间又有一个文化问题。
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之间排列出一个文明的序列;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却不能说色调单一而又质地细密的黑陶没有文化品味……。
如此说来,文明与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一般来说,文明的内在价值总要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而文化的外在形式之中又总会包含着文明的内在价值。
如果说穿衣有着一种文明的内在价值,那么穿西服还是穿和服则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我们很难设想有一种不带民族、时代、地域特征的、没有任何风格和样式的抽象的服装;如果说吃饭有一种文明的内在价值,那么吃中餐还是吃西餐则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我们很难设想有一种不带民族、时代、地域特征的、没有任何风格和样式的抽象的饭菜;如果说使用器皿有一种文明的内在价值,那么用中式的陶瓷酒盅还是用西式的高脚玻璃杯则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我们很难设想一种不带民族、时代、地域特征的抽象的容器……。
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文化是多元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如果我们只承认文明的一元论而不承认文化的多元论,便有可能得出“欧洲中心主义”之类的邪说;如果我们只承认文化的多元论而不承认文明的一元论,便有可能得出“文明相对主义”之类的谬论。
前者企图将一种文化的模式强加给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并肆意贬低和蔑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创造;后者则企图用文化模式的多样性来抵消文明内容的进步性,并以民族特色为借口而拒绝外来文明的影响和渗透。
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却有强弱之别。所谓“强势文化”就是指能力较强、效率较高,从而包含文明价值较多的文化系统。相反,所谓“弱势文化”则是指能力较弱、效率较低,从而包含文明价值较少的文化系统。譬如语言文字,这种因民族、地域的不同所形成的不同的符号系统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其作为人类的日常交际工具和信息传递手段却有着是否丰富、是否准确、是否容易掌握、是否便于处理等等差别。
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固然不能说云南纳西族人保存至今的东巴文字没有价值,但这种古老的象形文字系统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却难以发挥更大的影响。
一种语言文字如此,而那种以语言文字为子系统的大的文化母系统更是如此。怀特把文化看成是一个能获取能量的系统,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文化随着每年每人利用能量的增加而演化,从而满足着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各种需要。
尽管从环境保护主义的立场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是值得商榷的,但人类迄今为止的文明发展和文化创造却很难提出反面的例证。
文化的差异原本产生于时代、地域和民族的不同,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的改善、信息的加强,不同民族、地域之间以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政治对话、军事征服等各种方式渐渐打破了固有的文化疆界。然而,在世界一体化(也就是时、空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彼此影响和相互渗透并不总是自愿的,更不是等值的。
在这一过程中,“强势文化”常常居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这种影响和渗透自然有其好的一面,它使得居于劣势地位的“弱势文化”不得不改变其固有的状态,以提高其文明含量。
因此可以说,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也正是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文明总量的过程。但是,这种影响和渗透也有其坏的一面,它使得不同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别越来越小,文化面貌日渐趋同。因此可以说,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也正是人类文明不断减少其外在的文化差异的过程。
仍以语言为例,16世纪,英语还只是居住在英格兰岛上的几百万人的母语,而时至今日,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已达到3 5亿之多,全球有3/4的邮件是用英语书写的,而国际互联网上的英语信息更是高达90%以上。
不难想象,在英语成为世界语言的过程中,人类的交往获得了很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有多少个比云南纳西族更为不幸的民族文化连同它们的语言文字一同消亡了。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穿着西服,系着领带,开着丰田牌轿车,来到星级化管理的写字楼里,坐在由IBM公司产生的电脑面前,使用着由比尔 盖茨开发的WINDOWS系统呢?或许,这一数量与全球的文明总量成正比,但却与全球的文化总量成反比。
尽管美国人为印第安人设置了保留地,尽管中国人为纳西古乐建立了民乐团,尽管各大旅游区都有所谓民族村之类的保留项目,但要把各个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真正保留下来,使其不在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被淹没,又谈何容易呢?迄今为止的历史似乎表明,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是以文化方式的趋同为代价的。
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在开垦荒地、建造工厂的过程中灭绝着自然界的稀有物种;而且在殖民统治、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灭绝着人类社会的稀有文化。也许有一天,全球化的历史运动大功告成了,那么文化的概念会不会螺旋式地回到旧石器时代,再一次与文明的概念相重叠呢?
好在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影响和渗透并不总是单向的。尽管文化有强弱之分,但不仅弱势文化要从强势文化那里学习很多东西,强势文化也要从弱势文化那里汲取必要的营养。美国学者罗伯特 路威曾随手抓了一张欧洲人的菜单进行研究,分析的结果使人大吃一惊,菜肴中的四分之三原料都是从外地引进的:在哥伦布出世以前,欧洲的厨师们根本就没有见过番茄、土豆、四季豆、玉米和菠萝蜜,这些都是从美洲新大陆引进的。
至于饮料:1500年前,欧洲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可可,什么叫做咖啡,什么叫做茶。
前者是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带来的,中者最初只生长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至于后者嘛,熟悉鸦片战争的人都知道它是怎样从中国被运到欧洲去的。如此说来,如果没有对外的贸易或掠夺,没有文化的交流和渗透,欧洲人的餐桌上便只剩下三样东西:面包、白米布丁和牛奶。
反过来,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人自己的餐桌,也会发现比200年前丰富了许多,那上面不仅有烧饼、油条,也有面包、果酱,不仅有中国的老白干,也有德国的啤酒和法国的香槟。
毫无疑问,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交流无论对东方人还是对西方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它纵然不能增加已有文化圈之间的差异并突出其特色,但却使我们原有的文化形态更加丰富,从而享受的文明质量也随之提高。
在这一方面,或许日本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当今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个东方国家比日本的西化程度更高了;然而与此同时,恐怕也没有哪个东方民族比日本更善于保存传统文化了。一方面,日本人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在十分顽固地维护着自己的民族传统。
于是,在这个太平洋的岛国上,随处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奇妙的文化景观:西式的摩天大厦与和式的木制建筑同时并存;西服、革履与和服、木屐并行不悖;既可以发现握手的场面,也可以看到鞠躬的情景;既有地球上速度最快的电气火车,又有世界上节奏最慢的茶道仪式;既可以观赏到标准的芭蕾舞、西洋歌剧,又可以欣赏到传统的能乐、狂言;不仅旅馆、饭店,就连厕所也能够分出“西式”与“和式”两种。
真可谓是泾渭分明、并行不悖。说到底,文化只是文明的外在形式。因此,凡是具有文明价值的文化产品,无论东方西方,都可以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尽管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交流和渗透是一种历史趋势,但是这种交流和渗透却并不总是自觉或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文化的要素与功能、文化的结构与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理解。
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是由各种不同的要素组成的,而每种文化要素都有实现其文明价值的特殊功能,以满足人类群体的需要。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将这种需要分为基本的和次生的两个层次。基本需要一般是建立在生理需求基础之上的,包括摄取营养、生殖繁衍、身体舒适、生命安全、适当休息、行动自由、健康成长等;次生需要一般是建立在社会需求基础之上的,如劳动协作、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契约保障、情感慰藉等等。
人类正是在满足基本需要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次生需要,从而向文化提出越来越多的文明需求。
尽管人类的文明需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由于不同的人类群体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不同,因而满足其文明需求的文化方式也不尽相同。以中国人的饮食为例,所谓“东酸西辣南甜北咸”,看上去似乎仅仅是一种毫无道理的习惯而已,细加分析却不难发现,这些习惯的形成或受制于不同地域的物产条件,或归因于人体在不同气候环境下的生理需求,各有各的道理。
某些文化现象,在该文化圈以外的人看来似乎是毫无价值的,但经过认真考察却往往能发现其潜在的功能和意义。
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例证是约翰 怀庭关于产后性禁忌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之前,不少人仅仅将赤道地区妇女产后长期性禁忌的文化习俗归结为一种迷信。但怀庭的研究成果却表明,由于赤道地区植物蛋白含量较低,使得新生婴儿常因患蛋白质缺乏症而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妇女在产后过早地再次怀孕,就会因缩短哺乳期而增加婴儿夭折的可能性。因此,这种连当地人也说不出原因的产后性禁忌实际上是有着潜在的科学功能和文明价值的。
当然了,并不是说任何文化现象都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也不是说人类的文化现象中没有需要改造的陈归陋习。这一例证给人们的启示是,在没有弄清楚一种文化现象的文明功能之前,不要轻率地加以否定;反之,在没有搞清楚一种文化要素的文明功能之前,也不要生搬硬套。而这两种现象,恰恰是人们在文化的传播和移植过程中最为常见的错误。
文化系统不仅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而且各要素之间亦有着内在的结构关系。一般说来,文化的诸多要素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只有在其特定的文化结构中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从而实现其文明的价值。仍以饮食为例,筷子和刀叉作为一种文化要素,它们的功能是将烹饪好了的食物送进人们的嘴里,从而改变人类用手直接吃饭的不良习惯。
但是,筷子和刀叉只有分别在中餐和西餐之不同的饮食结构中才可能实现其文明的价值,否则,无论是用筷子吃牛排还是用刀叉吃水饺都只能成为一种笑谈。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矛盾和冲突,只是二者侧重的要点不同罢了。
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些要素虽然具有鲜明的民族或地域特征,但其内在的功能却有着相似之处。例如佛教信奉释迦牟尼,基督教信奉耶稣基督,伊斯兰教信奉穆罕默德,它们之间相互排斥,有时甚至势如水火。但从文明的角度上看,它们又都有着满足人们终极关怀的极为相似的文化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只看到外在的文化形式的差异性而看不到内在的文明价值的一致性,就可能带来盲目的文化冲突,甚至把这种文化的冲突误认为是文明的冲突。在这一问题上,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美国学者亨廷顿的那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文明的冲突?》 。事实上,这种文化间的冲突非但无助于文明的进展,还常常具有反文明的性质。
在另外一些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些文化要素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对应的相互关系,而其所需功能则往往由其他文化要素加以“代偿”。例如,一般认为,宗教和法律是古代社会调节人的灵魂(精神世界)和肉体(行为领域)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文化要素,但这两大要素在古代的中国却都不发达。
稍加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并不是中国古人就没有灵魂和肉体的问题需要解决,而是中国古人利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方法来解决精神世界和行为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
因此,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宗教和法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发达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艺术和道德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文化功能上,我们的古人主要不是依靠宗教而是依靠艺术给人们带来情感慰藉和终极关怀的,我们的古人主要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秩序的。
如果不理解这种不同文化结构之间的重要差异,就有可能用一种文化结构的标准来衡量另外一种文化结构的价值,甚至可能徒劳无功地将一种文化结构中的要素生搬硬套地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结构中来。
在这一问题上,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中国学者刘晓枫的那本风靡一时的著作:《走向十字架的真》。当然了,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不需要改造,而是不可能简单地根据一种设想来加以任意改造。
一种民族文化尽管有其自恰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系统,但这一系统并不是先验的、永恒不变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既不断建构又不断解构的过程。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致力于不同的文化要素之间的系统研究,其成就是显著的,但他将外在的文化结构归因于人类内在心理结构的做法亦有其偏颇之处。
我们知道,不同的文化模式产生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就连不同人类群体的心理结构也是由环境造成的。在这里,我们不想否认心理结构对文化结构的影响。
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仍以儒家文化为例,那种建立在亲子血缘基础之上的伦理―国家观念是黄河文明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产物,而并不是什么“恒常不变的道理”。
强行改变它是不可能的,永远维护它也是办不到的。它的命运,既取决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更取决于内部土壤的分化和瓦解。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随着商品生产的深入,儒家文化所赖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原始血缘关系正在一点点地被法律契约关系所取代,儒家文化所一贯张扬的伦理道德观念正在一步步地被公民权力观念所取代……。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只看到文化的建构过程而看不到其结构的意义,就会将文化间的影响和渗透看成是一种可以任意为之的事情;反之,如果我们只看到文化的结构意义而看不到其建构的可能,就会将某种文化的存在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事情。
因此,只有将共时的结构主义与历时的建构主义统一起来,才有可能既看到文化系统的自恰性和稳定性,又发现文化变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