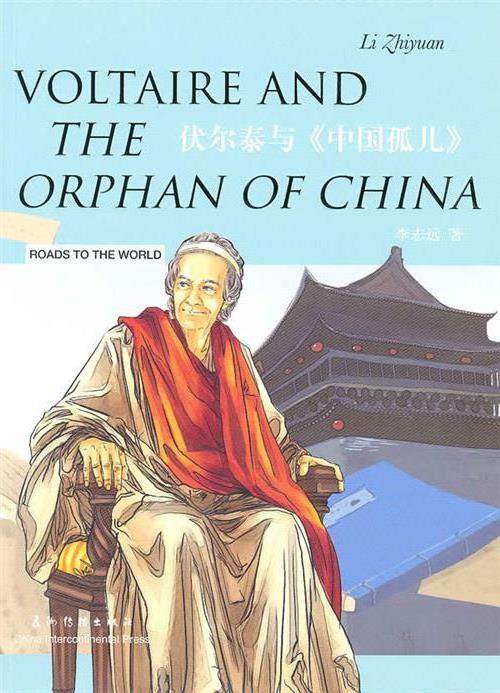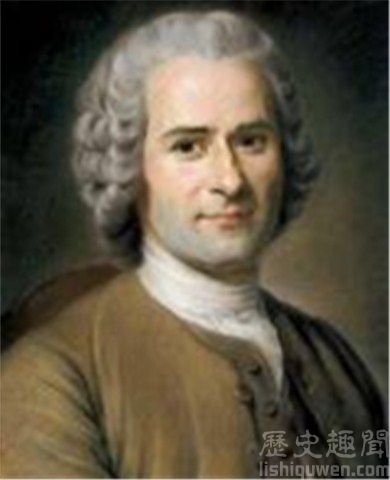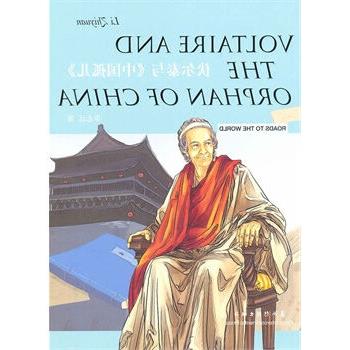《中国孤儿》:伏尔泰的中国文化想象
1755年8月20日,伏尔泰的中国题材悲剧《中国孤儿》,在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宫上演,获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广泛好评,把本来已在欧洲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中国文化热,推向了新的高潮。《中》的成功,使伏尔泰格外兴奋,其程度,甚至比当初《俄狄浦斯王》、《查伊尔》的成功更为强烈。这不仅是因为《中》让伏尔泰赢得了新的荣誉,巩固了伏尔泰的声名,更主要的是因为这出悲剧对伏尔泰来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它表达的是伏尔泰对他心目中的理想文明,即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想象。在伏尔泰看来,对《中》的肯定,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还是对他心爱的中华文化的肯定,进而是对他的启蒙理想的认同。
《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入法国的中国戏剧,伏尔泰最先是在巴黎的《法兰西信使报》上读到了该剧的剧情介绍,后来又在《中国通志》上读到了这部戏的译文。故事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为剧中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面对强暴与野蛮时表现的大义凛然的气质,维护正义的果敢坚毅,与强权斗争时的不屈精神所感动,于是决定把它改变成一部新剧目。但由于种种原因并他并没能马上着手,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755年,他的心愿才终于实现。
《中》改编自《赵》,但面貌全然不同。《中》挪用了《赵》里的某些情节,即作为故事生发原点的“搜孤救孤”事件。正是《赵》中围绕这一事件所发生的那些故事,感动了伏尔泰,触发了这位伟大思想家的灵感,因而他不忍舍弃。但所有其他的情节,却都是伏尔泰自己的创造。《赵》的时代背景是春秋时代的晋国,这时的中华文明正处于其辉煌的起点,在此背景之上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中华文明的内部。而现在,伏尔泰把它的故事背景加以重新设置,把中心情节发生的时代背景放置在宋元易代之际。这一重新设置具有关键意义,在伏尔泰看来,大宋王朝及其遗民代表的是人类的成熟文明,而成吉思汗的元朝代表的则是落后的野蛮文化。于是,宋元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文明与愚昧、正义与邪恶、理性与偏执的冲突。这样伏尔泰才便于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借故事带出自己对中华文化的想象。
时代背景的重新设置,必然会带来故事情节的重大改变。《赵》的情节紧张激烈,节奏紧促,扣人心弦,一切都围绕孤儿的命运来展开。《中》则不同,在这个悲剧里,孤儿的命运只是故事生发的原点,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伏尔泰实际上把情节的重心悄悄置换成对奚大美的争夺上了。伏尔泰企图借助这一故事重心的转移,巧妙地将《赵》的复仇主题,转换成了《中》中,宋朝遗民代表的文明的儒家文化与元朝统治者代表的野蛮文化间的冲突。这一转换的有效的(虽然不无逻辑上的裂缝),为在枫丹白露演出的成功所证明。伏尔泰正是以这样的情节,让他的人物展开表演,并以此表现他对中国的文化想象。
《中》的题目下有一个副题“孔子的五幕伦理学”,很明显伏尔泰这是在告诉人们,它是在借这一戏剧,展示他向往的儒家文化的魅力。在《中国孤儿》中,盛悌正是伏尔泰心目中的孔子伦理学的完美的承载者,换句话说,也是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承载者。盛悌并不是力挽狂澜的人物,在王朝覆灭文明存亡绝续之际,他只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儒者,但伏尔泰笔下的这个儒者,却仍不失为一个英雄。他毅然担负起拯救宋室遗孤的责任,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独子换取太子的性命。但他这样做主要并非是对皇帝的忠心,而首先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生命的关怀。有意思的是,伏尔泰笔下的这个儒生,并不教条。他有节操,敢于为保护孤雏献出自己的生命,甚至儿子的生命,但当他知道成吉思汗对妻子的感情后,反而尽力劝妻子活下来。伏尔泰通过盛悌这个人物,向他同时代的西方人展示他想象中的儒家文化,在他看来这种文化把维护正义看得高于一切,注重操守甚于生命,却绝不流于迷信,决不偏执。对照伏尔泰在《风俗论》所说,“似乎所有民族都迷信,只有中国的文人学士例外”[],这是非常有趣的。当然,事实是否如此,那要另当别论,我们只要别忘了,这只是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想象就够了。
如果说盛悌的身上体现了儒家文化刚性的一面的话,他的妻子奚大美却体现了儒家文化柔的一面,——也许应该说刚柔相济的一面更恰当。她的柔一是体现在对丈夫的恭顺,尽管她不同意丈夫的决定,以为那是徒劳无益之举,却并没有阻止丈夫计划的实施。再就是体现在对儿子的那一腔母爱上,当儿子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她以女性的柔弱之躯和母亲的刚毅坚强,保护儿子。伏尔泰以这个人物,表现儒家文化的仁爱,这仁爱的深厚与博大。不仅如此,伏尔泰还通过她,展示中国文化的尊严感,对尊严的珍视,尤其是对自由的维护,这体现了奚大美的的一面。在她心目中的杀人不眨的野蛮人成吉思汗面前,她毫不畏惧,敢于大胆指责他。不仅如此,作为战败者,她毫不畏惧毫不委琐,一如既往表现出对自己的文明的自信与自豪。成吉思汗见到她后旧情复萌,企图用强权、利益,甚至丈夫的、皇室孤儿的生命胁迫她屈服,但她毫不退让,甚至比丈夫表现得更勇敢更坚决更义无反顾。她对丈夫说:“我们要学习那些自由人的榜样。要死要活都得自己作主张。”这无异于一篇自由宣言。更为有意思的是,他们原先所做的是保护太子和拯救自己儿子的生命,而现在,当他们看到自由已经彻底无望的时候,他们宁可带着这两个孩子一同就死。这样,伏尔泰让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中,自由是最为珍贵的,它高于一切。这显然打上了鲜明的启蒙时代的色彩。
伏尔泰正是通过盛悌和奚大美夫妇,展示了他想象中的中国文化——孔子的伦理道德观。不要以为伏尔泰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孔子的伦理是对中国文化的贬低,事实上这是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最高评价。在他的《风俗论》——这部名著最初是写给他的情妇夏特莱伯爵夫人的——中,伏尔泰说中国“完善了伦理学,而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正是借助于盛悌和奚大美这两个人物,伏尔泰极力赞美了他想象中的中国文化。在伏尔泰看来,他们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中国文明的魅力,展示文明在野蛮面前的内在力量,她顽强的生命力。以至于横行天下战无不胜的成吉思汗,最后竟然在他们面前甘拜下风,“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了胜仗的君王了”。
至于成吉思汗,则是伏尔泰政治理想的实践者,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人物——开明君主。在《中》中,成吉思汗虽是君王,却以野蛮人的形象出现。他千方百计找到宋朝皇室的遗孤,目的是为了斩草除根。但他竟出人意料地被他的俘虏的德行所感动,在他们的人格面前低下头来,最后不仅不再杀太子、饶恕了盛悌夫妇,而且还“全盘中化”,实行大宋朝的法律,表现了巨大的胸襟和气度。通过这个人物,伏尔泰展示了儒家文化的魅力,以至于战场上的胜利者,竟心甘情愿承认文化上的失败,自觉地向被征服者的文化投降。
《中》表现出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想象,表现在对奚大美的态度,过于西方化了,不像视生命如草芥的东方专制君主,倒更像西方文学中的骑士。奚大美也不太像东方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淑女,却更像法国宫廷里的贵族命妇。奚大美决心为了自由而慷慨赴死的壮举,以及她对丈夫说的那番话,更使她成了伏尔泰本人启蒙理想的传声筒。正是对中国文化的这种误读,使他笔下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西方气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在《风俗论》也可以找到证明,而且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风俗论》中他总是尽一切可能赞美中国文化,表达他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以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某些时候,他不得不谈到中国文化的缺点,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他总是曲意回护,有时干脆强词夺理。比如在《序言》中,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科学上远远落后于西方,“中国人今天跟200年前的我们和古稀老人、古罗马人一样都是并不高明的物理学家”(话说得委婉之极),可接着他话题一转,“但是他们完善了伦理学,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显然是狡辩。说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伏尔泰这样说:“一个名叫始皇帝的暴君确曾下令焚烧一切书籍,但这个荒唐而野蛮的命令却警告人们把书籍小心保存起来。”[]明目张胆地强词夺理。
问题是伏尔泰为什么对中国文化如此情有独钟?为什么他不惜违背一向坚持的理性原则,在想象中极力美化中国文化,甚至为此牺牲故事情节的合理性,不惜故意歪曲历史事实?
在伏尔泰的想象中,中国文化热爱自由,坚持正义,仁厚博爱,宽容而不迷信,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而绝不偏执。这些恰是伏尔泰的启蒙理想,恰是伏尔泰理想的欧洲或更恰当地说是理想的法国文化。当然,这种理想形象的理想的方面恰是现实的西方文化所匮乏的。因而可以说,伏尔泰在展开他的中国文化想象的时候,是把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进行一种潜在的对照,在这种对照中,伏尔泰把他渴望而他以为欧洲又不具有的,都赋予他想象中的中国。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伏尔泰之所以热爱中国,乃是因为他想象中的中国是他启蒙理想的承载者。他对中国文化的维护,实际上就是他对自己的启蒙理想的维护。换句话说,他真正挚爱的,乃是他的启蒙理想。伏尔泰在《中》中让战场上战败的中国,在文化上成了最终的胜利者,正是他的启蒙理想的反应: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理性必将战胜愚昧,公正最终会获得维护,人类的尊严必得伸张。总之,人类的进步不可避免,文明是不可战胜的。
他的启蒙战友、思想上的对手卢梭的观点,都是冲着卢梭来的。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从《中》产生的现实因素来说,它就是伏尔泰与卢梭论战的结果。1750年,卢梭凭一篇征文的获奖一举成名,文中,卢梭以中国作为一个例证,证明科学对人类的危害,文明的无用。他说:“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艺是为人尊崇、摆在国家的第一位。如果科学可以纯化风俗,如果它能教导人们为祖国流血,如果它能鼓舞人们增长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当是聪明的、自由的而且不可征服的。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如果无论大臣们的见识或者法律所号称的睿智或者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所堆砌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不就是住满了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吗?”。[]1755年,卢梭把自己的新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赠给伏尔泰,书中,卢梭对人类文明的攻击变本加厉。伏尔泰没有对该书作评论,而是以《中》的公演来回应。在伏尔泰的故事里,中国尽管战场上失败了,但她的文明的魅力却强大得足以征服者匍匐在地,文明战胜了野蛮,进步乃是历史的必然。文明会为人类赢得尊严,而且是不可战胜的。这些都与卢梭的观点针锋相对。借助于《中》对中国文化的想象,伏尔泰回击了卢梭,维护了他心爱的中国文明。
《中》首演10天后,即1755年8月30日,伏尔泰给卢梭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先生,我收到了你反对人类的新著,我感谢你。没有人会动用如此心力来教唆人类返回动物状态。读尊著,使人渴慕四脚爬行。谢天谢地,我遗忘这种习惯已经六十多年了。”[]从此,两人彻底决裂。由此可见,伏尔泰对中国文明的维护,实际上还是为了捍卫他的启蒙理想。这才是伏尔泰创作《中国孤儿》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