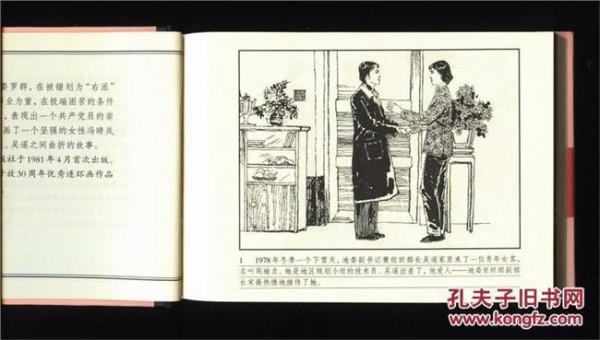鲁彦周发表于1979 《天云山传奇》鲁彦周[1977
7 我回到家里,看到了冯晴岚寄来的信。这封信来得正是时候,我多么想了解她啊!我饭也没顾上吃,就躲进房里读起来。正象我们久已疏远了的关系一样,她的信开头也用了一般的称呼,她写道: “宋薇同志:我们的现实情况,估计周瑜贞同志已经告诉你了。
你的情况,她也约略告诉我们一些。对于我们不同的处境,她也有她的看法,她是一个新型的人,她的许多看法,倒是颇有意思的,但是,我们先不管她的看法吧! “关于罗群同志的情况,我在我写的申诉中已经讲了。
现在我想谈一些我自己的事情,通过我的一些想法,你对罗群可能会加深一些了解,因为我觉得你对他其实是不了解的。 “对我和罗群的关系,你可能觉得很奇怪。的确,在我的亲属朋友当中,为此而大吃一惊的人确实不少。
他们经常问:冯晴岚这个人是不是神经上有点毛病?是不是有点浪漫主义?她为什么要主动背起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把自己的一生绑在一个‘屡教不改 ’的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身上?她现在肯定后悔了。
这些人好象很同情我,怜悯我,其实他们是完全错了。对这些人,我倒有点怜悯他们,他们哪里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难道追求一个浅薄的庸俗的生活方式,追随一个你并不爱的权贵,取得某种物质上和虚荣心的满足,就叫做幸福?事实上,我对自己所选择的路,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使我今天离开人世,我也敢骄傲地宣告,我是真正幸福的,是对得起养育我的人民和这个世界的,即使用一个较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也不感到惭愧,因为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完成了我应该完成的事。
“然而这也可能是我这个傻人说的傻话。 “对工作、对事业,我们先不谈吧,因为你很了解我是如何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作和事业,对党对人民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深厚的,我觉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认识罗群的可贵,说句真心话,谈起对党,对毛主席、周总理,对社会主义的感情,你我比之于罗群都差得很远呢!
“说来也是件奇怪的事,在天云山当我们共同结识罗群的时候,首先和他相爱的却是你。
我记得我是因为我太关心你们的爱情发展,而且是受你委托,才认真站在旁边观察罗群的,那时你用热恋的眼光望着他,而我却是以理智的心灵来观察他的。 “观察的结果,我记得我是跟你说过的,我从他的言行,从他对工作、对事业、对同志、对党的态度上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
记得在那天云山的清辉月光下,在那柔软的草地上,我在你耳边喃喃细语吗?我说罗群纯真得象水晶,又热烈得象火,忠诚坦白,是他最大的特点,对党的信念坚定不移,又使他具有惊人的毅力。
他没有权位观念,没有个人野心,这种人我认为是很难得的,当时你被我说得跳起来,紧紧搂着我。我们都一致认为,我们天云山区的工作干得踏踏实实,轰轰烈烈,人与人之间也正在开始建立一种新型的纯真的关系,正是罗群和当时考察队党委领导的结果。
“你那天和罗群互相表白以后,我是如何为你们祝福的,这些,我相信你是不可能忘却的。 “老实说,那时我根本没想到我自己会爱上他,我只是由衷地崇敬他,也许我已经爱上了他而我不知道,年青人的感情,有时候自己也分析不了的。
“我明确知道我自己爱上了他,那是两年以后的事。 “在这以前,我经历了很大的震动。 “你离开天云山到党校学习,是五七年五月吧,两个月后,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当以吴遥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宣布对罗群的右派言行要大胆揭发、无情斗争的时候,你想象我的震动吧!
工作组所宣布的所谓罗群罪行,以及他们对你和罗群关系的公然污蔑,我都在申诉材料里写了,正是这些所谓罪行,倒使我比较彻底明白了罗群的价值。
当时,为了表明我自己的态度,也是为了抗议,我代表你去探望他去了,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又一次受到了震动,我在罗群那里看到你的决裂书。
“恕我不客气地讲吧!你的信使我感到全身颤栗,使我看到了人和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使我感到对人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动摇,我就象正在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一翻过来却原来是一块丑恶的脏布片。 “难道所谓爱情,所谓同志就是如此吗? “我捧着你的信望着站在窗口、木然地望着天云山的罗群,我忍不住哭了。
这是解放以来我第一次哭泣,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你感到羞耻,为罗群感到悲哀! “我悄悄地走了。 “这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罗群,我只听说,在争论给不给他戴上右派帽子的同时,把他下放到特区所属的金沙区劳动去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给他写了一封劝慰的信,我怕他想不开,劝他思想上放开朗些。我那封信写得是很幼稚的,我用我的思想感情猜度他,以为他肯定是消沉悲观,甚至会发生意外的。
当我接到他的回信时,我脸红了。他在信中不但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悲观情绪,反而给我讲起运动员的锻炼故事来。照他的说法,这正是一次锻炼的机会,这使他现在真正有机会接近人民,可以从人民的角度,检验党的方针政策,从而为自己的思想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他在信的末尾,还开玩笑地说:‘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姑娘,他当我会对花发愁对月长叹吗?’ “你看,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在那里一直劳动到第二年,即一九五八年冬天,这个时候,我们特区忽然发了一道命令,要所有干部、职工、技术人员,停止一切工作去砍森林,连郊区农民也发动了。据说要把森林砍下烧炭,用这种炭去炼土高炉的铁,把我们在发现时曾经为之欢呼跳跃过的宝贵森林资源,准备付之一炬。
这实在是荒唐透顶的事。 “我没有去,我是有意拒绝去的,不久,我又听到一个消息。 “你还记得那位叫凌曙的区委书记吗?他是罗群的老战友了,在反右派时他被认为是和罗群在一起搞小集团的,也正在等待处分。
他和罗群听到要毁坏这片大森林时,就发动了一些老农民,组织了一个‘劝说小组 ’,堵在通往森林的路口,劝阻人进山,罗群还站在岩石上,发表了一通演说,把进山的人都讲得一个个低头不语,然后他和凌曙把人引到那些小山,砍伐灌木林去了。
“就是这样一件事,罗群的‘帽子’就给戴上了,凌曙也被撤了职。反对大跃进,破坏大炼钢铁嘛。 “倒是这个消息,使我们进一步接近了,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了他所在的一个小村子,这个小村子就在那森林边缘上,有一条瀑布挂在村东,发出轰然的巨响。
急促奔腾的河流,环绕着村子,使村子显得异常幽静。 “我是正午到达村子的,我在溪边的一棵大树下,找到了罗群,他坐在那拱起的树根上面,两脚伸在水里,旁边放了个还没吃的玉米饼,手里却捧了个本子,在那上面写着什么。
“我站在他身边半天,他也没有觉得。我偷偷注视着他,他那刚毅的轮廓分明的脸,除了被晒黑了一些外,没有任何变化。
他让那健壮的腿浸在水里,眼睛一会儿抬头望望那瀑布,一会儿又凝神在本子上写上几笔,渐渐,他的眼睛眯起来,一股我很难形容的笑容,在他脸上荡漾开来,这时正好有一道阳光,从老树的枝叶里射下来,照在他的脸上身上,使他有一种令人震惊的美。
这种美只有在那些有着非常高尚情操的人身上才会出现。 “老实说,当时我的心悸动起来了,在这一刹那之间,这才明白了,我的心是属于他的!
“我望着他,他回头发现了我,我在他眼睛一瞥之下,满脸飞红,我担心他已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内心的秘密。但是这个粗心的人,却并没留意,他只是笑笑说:‘你来了,正好,我正有件事想托你办呢!’我在他旁边坐下来,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问他什么事,他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我很难有工作可做了,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不为自己的理想而工作,宁可去死。
’我一听慌了,我说:‘你可别……’他不等我说完就笑了起来,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要自己安排我的工作,我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打算,我订了这样一个计划。
’ “他把本子递给了我,只见上面写着:学习和研究计划。在这个计划下面,他考虑了许多专题,每一个专题下面,都开了一些参考书籍,一共有十几页。
我翻着翻着,眼里不由又有点湿润了,原来他在被戴上帽子开除党籍之后,考虑的却是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他刚才的笑容,大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因为他又确立了他长征的目标。 “他见我沉思的神色,以为他计划有什么不周,他轻声问:‘晴岚同志,你给提提意见,你看这样行吗?’我说:‘行,太行了,不过这可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
’他说:‘是啊,我这种处境反正短时间也不会改变的,现在的困难是,我要书,要资料,要大量的书和资料,晴岚同志,你能不能给我办这件事? ’我说:‘这件事你就交给我好了。
’他见我答应了,高兴得象孩子,一下子跳了起来,几乎把全身都跌到水里。我也忍不住笑了。 “这一天,我们就是在研究计划和书目中度过的。
我们没有任何一句话,讲到我们之间的感情,他太严肃认真了,把我也变得严肃起来。他把自己的储蓄和本月的工资交给了我,要我充当他的采购员。 “假使到这时为止,不再向前发展,罗群的计划是可以顺利进行的,因为这时,他还是一个国家干部;当地的老乡也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坏蛋看待,因为通过凌曙同志,群众对罗群已有较深的了解。
“可是,很快事情又变了,五九年春天,罗群又被拉到一个水库工地上,强迫他在那里参加劳动,和他同时被拉到这里的,还有区委书记凌曙同志。
“这个水库也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产物,水库坝址你是知道的,本来水电组有个意见,要在这里修一个混凝土重力坝,但是设计还没有。大跃进以后,一声令下,立即动工,改为沙石土坝上马,说是一定要当年合灰成坝,当年发电,还说这是开发天云山区关键的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水库经过匆促筹备就上马了,一上马就暴露出问题,不说别的,光是从十几里外运粘土,就要运几年,要在当年成坝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里山洪凶猛,地质复杂,根本不适宜于搞土坝。 “这是我们这两个‘屡教不改’的分子,又忍不住了,他俩联名给特区、给省写了信,建议这个水库暂停上马,先创造条件。
这封信发出后,正好反右倾运动开始了,罗群又在汇报思想时对反右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再反下去,要死人的,这样一来,漏子就大了。 “特区领导和水库指挥部抓住罗群的思想汇报和他俩联名写的信,大做文章,在工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的运动,把罗群和凌曙拉到台上,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斗争’,当时为了教育我们,把我们这些本来不在水库上的人也搞去了。
“我又一次看到他站在台上,顺带说一下,主持这次会议的又是罗群的前任,你现在的爱人吴遥同志,那天会议的规模是非常大的,我站在人群里,目不转睛地望着罗群和凌曙,这两个人外貌完全不同你是知道的,一个魁梧奇伟,一个文弱矮小,但奇怪的是,这两个人的神情却完全相同。
他们镇定自若,有时用一种蔑视的眼光看看会议的主持人,有时又用忧虑的眼睛,望着乌云沉沉的天空,有时却又含笑望着土台下的群众们,这两个人啊!
“很快,罗群发现了我,他先是向我笑笑,表示要我不要担心。后来又向我眨眨眼,做了一个手势,又向正在讲话的人呶呶嘴。
我一看,完全明白了,他在暗示后面还有好戏看,他要准备讲话。我见他这样,又是担心,又是兴奋,担心的是怕事情闹大了,对他更不利;兴奋的是他可能要发表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讲,把大家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
我呆呆地望着他,不知道该向他使什么眼色。 “但是这天的会进行不久,就让一阵大雷雨给冲散了。 “山区的雷雨气势是非常惊人的,雷声震撼着大地,象是从山头滚下万吨炸药,轰轰隆隆,震得人发懵,紧连着一场大暴雨也倾盆地下将起来。
“会散了,人们乱嚷着、奔跑着,主持会议的一些人,早已惊惧地躲进指挥部的大工棚去了。就在这时一个压倒雷暴雨的声音在台上响起来了。 “又是罗群!
“他和凌曙号召大家去保卫坝子,抢救器材,这两个钢铁汉子,带头冲进大坝工地去了,他们的一声命令,比什么都灵,人们先是愣了一下,很快潮水似的都涌向大坝工区去了。 “那真是一场惊险的激动人心的战斗。 “然而一场悲剧也就于此发生了。
“大坝被山洪彻底冲垮台了! “凌曙同志,为了抢救人民的财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群众称之为‘我们的好书记,我们的贴心人 ’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今天写到这里,我仍旧止不住我的悲痛。 “令人万分难忍的是,居然不准为凌曙同志召开追悼会!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 “这天一大早,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去找罗群,我知道凌曙有一个在病中的妻子,还有一个不到周岁的女儿。
我想为她们做一点事,可是我走到罗群住的工棚,没有人,我这才发现所有工棚都是空的。冷飕飕的秋风,吹得那些棚子边上的荒草簌簌作响,那些红红绿绿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标语,被昨天的雷雨撕裂,倒挂在那里,显得可怜而又可怕。
“我站在那里,心里很凄凉,也很奇怪,人们都到哪儿去了呢?我信步向那大峡谷的斜坡走去,这才看见那山坡上,站着黑压压的人群,那么多人,却没有 什么声音,只有那漫山的松涛声。
我不知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一口气跑了过去。到了人群边上,我猛然止住步,在庄严肃穆的气氛里,我也低下了头! “原来这里正在哀悼凌曙同志。没有哀乐,没有灵堂,有的只是低低的啜泣的声音!我心里一酸,止不住想哭,我忽然听见我最熟悉的声音在讲话。
我抬头看过去,罗群站在凌曙同志的新坟旁边。 “他说:‘他是属于人民的,他是不应该死的。昨天那些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还在批判他,把什么右倾的帽子,戴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身上。
他是什么右倾?他不过说了共产党员应该说的真话,同志们,乡亲们,你们想想看,自从去年以来,我们在天云山区干了多少蠢事?我们不是在搞建设,是在败坏我们正在兴旺发达的革命事业。现在正是应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反右倾?这样反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将要遭受不可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在这里说,我也要给我们亲爱的党和毛主席说,我们不改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就是罗群当时说的话,这就是他的反革命行为的全部。
就是这一番话,和他的思想汇报,使罗群的问题层层加码,一直影响到现在。可是,这难道是一个反革命能说出的语言吗?如不是对党出自衷心的热爱,能敢于发表这样的意见吗?当时,罗群是泪流满面说的,这个硬汉子,我从来没见他这样哭过,他哭,群众也哭,我也哭。
“就在这哭声里,来了几个人,不由分说把罗群架走了。 “群众惊呆了,我也惊呆了,我跌跌撞撞跟了上去,但是几只手抓住了我,厉声问我要干什么,他们毫不留情地把我推倒在地上。
几个同志上来扶起我,他们又同情又担忧地望着我,他们第一次发现我和罗群有了非同寻常的感。 “这天晚上,我怀着极度的痛苦,坐在我和你一同睡过的那间房里,就是在这房里,你曾向我倾吐过你对罗群的深深的爱,就是在这房里,我们不断响起欢乐的青春的笑声,也就是在这房里,我们谈到对党对事业对爱情都应无限忠贞。
可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面对着悠悠明月和那唧唧虫鸣。 “我不知自己该怎么办,我怕罗群会被投进大牢,我怕我会永远失去了他。
我忽然想起,有人对我说过,吴遥在热烈地追求你,给你做说客的正是我们特区的第一把手,而第一把手又是你的老上级。那时你虽因不愿回天云山而调到别的市工作,但你是可以替罗群说话的,也许你已后悔你发出的信,也许你还在暗地里爱着罗群,假使你愿意来救救罗群,而你们又能重新结合的话,即使我永远失去了他,我也将是欢乐的!
“正是怀着这种心情,我才请了假去找你的,当你拒绝见我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是多么幼稚啊!
“对去找你这一段遭遇,恕我不写了吧,事隔多年,讲它仍旧是痛苦的,但是我仍感谢这段生活对我的启发,它使我有勇气有决心走我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从你那回来后,一件重大的变故,倒是促成了我的愿望,天云山特区被宣布撤销了,我们工作将重新分配。
也许就是因为撤销了这个特区,也许是有正义感的同志坚持,我获悉罗群只被开除了公职,仍旧放回原地监督劳动。开除公职,这本来是够惨了的,但是对我来说,倒是一个件值得庆幸的事,他只要不坐大牢,他的那些重要的研究计划,就有可能实现,而我也应当帮助他来实现。
“我向组织上要求,留在天云山区,教书或是搞地方上的科技工作都行,我这个要求很低,通过倒也顺利。
这样,我很快就到了一个乡村小学,安顿了一下,就找到公社党委,要求把罗群放到我们学校所在的生产队。当时的公社党委负责人,是凌曙的老部下,他不仅同意,而且给我提供了不少方便。这也证明,绝大 多数人,是非观念在内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我知道罗群正在病着,病得很重,我要了一辆板车赶到了他所在的生产队。 “这时正是一九五九年的最后几天,天冷得要命,阴沉沉的就要下雪了,那条瀑布仿佛冻结了似的,没有那种气势雄浑的轰鸣了,我把板车放在村口,找到了罗群的住处。
我看见他正躺在他那薄薄的行军被上,发着高烧。房里再没有人,只有老乡送来的面条和水,放在他的床头。 “我悄悄坐下来,看着他那明显消瘦了的脸,看着他房里的凄凉景象,看着他紧紧闭着的眼睛和枕边的钢笔、本子,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种又酸又苦又甜的东西,涌上心头,两行热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滴在他的被上、脸上,…… “他睁开了眼睛。
“他怔怔地望着我,我哽咽得不能出声。
他抬起头,他的眼睛突然亮起来,我从泪眼模糊中看到他那最真最柔并且充满着惊异的眼光,就象我明白我自己的内心一样,我明白了他的心。 “他把手从被里伸出来,轻轻地说: ‘你来了,亲爱的人!
’我一下伏到他的身上,我继续哭泣着。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我们的心彻底地贴在一起了。 “宋薇同志,我们就是这样结合的。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但是我同时也坚定地认为,有两颗互相温暖的心,有明确而崇高的目标,一切艰难险阻都是可以战胜的。
那天,我自己拉着板车,板车上躺着我的爱人,我们迎着寒冷的风雪,在古城堡下的路上前进着。许多人都用惊异的眼光望着我,我挺起胸骄傲地往前走着,不时回头和他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我感到真正的幸福是属于我们的!
“从这以后,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经济上,我们是穷困的,有时候窘迫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我只有那么点工资,我、罗群还有凌曙的女儿,我们亲爱的小凌云,--因为她妈妈也去世了,我们的一切,就在这几十元里面,我们不光是吃饭穿衣,而且还是要买书、要研究资料,有时候为了买一些我们急需的书,我们要一个月决心不吃菜,只用一点点盐水萝卜下饭。
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昂扬而极为丰富的。
白天我教孩子们的书,他或是写作,或是去作调查,或是找些老乡聊天。一到晚上,我们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特别是社会上的现实情况,都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有时我们也进行辩论,或是研究他当天所写出的文稿,这时的罗群,毫不夸张地说,他已经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学者了,而我则成为他的忠实助手,我是他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又是第一个批评者。
这个时期,罗群的干劲和毅力确是惊人的,他经常通宵达旦,第二天脸一洗又开始工作。
他的情绪始终是乐观的,有时,我埋怨、牢骚,他反过来劝我,他说:‘别这样,晴岚,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要不我们是为什么而工作而生活呢?我们的遭遇,是暂时的现象,总有一天,党会纠正这些问题的。
对我们的遭遇,也要看怎么看,这件事当然是件痛心的事,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呢,它又给了我们在上面所不能得到的条件,我有时间,我能接近人民,能体会到一些人所体会不到的东西,何况,我还有你,我倒觉得生活待我也不算太薄了。
’ “他就是这样对待生活的! “但是他对于问题的看法却始终是不动摇、不妥协的。一九六二年,曾经有人劝他对五七年五八年和五九年的言论和行动,做一些检讨,争取改变处分。
但他始终不同意,他坚持认为,那是左的危害,而不是什么右。 “正是因为他坚持了这些观点,他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升级了,林彪、四人帮把左的路线,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峰,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对罗群的迫害,其手段之毒辣卑鄙,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我,也跟着受到了最残酷的折磨,要不是我们对党对人民有着坚强的信念,我们早已不在人世了!
“宋薇同志:你读到这里,也许奇怪,我为什么要写得这么长,这么具体,甚至这么噜苏,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是连罗群也一直隐瞒着的。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进一步迫害,我的身体被彻底摧残垮了,我现在随时有死亡的可能,这件事当然是我极不希望的,曙光已经出现,航向已经拨转,大是大非正在澄清,四个现代化正在开始,罗群的问题最多也不会拖到明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前进的历史车轮谁也不能让它逆转。
在这个我和罗群盼望了多年的时刻,谈到死,当然是极不愉快的。 “但是我们毕竟是信仰唯物论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谁也否认不了它。我的病是在林彪、四人帮又给罗群加了顶反革命帽子,又把他关到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而得的。
我为了救他的书和著作,在老乡的协助下,冒着暴风雨,把他的东西,运到一个山洞里,又为了保存它们,忍受最难忍受的侮辱和鞭打,最后,把我和罗群绑在一起,跪在烂泥里几天几夜。从那时起我就得了病,这种病又因四人帮统治的时间太长,使我得不到医治,现在已难以医治了。
“因此,我这封信不得不写得长些,你我毕竟曾经是呼吸与共的朋友,尽管我们的命运是如此不同,有一些心里话,还是想和你说的,同时,我也相信,经过这十年的惨痛历史教训,你这个本质不坏而又聪明的人,一定也能正确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自己的鲜明态度。
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我们的革命先辈,你也一定会在新的长征路上迈开新的脚步! “关于你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知道得太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至于我,就象一开始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即便我今天就离开人世,我也敢骄傲地宣告,我是幸福的。 晴岚 七八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