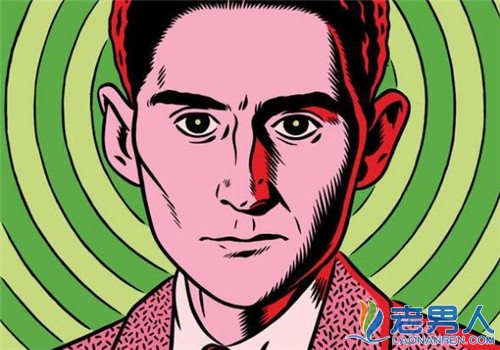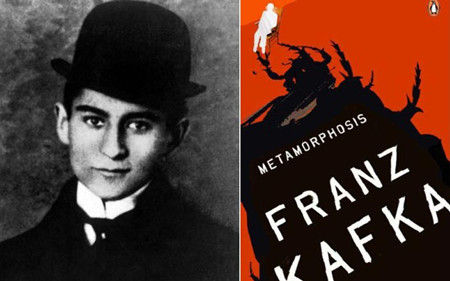晚年卡夫卡痛苦绝望 立遗嘱焚毁所有作品
[摘要]晚年的卡夫卡还是一直与父亲格格不入,生活还是那样的无聊和寂寞。恐怕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才成就了这位现代小说之父。马特利阿里疗养院的治疗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8个月的时间里,卡夫卡仅仅增长了8千克,而结核病则远远没有治愈。1921年8月,他回到布拉格,那里的一切都没有变样。
他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继续同克洛普施托克这样的新朋友及闵策艾斯纳这样的老朋友通信,他也再一次体会到他所厌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回家后不久,他就给妹妹艾丽写信,就她提出的关于孩子择校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在回信中,卡夫卡表达他对父母和孩子的问题的一些看法。卡夫卡希望艾丽的孩子们能避免布拉格富裕的犹太人的孩子们常见的命运,染上“渺小、肮脏、冷漠、偏颇的精神”。
在卡夫卡写给艾丽的几封信中,他声称:“孩子们可以拯救他们的父母”,并且补充说,“从理论上,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不要孩子的人。”但他又引用了斯威夫特的话:“在孩子的教育方面,父母是最不可信赖的人。”卡夫卡认为家庭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极其复杂且不稳定的有机体”,在家庭中,父母“剥夺了孩子的个性权利”,仅仅为“遵守某些要求的某些人”留下了空间。
就卡夫卡而言(他已经38岁了,又回到了父母身边,但他和家庭的一切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父母的自私自利这是父母真实的情感是没有限度的……专制或奴役是父母的两种教育方法,它们都带有自私自利的性质。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兽性的、愚蠢的,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孩子身上……怀疑是布拉格教育的失误之处。”卡夫卡谴责说:“装饰华美的房间里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有毒的、危及孩子的空气。”他似乎是回到布拉格来复仇的。
正是在这种了无生气的心境中,1921年初秋,卡夫卡草拟了他的第一份遗嘱,要求他的朋友布洛德在他死后焚毁他的全部作品。一连几个月以来,卡夫卡很少写作。10月15日,他重新开始写日记,此前不久他刚把自己以前的日记都交给了米伦娜。卡夫卡回到布拉格后,米伦娜曾到他的父母家几次拜访他。
这次,他决心写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日记,内容不再过分关注他在单身生活的痛苦:“这方面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健忘了,我的记忆力又活跃起来,并因此而失眠。”他利用日记给自己开辟了一块空间,从那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同那显然不可治愈的疾病的关系中,他占据着什么位置;他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到,于是放眼观察前面的地形。
他感到了“不得不开始的痛苦”。当他在公园里看到年轻的女人时,他发现自己没有丝毫的爱慕之心,他曾“多次想过和她们共享幸福,也曾多次意识到我过于虚弱不配享有这种幸福,愚蠢地认为我看透了自己和她们”。
面对着虚弱的身体,卡夫卡决定不向绝望屈服。他痛苦地感到,他已经纵容自己堕落成“一个身体上的废人”,因为他“不想被生活乐趣所吸引,而这种乐趣对一个健康的男人来说是必要的,就好像疾病和绝望还不够吸引人似的”。他同样嫉妒所有已婚夫妇。
有时卡夫卡也会暂停对这些精神账目的清理,走出自己的房间,试着和家人接触。一天晚上,他的父母像往常一样打牌。“我坐在一边,完全像个陌生人一样;我父亲要我玩一把,或者至少看他们玩;我编了个理由拒绝了。从童年开始,我就常常重复着这样的拒绝,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冷静的自省中,卡夫卡仿佛从他本人中抽离出来,安静地旁观着。
从这件事情来看,当我抱怨生活的涌流从来不会顾及我,我从来没有逃出布拉格,别人从来没有教我学会一项运动或做生意等等时,我是错误的我本来不该像拒绝打牌一样,拒绝每个提议。我只让荒谬的事物占据我的注意力:法律学习,办公室的工作以及后来做的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比如园艺、木匠活等……或许是出于总体上的软弱,尤其是意志上的软弱,我总是拒绝。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卡夫卡表现出对玩牌的兴趣,同意帮他的母亲记录分数“但亲密感并没有因此产生。”他只是感到无聊,后悔不该浪费时间。
l921年底,卡夫卡通过阅读托尔斯泰那部阴郁的著作《伊凡伊里奇之死》安慰自己。
1922年1月,卡夫卡的状态很差。他常常发烧,体重也减轻了,不过他的健康状况并未严重恶化。1月底,他的医生准备和家人一起去紧靠波兰的斯平德尔莫法尔度假胜地,建议他一起去。1921年10月,赫尔曼医生曾给卡夫卡看过病,诊断他患有肺粘膜炎,并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案,要求卡夫卡休3个月的病假。
大概在这段时期,卡夫卡开始写作小说《第一次痛苦》,这篇小说发表在他最后一部作品集《饥饿艺术家》中。小说讲述了马戏团的空中飞人的故事,为了使自己的技艺尽善尽美,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日日夜夜都在高空生活,始终保持训练状态,他的一切生活需求都要靠底下的勤杂人员满足,后者守在秋千下,把空中飞人所需要的一切物品用特制的容器递上拉下。同那些为自己的天职献身的孤独的艺术家一样,空中飞人与人们很少来往,有时他也有点让人厌烦他的存在干扰了其他节目的演出但由于他技艺高超,马戏团的头都能原谅他。假如不是需要到各地巡回演出(或许就像卡夫卡本人不得不同外部世界来往、去办公室上班一样),空中飞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满意的。
这是一篇典型的卡夫卡式的短篇小说:以完美精确、一目了然的现实主义叙述来描述荒诞、虚构的故事。它带有明显的戏剧性和表现主义色彩,这正是卡夫卡小说的风格特点。
1922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在去斯平德尔莫法尔休假之前,按照卡夫卡自己的说法,他似乎“崩溃”了,他的身体状况极差,同1920年初去美兰之前一样。他写道:“一切好像都终结了。”他无法入睡,“无法忍受生活”,似乎身体内部和外部的时钟走得不一致:“内部的那个时钟发疯似的,或者说着魔似的,或者说不知何故以一种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外部的那个则以平常的速度不紧不慢地走着。”他解释说,“内部时钟那狂热的速度”是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的内省的结果。他之所以崩溃,原因也在于他的与世隔绝:“在很大程度上孤独是强加给我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自找的但如果没有外界的强加又会怎样呢?现在这种孤独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它正在走向结局。那么结局是什么呢?最有可能的是疯狂。”他试着使自己乐天安命,“满足地栖息于片刻之中”,承认目前的状况之所以显得如此可怕,原因仅仅是对未来的恐惧。他尝试思考生活中另一个主要问题:结婚愿望的落空,并自问:“你是怎么利用你在性上的天赋的?”这件事原本可以“轻易成功”,仅仅是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才使一切计划破产不过,实际上事实并不像他说得那么简单。他觉得“性在侵蚀着我,日夜不停地追逐我,我原本应该战胜恐惧、羞耻心、也许还有痛苦,去满足它”。
尽管卡夫卡竭力抨击家庭生活,但一想到自己从未尝过做父亲的滋味“和孩子的母亲一起坐在摇篮前那种无限的、深沉的、温暖的幸福”他就觉得痛苦,感到可怕的匮乏。卡夫卡以前在使用“疯狂”和“精神错乱”这些词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它们当作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他后来告诉布洛德,这个时期他差不多要发疯了,他的遗嘱也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或许布洛德正是据此才没有按要求执行遗嘱。
1922年1月27日,卡夫卡去了斯平德尔莫法尔,出发之前他曾给当地一家旅馆写过信,用自己的名字预定了房间,但到达旅馆后他发现登记簿上留的名字竟是“约瑟夫K”。在那里,他坐雪橇、登山,甚至尝试滑雪。然而,他感到自己不能和任何人交上朋友,“我看到一群人快活地聚集在一起,感到无限惊讶。”在斯平德尔莫法尔,他和l月初一样写下了大量的日记,无情地对他自己、他特殊的命运进行剖析。他再一次想到他的父亲,认为他之所以同世界格格不入,是因为父亲“不让我进入这个世界,这是他的世界”。他借用《圣经》比喻自己是一个被父亲驱逐,不得不离开家园,到处流亡迁徙的人。
尽管卡夫卡从斯平德尔莫法尔给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卡夫卡帮助克洛普施托克办了一张护照,使他得以到布拉格工作)和闵策艾斯纳等人寄的明信片语调欢快,但他的日记却是一如既往地阴郁。在他看来,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境遇是“可怕的,独自一人待在斯平德尔莫法尔,暗夜里在一条废弃的路上滑雪,这是一条毫无意义的道路,这条路上没有一个现世的目标”。茫茫的雪地,莫名其妙地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确定的“现世目标”(暗示出还存在另一个更美好的非现世的目标)卡夫卡的处境同《城堡》(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约瑟夫K在小说开篇的处境何其相似。卡夫卡很可能是在1922年1月到达斯平德尔莫法尔之后才开始写作这部小说的。卡夫卡对自己说:“我喜欢恋人但却不能恋爱”,“我生活在别处”,不过“人世的吸引力是如此巨大,它能在一瞬间使我忘记一切”,“那些爱我的人之所以爱我,是因为我‘孤独无依’。”假如米伦娜突然到这里来,那将是非常“恐怖”的,因为那会使他陷入一个他无法生存的世界中去。
毫无疑问,疾病使卡夫卡过分耽溺于这些消极的思想,使他认为自己无法把握“人世”。他觉得“消极”像幽灵一样缠着他,每当他的生活中出现一些积极的因素,马上就会有一种力量挫败他,使他情绪低落。
尽管卡夫卡的病假5月4日才到期,但2月18日左右,卡夫卡就离开斯平德尔莫法尔,回到了布拉格,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没有任何好转。
不过,更重要的是,“为了在大家称之为‘神经’的东西前解救自己”,他又开始写作了。“我在一段时间以来开始写点东西了,大约从晚上七点起就坐在写字台旁,但这都没有用,就像在世界大战中想用指甲挖出一座防空洞一样。”他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创作力,因此他抓住每个机会来写作。除了《城堡》之外,他同时还在写另一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同作品中的饥饿艺术家一样,卡夫卡在这个时期写下的日记和信件都表现出孤独绝望的情绪,渴望被人理解。“如果窒息而死会怎样呢?”卡夫卡写道:“偶尔我也会离此不远……攀上攻击你的人的马背,并靠自己的力量驾驭这匹马。这是唯一一种可能性。”
3月15日,卡夫卡给布洛德朗读了《城堡》的第一章。这年春天余下的日子和整个夏天,他都在继续写作这部小说,到1922年8月又把它搁置一旁,此后再也没有修改过,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城堡》。
这段时间,卡夫卡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奥培尔特大楼,继续写作《城堡》,他本来以为5月4日就得回到办公室上班,但在4月17日他向公司提出申请,要求休完病假后接着续上自己五个星期的年假。保险公司批准他的申请,这就意味着他应该在6月8日回去上班,但是他的身体状态极差,于是6月7日,他终于决定提出退休申请。6月30日,他接到保险公司的通知,从次日起他就正式退休了,退休金为每月1000克朗。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终于结束了。不过,尽管卡夫卡不断抱怨他的工作削弱了他用来创作的精力,但他知道它同样为他提供了帮助,使他能够把握日常生活,而且为他的存在赋予了某种外在形式。无论他的内心如何困惑、茫然,从外表上看他永远是一个谨小慎微、踏实能干、受人欢迎的高级职员。
退休之后,卡夫卡立刻决定搬去和奥特拉一家同住,后者刚刚在布拉格南部60英里外的普拉纳小镇上租了一座房子度假。卡夫卡终于不再担心办公室的工作,可以毫无内疚地休假了。他知道他病得很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个事实:他活不了两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