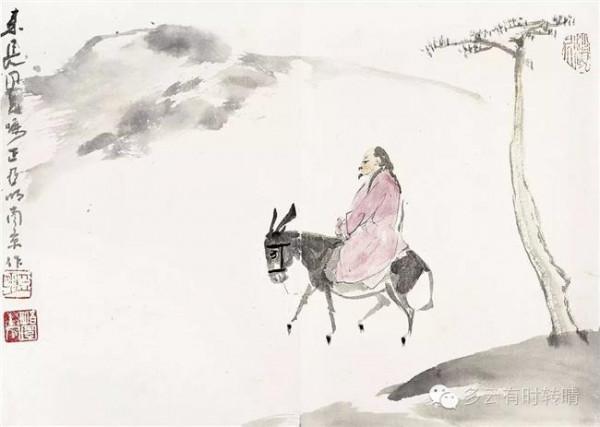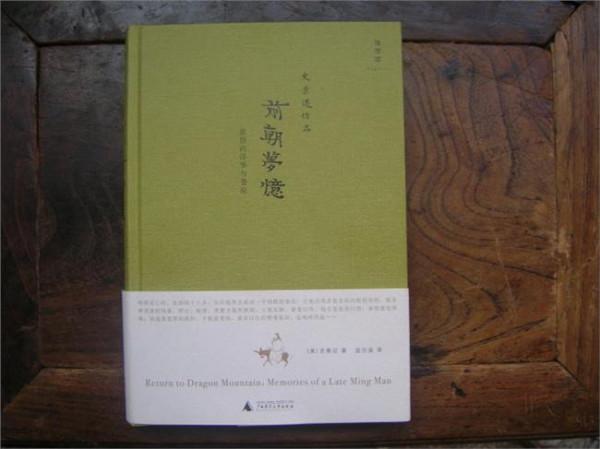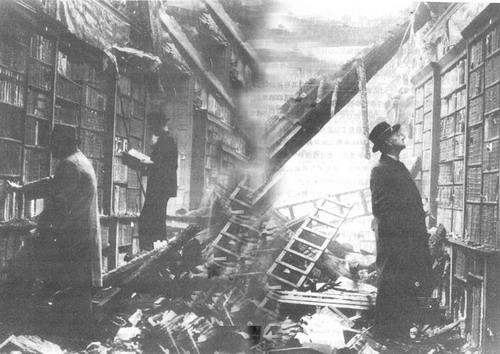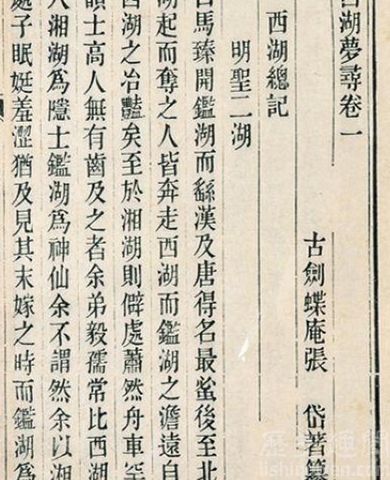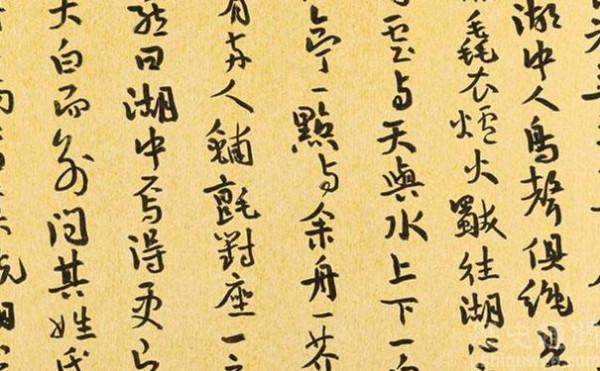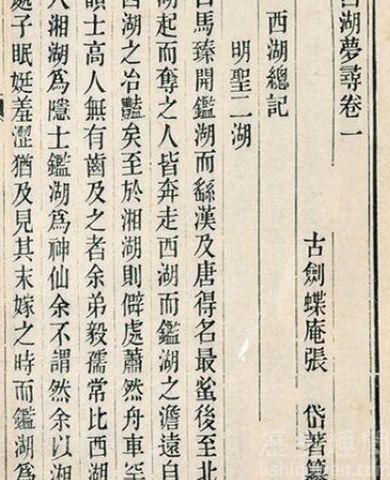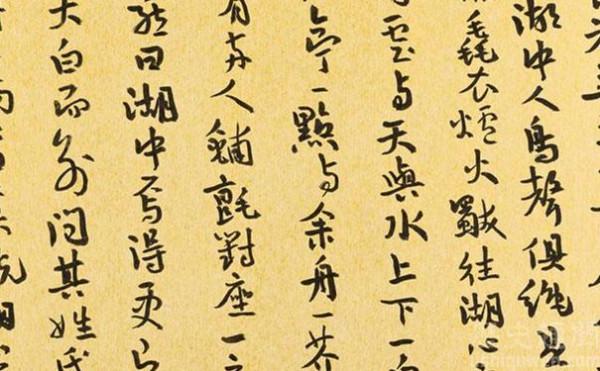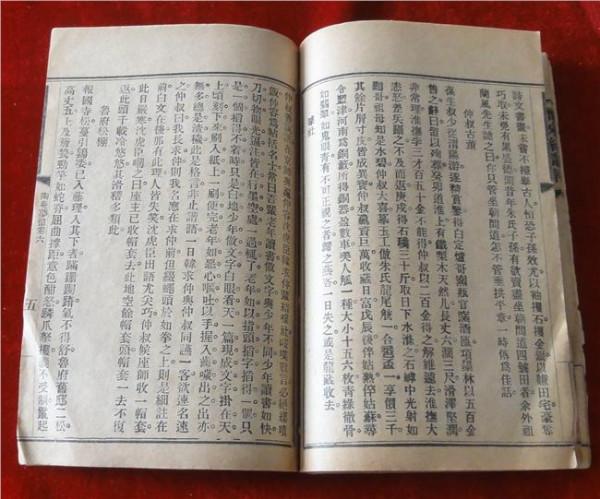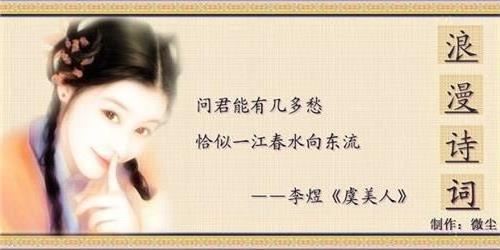张岱的作品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史景迁作品)(精装 )
大主考李九我清点了试卷数目,发现少了七份卷子,于是就问教谕是怎么回事。教谕答说:“七卷大不通,留作笑资耳。”李九我命其找出这七份卷子,照张岱的说法,“公一见,抚掌称大妙,洗卷更置丹铅。
易经以大父拟元,龚三益次之,其余悉置高等”。 主考李九我虽然有意把张汝霖放在榜首,但是“南例无胄子元者”,官员的长子不能放在榜首,这是南方的惯例,所以大主考李九我就以龚三益抡元,张汝霖放在第六位。
后来李九我对别人说,这么做有违自己的良心,“此瞒心昧己事也”。科考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上榜的考生要向主试考官表示谢意。
张汝霖也照规矩行事,“揭榜后,大父往谒房师(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教谕),房师阖门拒之日:‘子非我门人也,无溷我。’” 三年考一次的乡试一如进京会试,过程复杂,规矩又多,应试的考生有数百乃至上千之多,耗时数日,显然张岱为求叙述精彩而把过程简化了一些。
但重点是主考官李九我能随机应变,又能惜才,教谕则是照章办事,不知变通,容不得考生有异见。幸好张汝霖的才情能获得赏识,脱颖而出。
如果被打入冷官的这七份卷子果真写得很好,这或许说明了教谕对向来囊括榜单的绍兴人心存偏见,要不然就是他有特定的人选想呈给主考官。张汝霖后来当官,也做了主考,便特别留心榜单以外的考生,是否有遗珠之士,但是最后却因时常力排众议,而遭到解职。
” 张岱笔下的文人世界充斥各种矛盾:一边是令人目眩的名望与机会,一边是郁闷、沮丧,甚至肉体的衰亡。
张岱继续细数参加科举的族人,父亲张耀芳也经历类似的困顿与疾病纠缠。说到这里,张岱的语调更为粗涩,父亲早年生活顺遂,但随即困顿。万历二年(1574),张耀芳生在绍兴,自幼“灵敏”,很早就开始读书,“九岁即通人道”。
张耀芳十四岁就取得生员,有资格参加乡试。但之后将近四十年,张耀芳都是在埋首苦读。幼年对读书的热爱,如今转为抑郁牢骚,使得他情绪低落、为胃疾所苦,视力也几乎失去——或许是因为遗传父亲的眼疾。
张岱还在私塾念书时,父亲“双瞳既吒”,已近乎眼盲,但仍然读书不辍。张岱后来写道:“漆漆作蝇头小楷,盖亦乐此不为疲也。”显然是刚从外国传来的科技救了张耀芳的视力,“犹以西洋镜挂鼻端”,让他又能读书,到了五十三岁,才终于上了乡试副榜。
根据张岱的记述,他的叔伯各有因应科考之道。像是季叔烨芳”曾仔细看过亲戚为了科考所读的书,颇为不齿,“徒尔尔,亦何极?”但是张烨芳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耐,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下帷读书,凡三年,业大成”。
但张烨芳还是无意功名,也从未尝试,过着挥霍不羁的生活。更复杂的是张岱九叔(九山)与十叔(煜芳)的关系。十叔显然占了一些优势,“少孤,母陈太君钟爱,性刚愎,难与语。
及长,乖戾益甚,然好学,能文章,弱冠补博士弟子”。主考官从众考生之中选了张煜芳,提供津贴,让他去考乡试,长达三十多年。但是,这么优渥舒服的日子并没有稍解张煜芳的坏脾气。
崇祯六年,张煜芳的九兄张九山中进士第,有旌旗匾额送至,挂在家门之上,惹得他语带轻蔑骂道:“区区鳖进士,怎入得我紫渊(十叔的号)眼内!”照张岱的描述,十叔张煜芳“裂其旗,作厮养挥,锯其干,作薪炊饭,碎其扁,取束诸栅”。
张煜芳虽然脾气暴躁,管不住自己,又善妒成性,但他对于科举制度本身显然并不仇视。过了十二年后,崇祯十三年(1640),朝廷欲收天下人才,以解决燃眉弊端,于是就下令吏部破格开科进用,结果张煜芳名列特科二等第十九名,补刑部贵州司主事一职。
” 那么,张煜芳的学问如何呢?张岱则是一语带过:“紫渊叔刚戾执拗,至不可与接谈,则叔一妄人也。
乃好读书,手不释卷,其所为文,又细润缜密,则叔又非妄人也。”意思是说张煜芳脾气暴躁,别人很难跟他说话。但是他又喜欢读书,文笔“细润缜密”,由此来看,他又不是个“妄人”。
诸如此类的矛盾,竟然集勤学与暴戾于一身。 我们从张岱祖父、父亲的生平可看到,张家学子多有失明之虞。祖父是以处暗室以恢复视力,父亲靠的则是眼镜。
明朝时已可买到眼镜,一副眼镜值白银四两。但是比张岱小十岁左右的堂弟张培在五岁便双目失明,药石罔效。根据张岱的说法,失明的原因不是日夜苦读,而是张培喜欢吃甜食,加上亲戚纵容,这孩子要吃什么甜的,全都顺他的意。等到大人察觉张培的视力迅速退化时,就算是祖母“费数千金”,求遍天下名医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