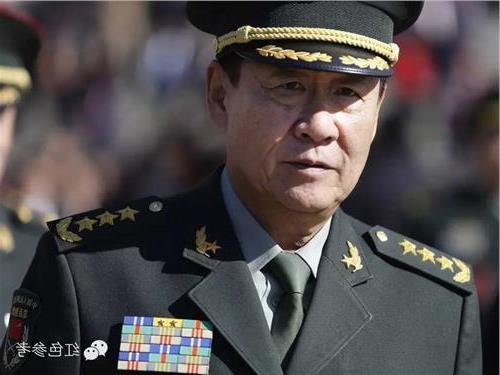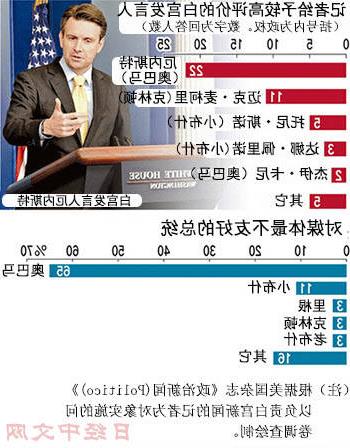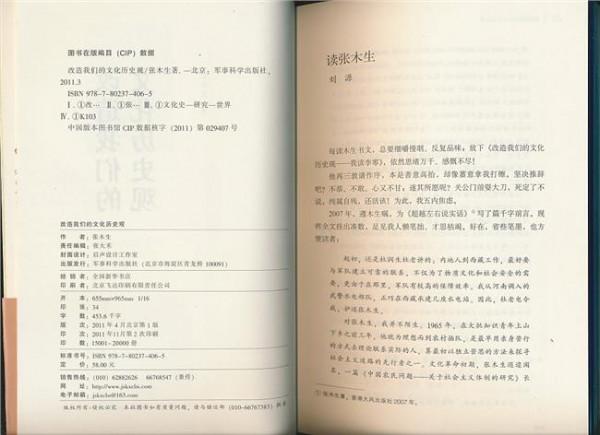红二代发言人张木生 黄纪苏在成都近代史讨论会上的发言
十月上旬在成都近代史讨论会上的发言
纪苏案:十月八到十二号,杨帆、李伟东在四川建安博物馆召开了近代史讨论会。李伟东、杨帆、秦晖、张木生、曹锦清、萧功秦、徐友渔、祝东力、刘仰、吴伟诸位都做了发言。这次会议在我参加过的会议中算是比较认真的一次,而且能有交流。我把自己的发言集中一下,发表在这里。其他地方根据录音整理的也许准确也许不准。
(以下针对李伟东的发言)
我觉得这两年的确有这么一种倾向,这只是我的个人观察,你所说的左翼的三拨人,像老左派本来就是体制的一部分。但民间左翼相对体制是边缘化的。从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像乌有之乡所代表的左翼思潮,他们离体制比较远,不是主流。这时候经济自由主义是主流。但我的感觉,这些年,左翼的确开始出现精英化、向国家主义靠拢的趋势。与此同时,近十年自由主义倒有一个民粹化的趋向。这种相反的趋势耐人寻味。民粹化的自由派一开始维权,维的还是陕北油田老板、东北黑老大刘涌之类,这些年也开始维拆迁户什么的权了。左右都有变化甚至分化。至于怎么评价则是另外一回事。
仇官仇富算左还算右?赵本山开了私人飞机,很多人上去骂,有的骂共,有的骂资,共产党和资本家确实难解难分。越往下越混沌越本能,越往上越抽象越流派,其实底下左和右是不太分的。他们主要是现在毕业又失业的学生,不包干分配,基本上是文化民工、知识民工的状态。他们可以说是自由派和左派的共同一块社会基础。
(以下针对秦晖的发言)
萧老师说到史学的功能,说到革命史学。中国人不能说没宗教,但总体来说宗教性不强,但历史感挺强,把历史当做思考现实和未来的重要参照,回顾就是前瞻,近代史尤其承担这种功能。萧老师刚才说到历史学是一门经验的学问,这很对。
人类社会经验的特点是普遍性不强,不像自然科学或工业,自由落体运动放南美和北欧全都一样,但人类社会确实没有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严格地说,人类社会没有规律(law),只有准规律,相似性之类(pattern, regularity)。
到了近代社会,变量越来越多,新的增量越来越多,诸如科学、工业乃至最近的互联网。在二十年多年前互联网没普及的时候,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的认识和预测肯定跟今天的的实际情形有不小的距离。
对于新变量剧增的近代一百年来说,当代史最难把握,但也最重要。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今天该怎么“参照”当代之前的辛亥革命,以及更远的“周秦之变”,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既不能历史虚无,又不能刻舟求剑。我扯远了点。
秦晖老师姓秦而反秦,反得很彻底。秦老师实际上说了三种“秦”,第一个是战国的秦,第二个是两千年的秦制,第三个是今天的什么“权威主义”、“大政府”之类——希望我没误读秦晖老师。我比较同意萧功秦老师的近代史大思路,那就是对外部危机的反应,这是一种比较传统也比较实在的认识。
这个大危机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哪个文化可以抵挡得住。清在历代王朝里算是好的,再烂也烂不过明,清朝的“中兴之臣”如曾、左、李、胡,解决传统王朝周期的问题,都是够格的。
但是他们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这样一个大危机,要把中国从这个沟里带出来,其实他们都力所难及,历史上的明君贤相,把谁搁那儿也不行。
清亡之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等于是将近四十年的国家分裂,这个国家分裂局面差不多就跟刚才秦老师和萧老师所说的战国很相像,国内像,国际体系更是虎狼世界。中国要想在虎狼世界中站住脚,就必须结束内部分裂局面。
哪条道路,哪种社会政治力量,那种社会政治哲学,哪种人生哲学,哪种道德,哪种美学,总之哪种东西有利于把中国带出去,哪种东西就有历史合理性,就能胜出。我说“胜出”着重于事实,没说一定就“好”。我很认同秦晖老师的价值观,即自由民主价值观。
但我想说,社会人生有很多价值,这些价值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排行榜。近代中国的价值排行榜上自由民主肯定不是排在第一位。那时要解决分裂问题,解决生存问题。你可以说中国当时并没要亡,但问题是大家都觉得要亡。
决定一个时代需求或道路的,是当时的普遍社会心理,也就是当时大家觉得怎么着。我同意萧老师刚才提到重要观点:晚清以来的碎片化造成了中国革命。从结束国家分裂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这一点来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起的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
记得以前读到秦晖老师一篇文章,说中国人民没等到1949年,在1945年就已经“站起来了”。这话也对也不对。看用什么标准了。要说1949年以后更专制、更不民主、更不自由了,这是事实。但按这个标准,也不用等到1945年,1911年中国就站起来了。我们一般说的“站起来”是结束分裂局面,为国家现代化基础建设提供必要条件。按这个标准,中国在1945年还不算站起来了,因为,各路军阀虽被灭了不少,但桂系滇系什么都还在吧,而且国共是分裂的吧。总之,为了彻底结束晚清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局面,或者你国共谈拢了,或者你国民党把共产党灭了,要不共产党把国民党灭了——今天的史学家在把玩“民国范儿”的同时,也需要平心静气想想为什么就输给共产党了。中国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你所说的、新的“秦制”,也就是共产党高度军事化的政治,高度政治化的经济。对这个新秦制,我一直是抱着历史的、理解的态度。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这个“秦制”就像副作用很大的猛药,是有重大缺陷的,大跃进闯那么大的祸,不应该对体制做深刻反省么?所以,尽管我对这个“秦制”的最初产生和后来发展有肯定有理解,但我并不认为它今天不该改造。
中国今天的形势跟百年前已有很大差别,今天中国的价值排行榜不能还跟百年前一样吧?你总不能说今天的重中之重还是救亡和逃命吧?曹锟时代不宜也不易实施的民主制度,今天您还说不合中国国情,中国得哪辈子才能凑齐您的“国情”啊?其实国情早就今非昔比了,今天中国的外部压力要比那会儿小多了,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有受教育程度比那会儿高多了,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欲望和能力跟杨青天李青天时代也都不能同日而语。
一个日益成长壮大的中产阶级、准中产阶级是需要民主的,民主越来越成为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成为他们相中的价值——他就喜欢你怎么办吧。
再说了,就连如今的秦官秦吏又有几个对秦制有自信呢——有自信他们往外国跑什么呀?他们的不自信其实来自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世界上行秦制的地方越来越少,剩不下几个了。
当然你可以说“少”才“好”呢,但秦官秦吏不这么看问题,他们随大流。总之,面对民主问题,强压是没用的,忽悠也是没用的。
秦制肯定需要改造,但改造不是简单地,就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把毛主席纪念堂拆了原地盖座国会山。尤其不能靠一大帮没心没肺的乌合之众造谣传谣起哄架秧子,这样做只能加固秦制,甚至哪天加出个希特勒都说不定。
刚才萧教授提到《中国不高兴》,我就再多说一句。在全球战国里,秦制的确是有比较有力量的。应该说,过去几十年里,行“秦制”的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是个赢家。
但“中国秦制”或”中国模式”面临两个重大挑战,一是内部的,一是外部的。从内部说,你两级分化到这地步,道德沦丧到这地步,官吏腐败到这地步,人民开始不干了。从外部说,这个让“中国秦制”受益匪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混不下去了。
船要沉了,你拿到头等舱的钥匙又能怎么着?资本主义世界体制本来和中国旧王朝是一样的,改朝换代呗,萧条复苏呗,不存在可持续问题。倒是环境尤其是能源危机把它领进了死胡同:这个体制赖以生存却又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能源,为我们重新思考世界的现状和未来提供了真正的机会,需要比较彻底的解决了。
世界资本主义是个更大的秦制,这个秦制也是需要改造的,至于改造成什么样,我不认为过去的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之类是什么好办法。
未来世界应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中社会主义的成分应该多一些,因为这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尊严,此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种种“主义”也自有其道理,都应有一席之地。《中国不高兴》讲的无非是,世界体系需要大的改造而世界的地主老财又缺少改造的动力,这个动力中国也许有,应为此做好准备,先把自己改造好了。
(以下针对徐友渔的发言)
好多年前跟河南的老袁有过一次讨论。当时聊的话题是公民社会,因为寄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公民社会来制约官僚和资本。老袁说文革时的红卫兵组织实际就是公民社会,对此我不太同意。刚才徐老师说的“人民文革”,跟公民社会有接近的地方。“人民文革”,也就某些群体和个人通过毛提供的文革手段实现自身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替毛主席打到谁,我想肯定是存在的。我们院有个姓沈的伯伯,解放初期就被刘大年他们的整成了右派反党小集团,一直受压制,文革时举旗造反,组织了个“六月天兵征腐恶”战斗队,闹“人民文革”。可没闹几天,就被打回到到了“美国特务”,因为抗战时他给美国军队当过翻译。“社会冲突说”肯定可以解释百分之几十,但解释不了百分之百。毛泽东的确是文革的最重要前提之一,没有这个前提,文革根本不可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文革”也是非常有局限的。毛主席让你们造反,你们就能造;不让你们造了,你们就“广阔天地”呆着着去吧。
关于毛泽东,我跟伟东的看法略有不同。毛泽东可能是近代中国各种身份、各种人格最复杂的一位。就说文革吧,他既是最大的当权派,同时又是最大的造反派,两种身份此起彼伏,打打闹闹,至死方休。先是一路造反,造到武汉7-20事件,下面也要造你这个最大当权派反了,结果又镇压造反派。到了四五天安门事件——那相当于一次全民公投——彻底否定了文革路线。毛的确是社会主义官僚体制的一个异数和悲剧英雄。可以说,文革是为探索社会主义民主而进行的一次代价惨痛的试错,证明此路不通。付出这么大代价的教训再不吸取,还一味起哄,就真没什么意思了。
我不太同意伟东说的、毛要借文革推卸大跃进的责任。因为文革、四清和更早的鸣放,在毛是有一贯之道的。他的确对官僚集团的腐朽非常警惕,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谁不想多坐几代啊?56年他的方法是准西方的民主制衡,即让党外知识分子干官僚,王绍光头些天写了篇很实证的文章,也是社会冲突说,意思是毛泽东要这么干,但工农出身的官僚集团不干了。【以下是我的引申】作为官僚集团的总司令,毛泽东既然不想当光杆司令,也就只好刹车,但要有个交代,于是他忽悠官僚集团说,咱们鸣放是引蛇出洞,后发制人嘛,所谓欲擒故纵,兵道诡也。此言一出,让全国读书人恨毛泽东一直恨到今天,说怎们这么阴狠毒辣呀!可以说,不是最大当权派,毛当不了最大造反派;但既为最大当权派,毛这个造反派也就当不长,当不彻底。这是毛身上诸多矛盾中最重要的一对。
到了四清,他总结了上一次的教训,别党外整党内了,还是官僚自己整自己吧。他当然知道自己整自己谁也下不去手,于是用体制内的这部分整那部分。不疼不痒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官僚还凑合能接受,“整”就不干了,于是四清也是不了了之,共产党的自我纠错机制还是建立不起来,五八年就惹了大祸。到了文革,毛以最大当权派兼任最大造反派拼死一搏,结果更惨。历史这回不知反弹到哪儿去了,中国后来走的极右野蛮资本主义路线,这是最原始的推动力。
我想问徐老师一个问题,他们的“社会冲突”说,即原有的利益冲突借文革再博弈一下,也就是说既有的矛盾是造成和推动文革的原因。我很想知道,文革在多大程度是造成矛盾、派仗的原因呢?本来没多大事,因为文革彼此一斗,从此结了梁子,延绵不绝,这事好像也不少。记得文革中毛泽东曾纳闷工人干嘛要夺权打派仗,说“在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也许本来是没有,但你把大印往地上一扔让大家去抢,这就抢出厉害冲突了。权力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等于各种好处,这拨工人抢到好处就归这拨工人,那拨工人当然就不干了,便也来抢。所以,我很怀疑这些“利益集团”,有不少是文革的结果而非文革的原因。
(以下针对张木生的发言)
“国进民退”的问题今天争论很大。照我看国企的问题不在于“国”是进了还是退了,有垄断还是没垄断,而在于它赚来的钱去哪儿了,这是老百姓真正关心的。老百姓才不会说国企一边呆着去,赶紧把有利地形让给私企吧。国企赚了钱揣兜里,人民还可以理直气壮管它要,私企赚的钱人民打听得着么?因此我不反对国进民退,我只反对国企把钱揣自己兜了——国企老总凭什么一拿拿几千万?就给他五十万顶多一百万,不干滚蛋,我还真就不信找不着人干了。张老师刚才说的社会分红,国企利润进社保、进养老、进医疗,这才是国企本分应当。但目前的问题是“国”为什么要跟自己过意不去、把利益拿出来分给大家呢?就目前而言,危机感也许能、也许不能成为这么做的理由:您再这么贪吃贪喝下去,真可能就把命丢了,要想继续活而且活得好,您就得节食、就得舍宾。重庆方面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打黑社会保护伞、整顿官员、民生工程,都是这意思,简单说,就是要向老百姓让利益。
张老师说的政治改革那块,听着有点太容易了。就说这工会、农会吧,你说得是“共产党领导的”,刚才秦晖老师问了全国总工会,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是你又说那个根本算不上工会。萧功秦老师刚才说到了一种情况,即在独立工会与政府之间居间调停的“法团主义”。不一定非要政府站在哪一方,您就抑强扶弱,两边抹抹平,往中间找找齐就行啊,总比现在工人一闹事您就过去抡警棍强吧?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受教育的人口里越来越大,尤其是那些人文知识分子,比如干媒体的、搞艺术的、弄文史社会科学的,他的生存方式、他们的尊严直接依赖于言论自由,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生存需求,你不能不解决,更不能不在乎,因为他们的力量真的也不小啊。解决他们的问题,一点不比解决经济问题容易。
(以下针对萧功秦的发言)
刚才萧教授的分类跟你对国家主义的定义是有关系的,因为你认为国家主义就是民族主义,二者是重叠的。【萧功秦:在中国,这两者重叠很高,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国家主义重叠程度很高】你的“国家主义”基本是对外的,但国家主义更是对内的。
中国的格局里有官、商、民这三块。民,也就是老百姓,并不必然选择什么。但当他自己争不到公平,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时,他会希望现成的官僚体系里出强人,如普京,再厉害点的毛泽东,甚至更狠点的希特勒。
魏玛政权末期德国失业人口多达七百万,只能靠强人强政府了。这当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对当时的德国人民来说,肯定比没工作、有了上顿没下顿强。以今天中国的情况,社会不公、道德沦丧、官僚腐败,也就是杨帆昨天最后提的那个问题,如果官僚不让出利益、资产阶级不让出利益,还成天富二代官二代嚣张成那样,会逼得老百姓别无选择,只能在官僚找靠山找青天。
老百姓虽然恨官,他还是盼官,盼好官清官。他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这不可能。
老百姓不会希望国家把好处都让给资本家——国家的钱起码名义上还算老百姓的,钱进资本家兜里跟老百姓就拜拜了。所以别指望着老百姓会支持资本家。如果中国的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就是不让利益,一条道走到黑,民间可能会出现而且已经出现了对强人对普京对毛泽东的强大需求。
这是老百姓最便利也是最自然的选择。我是不希望中国朝那儿走的,因为过去的教训太大了。中国的官和商要让一让,你不让,那到最后就只剩下强人和底层相结合的选择了。
中国和世界都再次进入未定之天,未来是一个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里,知识分子要能不被旗帜遮挡视野,不被主义限制思路。张木生老师的新民主主义是一个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