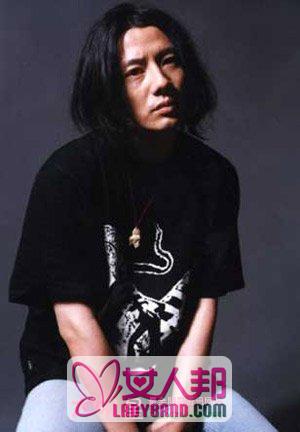郑钧:如果没这几年的改变,我早上吊自杀了
郑钧
五月初的北京总是阳光明媚。从张自忠路地铁站出来不远,就是历史感浓重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在旧址外侧围墙的不起眼处,有一扇小门,门里的空间并不宽敞,光线也总是阴暗着,与外面的景象格格不入。不过,这里却是京城最有名的Livehouse之一——愚公移山。这天,郑钧像往常一样戴着黑墨镜、穿着黑外套,出现在了这里,为他即将在6月24日首都体育馆举行的“私奔”演唱会启动新闻发布会。
说起来,郑钧已经七年没在北京开过个唱了。在这七年里,他并没有闲着——创办音乐创作平台“合音量”、和国外专业团队共同制作动画电影《摇滚藏獒》、和儿子Jagger登上亲子节目,同时也写出了《作》《风马》等几首高质量的单曲……今年刚满50岁的郑钧,已经不仅仅是个歌手,他还身兼着老板、电影人、丈夫和父亲等多重角色。
不过,当拂去诸多标签,如今坐在新京报记者对面的郑钧,讲起话来却尤为云淡风轻,这与当年那个“躁起来”的摇滚青年,显然无法重合。对于这种放松的状态,他说,这要得益于每天清晨那雷打不动的禅修和瑜伽,“现在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轻松快乐的阶段。这种半僧人式的生活方式对我帮助很大,也让我明白了怎么驾驭自己的生活。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虽然可能在别人看来很不错,但实际上是走到哪儿,算哪儿;而现在的我是自由的,开着自己的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在郑钧这次的北京演唱会上,将作为嘉宾现身的,是和他一样同为中国摇滚圈的美男代表——高旗。
郑钧和高旗已经结识许多年,而据郑钧透露,在刚见面那会儿,二人多半情况下都是不清醒的——在周围都是美酒加美女的各种酒吧里,一群乐手总是晃荡着酒瓶,干杯到天亮,《回到拉萨》就是诞生于那段日子。不过,“老高身上没江湖气”,郑钧说,“我也是这样,江湖不了。其实还是跟有些人玩不到一块儿,因为骨子里还是有读书人的感觉在。”
郑钧和妻子刘芸
这种天生自带的读书人气场,大概离不开郑钧的成长环境——1967年,郑钧出生于陕西西安的一个大户人家,爷爷郑自毅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传奇人物,而陕西省博物馆旁,就是郑钧从小玩到大的地方。在他小时候,时髦的哥哥们总是拿着砖头大的录音机播放着一盘英文歌曲合集,在他耳边晃来晃去,一来二去,就为他种下了音乐启蒙的种子。后来,郑钧考上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一个热情又美丽的美国外教,为他开启了摇滚乐的大门。不过,谈起真正走上摇滚歌手的道路,郑钧感慨说,这还是要归功于他家庭的时代进步,“我爸爸在我7岁半时就去世了,他在上学的时候,因为长得很帅,就有电影厂想找他去当演员。但是我爷爷说我们家不能出戏子,不允许玩离经叛道的那些东西。”
“但我骨子里就是个嬉皮加庞克。”郑钧说,在真正来北京闯荡之前,他还跟着西安的草台班子去县城里演出了好几个月,过了一段吉卜赛人式的生活,“在那段时间里,我了解了基层文娱工作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有一个大篷车,还有一些舞蹈队的美女,我是乐队的主唱也是吉他手,还是搬运工,每次到了现场就要把设备搬到台上。到了晚上,没人看设备,我们就在旁边拼俩桌子睡在上面。轮到我看的时候没事干,就开始写歌,《赤裸裸》就是在那里写出来的。当时我们老板的儿子吹萨克斯,他还问我你在干吗呢,我说写歌呢,他说你写什么歌呢,我说也就是写着玩儿吧。”
有人说,郑钧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当之无愧的“摇滚明星”,但如今在他看来,那段日子却是他人生中最焦虑、最迷失的阶段。
1992年,郑钧本打算在大学结束后出国留学。当他到北京办理签证时,却偶然结识了黑豹乐队的经纪人郭传林。在听过郑钧的作品后,郭传林当即把他推荐给红星音乐社,就这样,郑钧签约了第一家公司。当时正值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出众的外貌,让他在1994年推出首张专辑《赤裸裸》后,迅速走红。接着,《第三只眼》《怒放》等专辑,又将郑钧推上了事业的高峰。
在大红的日子里,郑钧认识了高晓松和一众玩乐队的好友,而几乎每天,都有一群朋友在他楼下聚集,等他一同绝尘而去,奔赴酒场。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十年。2007年的某一天,他的前妻郑重向他提出了离婚,然后带走了房子、女儿和狗,而此刻的郑钧,身体也到了崩溃的边缘。“那时候我就像无头苍蝇一样,身体亚健康得厉害,神经衰弱,每天晚上就戴着耳机,放着巨躁无比的Metal,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后来我意识到,我的目的不是当个音乐家,而是能驾驭自己的人生,能过放松快乐的生活。”
郑钧直言自己是个“经验主义者”,为了医治好自己的身体,他吃过中药,没用,后来翻山越岭去了中国西藏、尼泊尔、不丹、印度,去寻求大师的帮助。在路上,他也遇到过骗子,直到遇见一个出生于1980年的年轻师傅,“我不喜欢那些玄乎的东西,只想知道怎么打坐,怎么练瑜伽,它们对我的身体有什么用。这个师傅真的很厉害,他从4岁出家,接受了很多实操方面的训练,后来我就跟着他练,他也带着我去见了其他的高人。”郑钧认真地说,“这八年时间,瑜伽和打坐对我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我原来是一个情绪很大的人,容易急躁,脾气也比较坏,这几年下来,我没有原来那么紧张了,整个人也都放松下来了。如果没有这些,我要么真的私奔到什么地方自个儿待着了,要么早疯了、早上吊自杀了。”
采访的当天,郑钧的手腕上戴了一串红珠,当记者问起他这串珠子是否有什么来历时,郑钧却哈哈一笑,说只是为了拍照好看,“不过我也有一串长期念经用的珠子,就在背包里面,它的作用就是时刻提醒我还有功课要做,不要忘了自省。”
虽然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练着藏传佛教的瑜伽,但当下的郑钧只在乎用自己的信仰,去打开精神世界的牢笼。如今,郑钧早上起来,先打坐两个小时,再做会儿瑜伽。在时间充裕的时候,他一天可以打坐六到七个小时,而在最开始时,他认为盘着腿一坐几个小时简直是不现实的,“按中医来讲,就是痛则不通嘛,我刚开始觉得打坐双盘腿,根本做不到,后来练了瑜伽身体就柔软了,我就开始打坐,但最初十分钟就痛得不行,因为血脉不通,慢慢地就可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血脉通了,自然也不疼了。当你身体通畅的时候,心情也就很愉快。也有人笑我,说你干吗呢,每天早上起来折腾一些有的没的。但其实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它的作用了。我现在遇到事确实也会着急,但是往往一会儿就过去了;另外一点是,我也会愤怒,但不会转变为仇恨。身体变柔软,心也会跟着柔软了。”
放松,是郑钧在采访中提及最频繁的词汇,他说,现在一到晚上,自己倒头就能睡着,而且在音乐创作中,他也进入了更为高度集中的境界,“其实有的时候我在台上怒吼,也有点像禅定的状态,跟打坐到最后进入的寂静状态,完全是一样的。”
除了日常的修行,身为一名项目经营者,对于合音量的运营,郑钧目前还算满意,他企图为草根音乐人铺上康庄大道的念头,依然扎得牢实。而在《摇滚藏獒》之后,郑钧目前还没有新的电影计划,但如果有合适的项目,他说自己也并不排斥。
事业之外,和妻子刘芸的缘分让郑钧认识到“自己是个糟糕的人”,所以他不停地说,希望能为大众呈现更多美好的东西。当提到儿子Jagger,他直言这段陪儿子的时间确实比较少,挺对不起孩子的。“我们从来没强迫他学任何东西,但有一天他自己说想学吉他,我就找我的吉他手姚林教他,后来姚林没时间,我就找了音乐学院的老师教他。去上课那天,他走到门口看见那个老师的头发和样子可能比较另类,有点吓人,就没敢走进去,但他回来之后我也没怪他。我就对他说,你这样做对那个人不公平,你最起码跟他打个招呼,聊会儿天你就知道他可不可爱,是不是个好人了。他觉得挺有道理的,下次去就跟人聊了半天。他其实很爱聊天的。”
对即将到来的演唱会,郑钧说儿子一定会到场,但妻子刘芸却“不一定”——“我演出的时候是一种释放的状态,和平日里的我不太一样,简单地说就是人来疯,而芸姐平时不太会看到我人来疯的样子。我的脸皮有时候厚有时候薄,家人在的时候我唱起来就会尴尬,会不好意思。但儿子会来,因为他就是人来疯。”
Q:现在很多人都称呼你为“摇滚男神”,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A:行了行了,这个名词儿听起来太吓人了。我觉得吧,叫我老郑就挺好。摇滚男神,我真不是,我有几斤几两我自己太清楚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最怕的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让自己以为有多牛,这根本不靠谱,而我知道我是谁。
Q:今年11月就满50岁了,会对这个数字有什么别样的感受吗?
A:前段时间跟我大学同学们欢聚,我就觉得,哇,他们已经都是老头儿老太太了。但说实在的,我到现在对自己还没有明确的感受,我觉得体力还不错,状态还可以,也挺快乐的,可能是跟这个行业有关系。还有一种说法是,真正去做瑜伽的话,从你做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冻龄了。这个肯定是有夸张的成分在,但也肯定是有帮助的。
Q:从2007年的《长安长安》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布过完整的专辑了。目前新专辑有什么计划吗?
A:其实最近我都在断断续续地听之前录在手机里的小样,现在计划的是先好好把这些小样整理一下。出唱片应该是真正能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不是凑数,那也没什么意思。
Q:现在唱《私奔》,和之前写这首歌时的心情是不是已经不太一样了?
A:是很不一样,当时写这歌时,就是觉得私奔这个想法每个人都有,要逃离无奈的现实环境,私奔到一个具体的地方。现在觉得无论逃到哪儿都一样,因为当下这个时代,你逃到任何地方都逃不出手机,哪里都有很多烦恼。所以现在的私奔,就是想逃到内心世界的一个寂静的地方,而且只要你愿意,随时都能逃到内心深处的宁静美好,这就是我现在期待的私奔,也是跟以前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Q:《私奔》里有一句著名的歌词“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你觉得现在的自己达到“真爱和自由”的状态了吗?
A:还在努力达到吧。真爱其实是无条件的,当你真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很美好的,而且在真爱中,最大的收获不是被爱的那个人,而是你自己;自由,其实就是放肆的状态,并且有权力和能力拒绝做不愿做的事儿和不好的事儿。这两者我都体会过。我希望自己能够彻彻底底地一直做下去,因为每个人都还是应该追寻真爱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