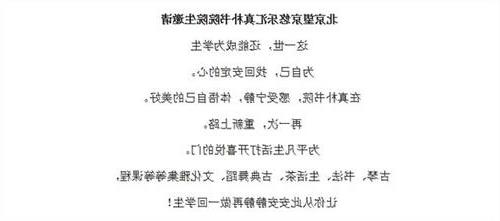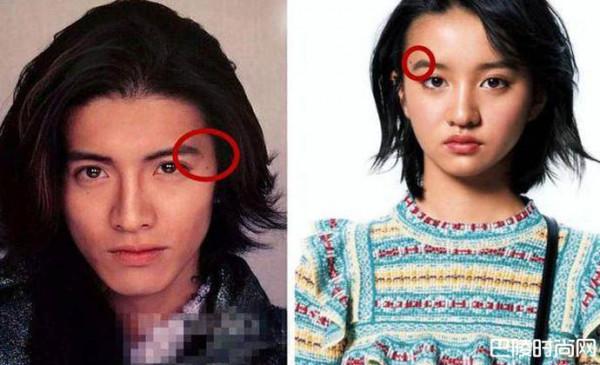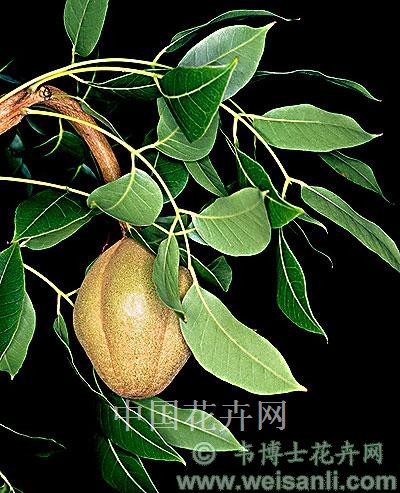木心是个怎样的人 木心 不只是个艺术家 竟还是这样一个老人!
去年读完木心的《文学回忆录》,相隔不过数月,我又见到木心了。不是在他自己的作品里,而是陈丹青的《草草集》。
这本书并不厚,可是如果只挑一篇文章推荐,我一定推荐这篇《守护与送别》,它还有个副标题,叫“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
【衰老的细节】
“但这是我第一次目击垂老的人,病危,衰竭,死。我不想限制篇幅,不愿遗漏种种细节。这是木心以自己性命的完结,给我上最后一课。”
我的确是从他的文章里读到了真挚的感情,这篇文章里的木心,不只是个艺术家,更是一个要经历衰老和死亡的普通老人家。
“谁不在心中对迟暮的老人略起倦怠么?近年,说实话吧,先生已难得惹我兴致勃然。谈锋,语笑,都还在的,但如所有老人,便是木心,也终于再四说起我早听过的人名、警句、轶谈——三十年代他的母亲如何率领街坊扑灭大火的故事,至少与我说起过六七回——我大笑,或表惊异。先生似乎着即看出我的佯装,随之抱以狡黠的、我所经年熟悉的轻笑,与我对视,在对视的一瞬,交换了彼此的宽谅——但愿我没会错意吧——稍稍静默后,于是起别的话头。”
木心和陈丹青都是很聪明的人,我不知道那一瞬间他们是什么心情,但我读到这里,觉得很悲伤。
“他不再费心维系我俩勉力合谋的欢谈。如我母亲,他耳背了,羞惭而无辜地看着我——这是他老迈后新的神情——听我扬声对他叫。”
那个自恋的木心,在面对身体无可抵抗地衰老,也只能为自己给别人添麻烦而感到羞惭。衰老,对于一个骄傲的人,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活在文学世界里的木心,也不可避免地要让人看到自己失禁的窘态,无能为力。
“先生必须完成后事的嘱托,签署文件。入院前,他的手书遗嘱笔迹颤抖,才几行字,未及写完。现在作难的是:他几时清醒?我不想描述详细的经过,终于,到那一刻,他很乖,被扶起后,凛然危坐,伸出手,签名有如婴儿的笔划,‘木’与‘心’落在分开的可笑的位置,接着,由人轻握他的手指,沾染印泥——先生从来一笔好字啊,人散了,我失声哭泣,哭着,这才明白自己积久的压抑。”
【呓语】
木心先生最后的时光里,已是神志不清了。陈丹青便记录下了他的呓语。
“那好······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
木心先生很少谈及他的过去,大家看到他时,总是调皮而乐观的,然而在难以保持清晰的神智时,他还是表露出了对失去自由的恐惧。他在自己的身上克服了这个时代,却无法完全克服过去的经历带给他的影响,哪怕是深埋在心底,但依然还存在着。
“······地底下有玫瑰色的火焰······在读我的诗······弥赛亚······我说完了······我要跪下去了······不行啦,不行啦······这样下去,我要屈服······”
在木心先生火化后,两位纽约电影人寄来悼念稿,播放了木心生前为他拍摄的纪录片的片花。
“愈是目睹死者的影像,愈是死的确认。午间才刚亲手捧了先生的骨灰盒,几小时后,木心复活,抽着烟,又在说话了······
全场肃静。我远远瞧着视频,心里藏着一桩秘密——他闪身走出,随手掩上玻璃门——直愣愣盯着木心,我又看见熊熊烈焰,看着,骤然想起他在病榻上的呓语,暗暗一惊:我的话说完了。弥赛亚!地底下有玫瑰色的火焰,在读我的诗。”
【小代和小杨】
木心暮年,小代和小杨寸步不离照顾先生。丧礼第二天,只剩下作者和他们二人了:
烦吗?在医院时?我试着笑问他俩。孩子不吱声,只是愣着。“久病床前无孝子。为什么你俩对先生这么好?”我又问。
小杨看看小代。停了片刻,小代,缓缓地说:“你知道的,丹青老师,我们在外打工,就是两条狗······到这里来,先生把我们当人看。”
“怎样当人看?”
这回是小代看看小杨,然后直视我:“比方说,我做对了事情,先生会夸奖我,做错了,他从来不骂的······”那他怎样呢?“他教我下次怎么做,下次怎么说。”
我转向小杨,他为必须说话而苦恼了。忽然,他又那么眼睛一闪,飞快地说:“我来这里,半年不敢看先生哩!这样的老头子,我没见过啊·······”
【杰克逊高地】
木心昏迷的前两个月,贝聿铭的弟子去到乌镇,与他商议如何设计他的美术馆。木心笑说: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个死不悔改的人,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木心幼年丧父,青年丧母,小姐姐死在十五岁年纪,木心四十岁时,大姐姐被批斗致死。此后岁月,这份江南人家就剩木心一人活下来。文革期间所有作品皆被焚毁,三根手指惨被折断。木心一生未婚,生命坎坷而孤独,可是我想用这首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有次上课,大家等着木心,太阳好极了。他进门就说,一路走来,觉得什么都可原谅,但不知原谅什么。那天回家后,他写成下面这首“原谅”诗,题曰《杰克逊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