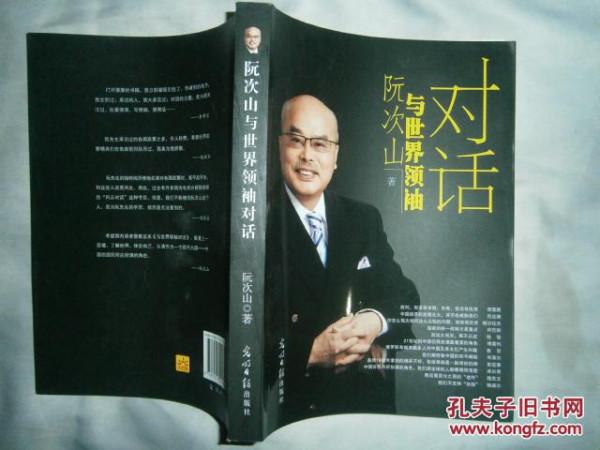许地山图片 对话许地山之女许燕吉 “落花生精神”已遗传进我的血液(图)
“父亲在世时,家境还算富裕,每年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全家都去‘景星’拍照,那是香港当时最好的照相馆,现在还在营业”。
窍的我,他也会发明些玩法来哄逗。他把背心撸上去,光膀子躺在竹席上,告诉我每个痦子、每个疙瘩都是电铃机关,一摁就有反应。我看到那两粒奶头倒真像两个门铃,一摁,他就发出叮咚的声音,再摁别处,他就发出另一种声音,高高低低,有好听的,也有怪声的,惹得我咯咯直笑。也许摁了一下,他就会猛地坐起来,捉住我亲嘴,我捂着腮抗拒,他说谁叫我摁了“亲嘴”机关呢。
而且父亲还很幽默。记得有一次,我吃橘子,不小心咽下去两个橘核,正在发愣。爸爸问:“怎么啦?”“我把核咽下去了。”“几个?”“两个。”他煞有介事地说:“明天你肩膀上就会长出两棵橘子树了。”我想,要是树从肩膀上钻出来,得多疼呀,咧着嘴就要哭。爸爸说:“不疼,不会疼,以后你还可以伸手到肩膀上摘橘子吃,多好!”我看他开怀大笑的样子,将信将疑。不过一晚上,我还是睡不着,不住地摸肩膀。
新金融:父亲很喜欢小孩子?
许燕吉:公公说他是“孩子头”,妈妈说他“不分大小”。抗战时期,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常有些亲戚好友路过暂住。小客人也常有,我们就成了伙,跑呀、蹦呀、玩捉贼、捉迷藏……爸爸总是自告奋勇当捉人的。
还记得有一次,爸爸带回家一个流浪儿,是个男孩儿,比我大一点。袁妈给他洗干净,换上哥哥的衣服,爸爸把他送到收养孤儿的学校去了。那所学校爸爸也带我去过,孩子很多,他们看见爸爸,都欢呼着围了上来,可见爸爸是他们的老朋友了。
新金融:许地山先生非常看重音乐和音乐教育,是吗?书中写道,“6岁时,家里买了一架钢琴。”父亲会弹钢琴吗?
许燕吉:我没见过父亲弹钢琴。不过,他的一位台湾同乡柯政和先生,是搞音乐的,他们二人合作译过许多外国名歌,也写过许多歌词。那时我家有百代公司的好些唱片,唱的都是爸爸的作品。我只跟唱片学会了一首《纪律》,歌词是:“在上学以前,床铺要叠起,在讲堂内里,文具要整齐,所作不苟且,件件合条理,那就叫做有纪律。
如果事事都能如此,将来服务才有效率,可爱同学们大家齐努力,一切行为守纪律。”爸爸的歌主要是给学生、孩子们写的。
新金融:在《怀念地山》中,您母亲写道:“有你的时候,屋子里的陈设,经过你布置,甚至于几朵野花经过你插瓶,都会有特殊的趣味……我们所有窗帘、地毯、围屏以至于瓷器上的花纹都是你的手迹。”您父亲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吧?
许燕吉:我倒是记得他喜欢画画。在他给我妈妈的信中,我就看见过他画下了自己手的形状,并写下:“告诉苓苓(我哥哥),这是爸爸的手。”而且后来据一个翻阅过父亲线装书的澳大利亚教授说,在我父亲的书中发现了不少他画的怪样画。
父亲的爱好很广泛,对自然科学也很感兴趣,书房里有好多自然科学的书。但是他数学不好,我母亲常说他连账都算不对。
永远的“落花生”
新金融:现在您手里还留有父亲的遗物(书籍、信件等)吗?
许燕吉:我们逃难离开香港的时候,把父亲的书籍都存放在香港大学里,二战结束后,英国办学的经费也不够了,香港大学只留下了我父亲的英文书,线装书就都卖给了澳大利亚的东方学院。结果放在书库里一放几十年,也没被利用起来。
今年3月份,原来香港大学教授马鉴(我父亲的老友)的孙子捐出来一些我父亲和我祖父的手迹给了香港大学。
我母亲留下了很小的一部分,包括一些父亲的原版书、写给她的十几封信,还有泰戈尔送给父亲的白色小瓷像。母亲去世后我都捐给现代文学馆了,我想这样才能让父亲的精神永远流传下去。
新金融:在本书的附录中您写道:“父亲去世太早,太仓促。他的学术成果,许多都没来得及写出来,只积累了上万张的资料卡片。”虽然父亲去世得早,但您母亲95岁才去世,她不给您讲关于父亲的事吗?家里的后人有没有想过系统整理许地山的资料?
许燕吉: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出去工作了,这以后就是逃难,逃难回来后,我母亲一直住在集体宿舍,而我就住在学校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始终不得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1981年才调回南京,可那时我还要上班,所以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前些年南京大学出过一本《许地山研究集》。还有我母亲的一个同事叫王盛,“文革”期间停课,就借着我母亲的第一手资料,开始研究我父亲,后来他成了研究许地山的专家,他写过一本书叫《缀网人生》,是关于我父亲的传记。
我和哥哥都是学农的,我们的后辈也都跟文学隔着行呢,所以暂时没这方面的打算。
新金融:您和哥哥为什么都选择了学农?
许燕吉:我哥哥受刘娘(我母亲的好友)的影响,认为教育乃救国之道,可当时刚刚解放,母亲有些认不清形势,就写信求教于我外祖父的忘年挚友陈叔通,当时他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母亲相信他能给予最正确的指导。陈老的回信果然很快就到了,他说若是思想跟得上形势,就可以学社会科学;若是思想跟不上形势,最好是学自然科学。
另外,在香港的时候,我父亲有一个叫弗朗士的同事,是英国人,他家在香港岛另一面的一座小山上,养着一头驴用来驮水,养了一群羊,还有奶牛、鸡、鸭、鹅、兔子、蜜蜂,猫和狗,俨然是个小畜牧场。我们常常去他家玩儿。后来我和哥哥都学了畜牧专业,应该就是那时培养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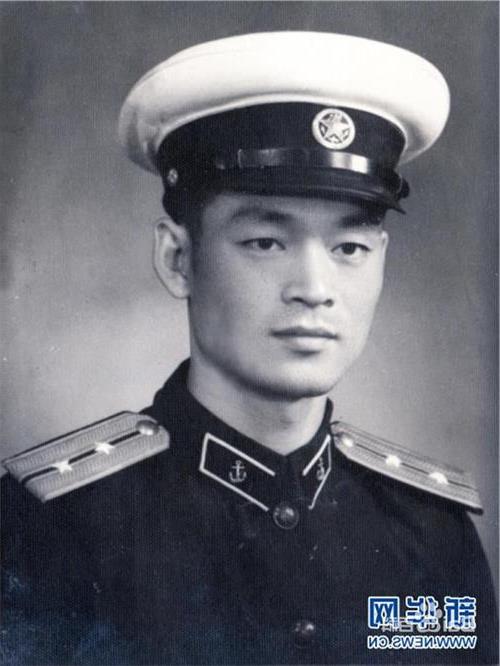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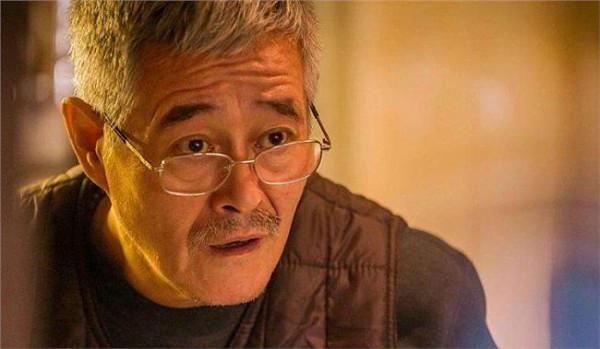




![>李文国许丹二人转拉场戏[刨根问底] [东北大实话] 李文国许丹 [双送礼]](https://pic.bilezu.com/upload/b/26/b26bd5ac79af78675112e8513fbf8fc3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