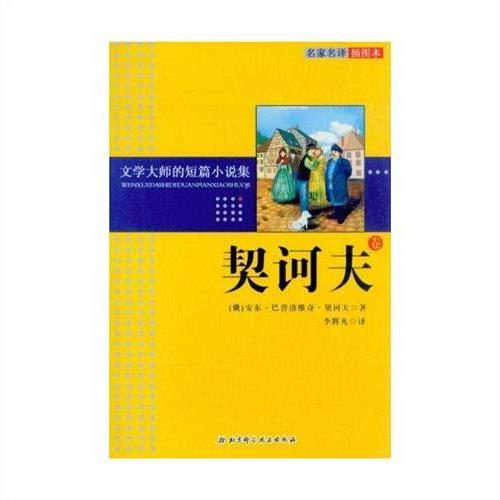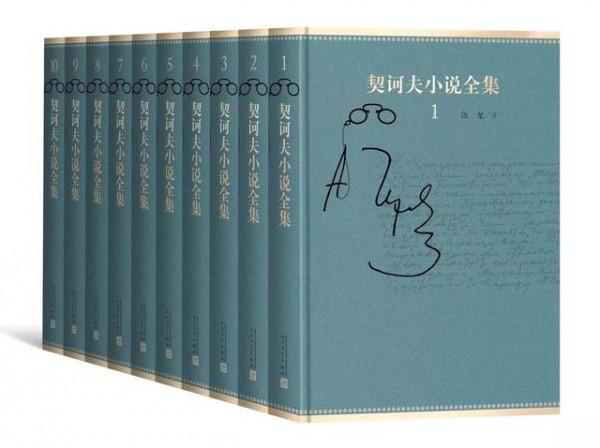汝龙日用品 在契诃夫的去世纪念日 让我们怀念他的译者汝龙
在中国,外国经典作家的名字常常与一位最为传神地再现其精髓的翻译家联系在一起。提起莎士比亚,便会想起朱生豪;提起巴尔扎克,会想起傅雷;提起托尔斯泰,会想起草婴。而对于契诃夫来说,这位中国的翻译家便是汝龙。汝龙一生翻译了一千多万字,是翻译外国作品数量最为丰富的翻译家之一,其中耗费大半生心血的是契诃夫的作品。巴金曾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读者爱上了契诃夫"。
作家冯骥才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诃夫的作品,因与汝龙谈不拢,便绕过他,邀请了一些俄文专家,试译契诃夫的《套中人》,看谁译的好,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把契诃夫的味道译出来,最终还得去找汝龙。
冯骥才说:"契诃夫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只有能够神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才能去译,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
2016年是汝龙的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全集》,收录了契诃夫自1880年到1903年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近五百篇。汝龙之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汝企和回忆父亲说,"为了有更多时间进行翻译工作,他深居简出,社交活动少得不能再少,每天几乎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翻译。
在一般人看来,他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没有周末,很少娱乐,几乎与世隔绝。翻译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他最大的乐趣。"
汝企和不止一次地听父亲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与苦闷,"那个时候他整天无所事事,说是在一个教会中学念书,其实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是泡在戏园子里听戏。他父亲经常教导他要做大官,光宗耀祖,他心里却想祖宗我根本没见过,凭什么为他们活着。而且看着周围那些高官,尽管飞黄腾达、穿金戴银,却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同许多年轻人一样,汝龙也经历了这样看不到出路、找不到人生意义的时刻。
他开始阅读鲁迅、巴金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可以说是巴金拯救了他。巴金为当时苦闷的青年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为人类服务,甚至为人类献身。这个高尚的目标成为了汝龙的理想,"正是这个理想挽救了我,使我没有变成坏人,他更支持了我一辈子!"他以读者身份写信给巴金,诉说自己想从事文学工作的愿望,巴金回了信,从此巴金成了他一生的挚友和导师。
在巴金的鼓励下,汝龙选定了翻译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起先汝龙想翻译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征求巴金的意见,巴金说,"你既然愿一生干翻译工作,就该译较难的古典文学, 系统地介绍一位作家的作品,这样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风格。你就译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吧。"
自此以后,汝企和说,父亲的翻译工作用"几十年如一日"来形容毫不夸张,"为了有更多时间进行翻译工作,他深居简出,社交活动少得不能再少,每天几乎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翻译。在一般人看来,他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没有周末,很少娱乐,几乎与世隔绝。翻译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他最大的乐趣。"他甚至没有去过一趟前苏联,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彻夜工作是汝龙几十年来的惯例。1949年前汝龙是中学教师,身边又带着两个女儿,白天时间全被占据,只有夜里才有时间翻译,因此养成了熬夜的习惯。为了使自己不困,他常常是站着趴在箱子上翻译。五十年代,他经老友介绍做起了大学副教授,但一年后他就辞职专心翻译,之后的岁月基本都是在独立翻译的情况下度过的。他依然熬夜翻译,因为夜里干扰少,精力更容易集中。
"我家住的是独院,每到夜深时,只有父亲屋里的灯光还亮着,光透过绿色的灯罩,把玻璃窗也染成莹莹的绿色,现在一闭上眼睛,我还能看到那片柔和碧绿的灯光。"汝企和回忆道。
汝龙对自己的译作要求非常严格,每次出版前都要反复修改。由于国民党的封锁,49年前人们很少看到俄语书籍,所以他只能通过英语的译作转译契诃夫小说。49年后他从头开始自学俄语。他买来俄语的契诃夫全集,将以前转译的700多万字的契诃夫作品又重译了一遍。
由于常年伏案,汝龙患有严重的痔疮,发病时裤子都被血染红了。这时候他仍然不休息,在椅子上放一个垫子继续工作。汝企和回忆,他父亲经常说,"对待疾病就要像打仗一样,不能退让,你退一尺,它要进三尺,你咬牙顶住,它就退缩了。"
文革时,汝龙遭受到了人生最沉重的打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造反派贴出了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的所有值钱物品,都主动上交给了红卫兵。汝企和清楚地记得,1966年秋的某一天,父亲呆呆坐在屋外台阶上,目光停滞,表情木然,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
后来汝龙说,当时他真的认为自己一生的路都走错了,本来以为翻译是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是"为人类献身",结果却是宣扬"封资修"。辛勤劳动的成果成了罪证,心里的痛楚和无尽的自责是语言无法表达的。
不过幻灭没有持续多久,各种渠道传来的"小道消息",使他逐渐认识到文革可能是错误的,过去的工作仍然是有价值的。于是他又拿起了笔,汝企和回忆,"当时全家人被赶到西单达智西巷六号的两间小屋里,和我奶奶挤在一起,唯一的一张大床是奶奶和母亲合用,父亲睡小屋里的一张小床。
屋子里很挤,走动都要十分小心,才不至于碰翻东西,父亲只能在一张很小的桌子上翻译。当时完全没有出版翻译小说的可能,也看不到任何希望,但父亲相信,总有一天,他翻译的书会出版。"
由于文革初期的沉重打击,汝龙那时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经常觉得脑力不够,只好拼命抽烟来提神,结果哮喘病越来越厉害,病一发作起来脸都变成铁青色。当时他的稿费全都上交,每个月就靠人民文学出版社给的生活费度日,吃的很差,病也得不到很好的医治。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契诃夫全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并且开始翻译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文革后巴金到北京参加会议,期间到西单达智西巷看望汝龙,他看到汝龙一家三代人挤在一个小平房里,同样翻译俄罗斯作品的汝龙妻子文颖正在缝纫机台面上做翻译,汝龙的哮喘病也因为室温太低而经常发作,巴金神色顿时凝重,半天没有说话。
后来巴金回去后立即向一位以关怀知识分子而闻名的的中央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1982年3月23日巴金在致汝龙的信中写到,"你的房子问题看来一时无法解决,但是我还是要讲,有机会就讲。"终于1982年下半年,汝龙一家离开了那栋有百年高龄的老屋,搬进西便门的两所毗邻的崭新单元房。若干年后巴金的义子曾向汝企和回忆,巴金对他说,"我这一辈子干了两件托关系的事,一件就是给老汝要房子。"
文革后汝龙得到平反昭雪,房子也解决了,稿费又退还给他,藏书也大部分归还。他专门定做了十几个每层能放两排书的大书柜,塞得满满的全是书,又买了两个大写字台,一个用来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个用来修改契诃夫文集。当时他的心情特别愉快,计划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然而由于重病缠身,他终究未能实现这个愿望。
在汝企和眼中,生活中的父亲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嬉笑怒骂全挂在脸上,高兴起来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看电视看到感人之处又会像孩子一样泪流满面。每当电视里播放反映俄国社会的电影时,汝龙和妻子便看得非常仔细,他常会指着荧屏上的器物对妻子说:"快看,这就是书上写的东西。"
对古今中外的小说,他都非常熟悉,每当谈起文学名著,他都会两眼放光。他最喜欢的书是《红楼梦》,他经常说,每当脑子发木,感觉翻译的语言不流畅时,就要拿出《红楼梦》读几页,再回来翻译,笔下就顺畅多了。
对当代文学,汝龙也很关注。他晚年时女儿借来了金庸小说,他一看起来就放不下,常常一口气看到天亮。看了老鬼的《血色黄昏》后他说,这本书受《水浒传》的影响很深,对人物的刻画既生动又深刻。对张洁、蒋子龙等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他也十分赞赏。
为使译作更为生动,汝龙十分注意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五十年代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音响,他买了当时最好的美国进口的收唱机,有一米多高,看上去像厚厚的书柜。每当觉得没有翻译原作的激情时他就停下笔,听几张激昂的古典音乐唱片,再回来翻译。他也经常关注各种美术展览,还以高价买了一套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共20余册,里面收藏了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名画,在翻译感到疲劳时,他就取出来翻阅。
汝龙对翻译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经常说文学就是人学,是研究人的世界观、描绘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文学翻译不仅要耗费脑力,更要耗费感情。要想感动读者,自己就要加倍的投入感情,翻译出来的小说才能感人肺腑。
1991年7月13日,汝龙在一家民办的康复小医院里悄然离世,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也没有发讣告,按照他的遗愿,火化后连骨灰都没有保留。去世不久,《文艺报》在一版左下角发了一条消息,报道汝龙去世及他生前要将自己的全部稿费积蓄捐赠国家的遗愿。他所有藏书和全部手稿都捐给巴金提议创办的现代文学馆。
如今汝龙的家里依然摆着他当时翻译的写字台,书柜摆满汝龙的译作,从库普林的《亚玛》、《生活的河流》、《侮辱》,安德烈耶夫的《七个绞决犯》、《总督夫人》,到高尔基的《我的旅伴》、《沦落的人们》、《人间》,以及近年出版的《契诃夫文集》、《契诃夫小说全集》,各种版本的《复活》、《契诃夫小说选》等等。
汝企和依然常常想象,父亲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孤灯苦读:周围没有灯红酒绿,没有声色犬马,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他面对的只有堆满桌子的书籍,环绕他的,只有贴墙而立的十几个大书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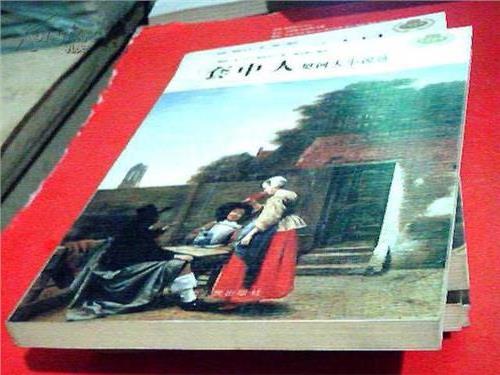

![汝龙书法 [书评文论]关于汝龙及汝龙译契诃夫的不足](https://pic.bilezu.com/upload/8/98/8983b71a1d37cae35d1da38edc2e102a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