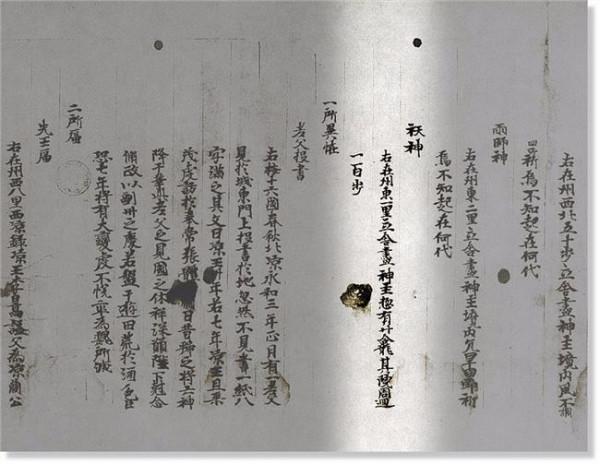敦煌守护者樊锦诗 樊锦诗:敦煌的守护者
齐耳短发,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女,手拿草帽,肩挎背包,整装待发……这是矗立在敦煌研究院的一尊雕塑,名曰《青春》。
瘦小的身材,朴素的穿着,花白的头发,匆匆的脚步,劳碌的身影……这是有“敦煌的女儿”之誉的“中国十大女杰”樊锦诗。今年3月初,全国妇联公布了十位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的名单,樊锦诗名列其中。
一般人很难将塑造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春倩影与年过古稀、不施粉黛的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樊锦诗联系在一起。其实,《青春》雕塑的原型就是当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直奔祖国大西北的樊锦诗。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青涩女孩如今已是满头华发,不变的是报国志、赤子情。
她爱上敦煌莫高窟,“厮守”50多个年头,不离不弃。对这位把青春交给大漠戈壁、把敦煌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敦煌的女儿”来说,敦煌就是家,割不断、离不开的家!她那斑白的华发似乎在向我们娓娓讲述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传奇。
□吴志菲
人物名片
樊锦诗,汉族,女,浙江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1963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有“敦煌的女儿”之美誉。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
●一见钟情
“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有“墙壁上的博物馆”等称誉。
在敦煌这个古远而神奇的地方,樊锦诗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度过了50多个春秋。樊锦诗说她喜欢晚上出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晚的莫高窟像个沉睡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现在对我来说,这还上升到了一种使命感。”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算是小康之家。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她,从小体弱多病,出生不久就患有小儿麻痹症,这种疾病导致她的腿脚不如常人那么灵便。“父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也感染了我。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教授的“石窟艺术”课是樊锦诗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大学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热烈地向往着敦煌的神秘宝藏。
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站在莫高窟前,她立刻被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深深打动,全然忘记了洞窟外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简陋宿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一见钟情”的她钻进冰凉孤寂的莫高窟感觉就像来到了故宫博物院,新鲜而充满乐趣,她为敦煌艺术而自豪,为自己有机会直接接触敦煌这份伟大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而欣慰……
鉴于樊锦诗在实习期间的突出表现,她被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所器重。同时,樊锦诗为常书鸿的事迹所感动、敬仰:“当时,我常想:这地方,他怎么能呆几十年呀?没有电,没有饮用水,晚上上厕所都要去很远的地方。
根本没有娱乐,与世隔绝,平时来个人都会觉得新鲜,信息也不通,报纸一来一大摞,起码都是一个月以前的。一部《列宁在1918》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还披着军大衣看。我在大城市长大,确实没有想过要在那里干一辈子。”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研究所去学校协商要人,我们4个实习生全要。学校当时只答应给两个,我是其中之一。”尽管学校已决定她留校工作,但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大都市的生活,奔赴了西北大漠深处的敦煌。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她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时,才真切地知道了什么叫“反差”:交通很不便利,樊锦诗清晰地记得,当初他们从敦煌到莫高窟时,在敦煌东大桥花了好大工夫才拦截到一辆过路车,让其顺路捎带一截。
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本来以为敦煌那么漂亮一个地方,肯定是窗明几净,那些专家们肯定都很气派。结果都穿着一身干部服,洗得淡淡的,一个个都跟土老帽儿似的。”樊锦诗坦陈:“说没有犹豫、没有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樊锦诗来到所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其他几位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3年后草稿刚刚完成,文革让研究工作被迫搁浅。这时,樊锦诗的心灵受到极大震荡,自己崇敬的常书鸿整日跪在地上端食喂猪……自己则每日顶着烈日风沙,被迫参加无休止的开会、劳动、大批判……
文革以后,岁月倏忽,人已中年。“十几年磨合,我早已习惯了大西北,爱上了莫高窟,把研究石窟、保护石窟当成了一份终生的事业”。
●“嫁给”敦煌的女人
就像一个清纯少女不肯割舍自己初恋的情人一样,当樊锦诗选择了敦煌这个意中的“情人”后,就再也不愿割舍它了。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在学校谈的恋爱。彭金章的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在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于是志趣相同、情笃意深的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
樊锦诗说,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3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
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而樊锦诗心里在打鼓,她跟莫高窟有感情了,难言离开。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合。自此,天各一方的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1968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临产前3天,樊锦诗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敦煌条件太差,准备到武汉去生。樊锦诗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彭金章的母亲从河北农村也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樊锦诗回来。
可是,樊锦诗却因为忙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只好挑着东西反复倒车,等他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个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未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
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糊得满手、满脸、满身,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7个月,可每次走近家门听不到小宝贝的哭声,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孩子会不会被绳子勒死了?”
1973年,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把他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一次,樊锦诗去接5岁的儿子时,猛地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这时,彭金章的大姐说:“你没见你儿?”于是,樊锦诗便猜到了是刚才旁边那个黑不溜秋的小孩。
大姐笑着问:“你都不认识你儿了?”樊锦诗说自己真的不认识了,孩子也不认识她,把她忘了。在大姐的一再引导下,那个娃娃才勉强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又刷刷地下来了。
当年,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要么跟着父亲或者母亲。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我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对于敦煌,时间久了,越发觉得有意思,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特别是当上研究所的业务副所长之后,我的肩上又多了责任。”每次探亲,樊锦诗都记得儿子就会期待地问:“妈妈,这回能待多久?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呀?”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3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3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最终“投降”了。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这一年,樊锦诗48岁。“应该说是我丈夫下的决心。
他一直希望我到大城市去,起码是为了孩子受教育,但是他可能也看出来了,我黏黏糊糊不想走,因为我实在喜欢这里。”还是丈夫做出了“牺牲”,从湖光山色俱全的武汉大学调到了罗布泊边缘的敦煌石窟,做了一个“敦煌的女婿”。
樊锦诗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走了。”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为敦煌“延年益寿”
1998年,整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到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
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商业化的运作与保护的矛盾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我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
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日渐消瘦的樊锦诗却又有了新的思考,她开始进行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神秘的莫高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使莫高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气候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二氧化碳长时间滞留窟内以及窟内相对湿度增加,空气温度上升,都有可能侵蚀壁画。”
樊锦诗和她的研究集体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科学的途径,来化解文物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樊锦诗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石窟“延年益寿”,尽量老得慢一些,争取让它再活1000年。
面对游客迅猛增加带来的挑战,敦煌研究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保护工作,顺利完成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从研究、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约束力的保护措施。同时,敦煌研究院还开展了洞窟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寻找着莫高窟洞窟游客承载量的科学数据,建立了洞窟旅游开放标准,实施轮流开放、参观预约和预报制度,控制进窟参观人数。
“文物就像人的胃,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必须建立在保护为主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适度地利用。”
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目前,提案的各项建设得以实施。
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了专门从事研发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的部门。在樊锦诗眼里,任何文物都在逐渐退化,何况有1000多年历史的石窟、壁画。“敦煌有那么多洞窟、塑像、壁画等珍贵文物,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信息固定保存下来。‘数字敦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樊锦诗憧憬,“数字敦煌”让千年敦煌成为“不朽”遗产。
樊锦诗注意到,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由于财力有限、观念落后、人才匮乏,往往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少、利用多,有的官员甚至只把眼睛盯在了增加收入上。于是,她在全国两会上一次次呼吁:世界文化遗产绝不是“摇钱树”!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樊锦诗提交了《关于世界文化遗产收回到省级部门保护管理》的提案,建议由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世界文化遗产,集一省的专业、科技力量,提高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正确处理利益之争,为子孙后代留住顶级的文化瑰宝。
“赞叹敦煌异彩珍,狼烟四起泪花频。樊篱难阻沙尘暴,妙手能回石窟春。锦绣缤纷丝路杂,山河壮丽世风纯。诗歌曲赋当书写,荒漠精心护宝人。”曾有人赋七律一首,如是赞樊锦诗。她俯身甘愿化作敦煌一段华丽而又朴素的锦缎,扎根沙漠,用执著的信念锤炼着一首值得咀嚼、回味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