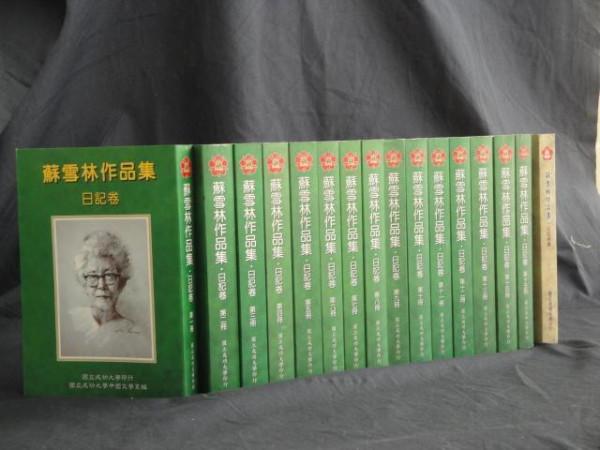苏秉琦关于考古学 生命在事业中永生——谈苏秉琦先生对考古学的贡献
考古学大家苏秉琦先生已逝去13年,但他仍活在许多考古学者的心里;他的考古学系统理论仍在指引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在他的理论指导下的考古实践与研究,促进了"中国学派"在世界考古学领域中崛起。
苏秉琦先生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同年进入北平研究院开始从事考古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任研究员。1952年,他去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我从1954—1959年在北大历史系学习考古学,毕业后分到考古所,同先生一起工作。50多年以来,我一直是在先生思想的影响之下进行考古学习与工作的。
苏先生60多年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前30年主要精力耗费在两个方面:一是绕出两个怪圈: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和把社会发展史当做全部历史;一是通过对一种古器物(瓦鬲)的研究、对一个古文化(仰韶文化)的研究,找到了考古学发展的新起点。"
抗战期间,苏先生在昆明整理他在陕西宝鸡发掘所得的先秦的考古材料,从中提取了中国独有、分布广、延续时间长的中国古文化的 "标准化石"——瓦鬲,进行了开创性的专题研究。他认为,商王朝时期周人已在西部兴起,殷人的瓦鬲在宝鸡地区与先周时期周人的瓦鬲共存;先周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西北方来的姬姓成分,一是关中土著的姜姓成分。
周王朝时期,秦人在陇西兴起,当秦人东进到宝鸡地区时,带来了素面鬲、屈肢葬、铁器等文化因素。这就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商、周、秦不同源。王朝更替与中国古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多元文化不断团聚融合的过程,从而绕出了夏、商、周、秦一以贯之的大一统的王朝正统体系的怪圈。
1958—1959年,苏先生指导我们班实习发掘陕西华县泉村仰韶文化遗址。在整理过程中,他从仰韶文化纷繁复杂的因素中,提取了在关中地区仰韶遗址中普遍存在的三类六种陶器作为"分子",进行排比研究,由此掌握了仰韶文化的突出特征、发展阶段和相应的社会变化,并重新界定了"类型"。
通过解剖仰韶文化这只"麻雀",先生顿悟:"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文化区系确确实实存在过。我就是这样绕出了把社会发展规律当教条、生搬硬套考古材料的怪圈。
也就找到了新的起点:中国文化是多源的,必须按实际存在的不同系统,寻其渊源、特征、各自发展道路。这一认识为我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新基础,从中孕育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学说。"
"文革"中苏先生受到冲击,但他泰然处之。在"五七干校"期间,他还在息县进行"业余考古",并对区系类型学说进行了充分的思考。总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对考古学的未来满怀乐观。
苏先生概括他的后半生是"走出了决定性的两大步:第一步是从宏观的角度,围绕中国文化的起源,应用区系的观点指导田野工作并作理论探索,其最终目标是为阐明十亿中国人民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第二步是从微观的角度,应用分子分析的方法,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对中国文化中那些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如何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的千古之谜,从考古学上寻找‘破秘’的钥匙。"
从干校返京不久,苏先生就在一些学术单位讲解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要点在于:中国历史文化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却是自成一系的。在中国古文化大系内部,可分为六个大的文化区:一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二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三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四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五是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六是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
这六大区又可以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各三区的两半,或分成以面向东南海洋和以面向欧亚大陆的各三区的两半,形成了对立统一的格局。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而主要着眼于考古学文化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
直到今天仍未能完全排除这六大"区"的存在和作用。所谓"系",是要追溯各区文化本源。既看到它自身发展的连绵不断,又要看到发展中的错综复杂、丰富多彩。所谓"类型",是指各大区内部因发展的不平衡而存在的不同地域分支。
实际上,从考古学上能明确显现渊源,又有充分发达的典型文化特征和完整发展道路的,往往只是一两个类型。也就是说,每一大区中各有范围不大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它们常常是后来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的基点。
当然古代历史文化区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像今天行政区域划分得如此明确。各大原始文化区系之间也还会有一些文化交汇带。区系类型的理论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所以并不深奥难懂。因此一经提出,即得到考古学界内外广泛热烈的响应,把它视为考古实践、研究的指导思想、基础理论,同时也就是考古学"中国学派"的一个基础理论。
区系类型理论代表一种辩证的方法。苏先生多次给我们说到《庄子》中"庖丁解牛"的寓言。庖丁初学解牛,所见"皆牛也",即都是全牛;经过一段解牛的实践,再看到牛,则 "无全牛";最后达到"游刃有余"的高超境界。
他告诫我们,不应只把古代中国视为"全牛",区系类型的理论就是庖丁手中的解牛刀,用心实践就能认识"古代中国"这个"牛体"内部的复杂结构及其间的有机联系,从而达到"无全牛"的认识高度,逐渐进入"游刃有余"的境界。苏先生诙谐地说:"如果把认识一直停留在‘皆牛也’的阶段,岂不只是一个放牛娃?"
区系类型理论也是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先秦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理论。为深入地探讨各区系内部的文明进程及其阶段性和多样性,苏先生以七八十岁的高龄奔走于燕山南北、甘青一带、豫西晋南、张北口外、山东、杭州湾、岭南粤北以及成都平原等等,亲临发掘工地、考古库房,与考古第一线的学者一起对田野考古成果进行了微观的、深入的考察,得以验证、丰富、总结出有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系统理论。
这一理论可以概括为:从氏族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古文化、古城、古国";国家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
区系类型理论同样是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基础理论。苏先生说,中华民族是个大熔炉,各区系也都是熔炉。过去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看成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民族及其文化不断地组合、重组,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又是多种因素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她根深叶茂、本固枝荣。根深、本固造就了强大的凝聚力;叶茂、枝荣造就了文化上无与伦比的丰富多彩。多元与一统,是辩证的统一。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总趋势。
我所认识的苏秉琦先生不是那种一生与青灯、黄卷为伍,著作等身,到头来却"高处不胜寒"、怆然孤寂的学者。他全身心地投入考古实践,贴近田野,亲近基层学者,凡是事业需要他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海内外的学人来拜访他,都是他的座上客,而无高下之分。
他倾听来客的报告和需求,因而能准确把握考古学发展的脉搏和学术生长点。苏先生更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看风使舵,到头来追悔莫及的虚荣学者。先生有坚定的信念,耐得住寂寞,宽容误解,自然能高瞻远瞩,完成大业。
他对考古学、古史研究的贡献不是在一个"点"上的突破,也不是一个"面"上的丰收,而是贡献了一个全新的古史架构,他的著作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国家图书最高奖。苏先生真的同事业融为一体,他的生命将与事业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