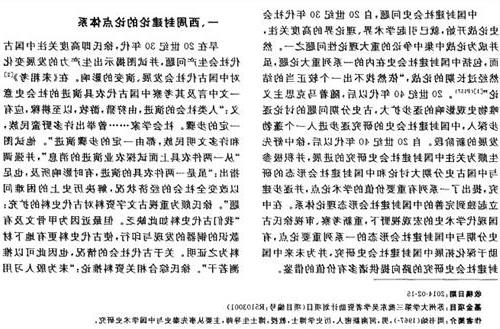徐法言徐中舒 徐中舒与中国前封建社会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大体始于20世纪初。早在1906年,刘师培陆续发表《古政原始论》《古政原论》等著作。其中《古政原始论》讨论的十三个问题,涉及先秦时期的氏族、君长、阶级、礼俗等,刘氏除引用文献外,还利用了金文、钱币等古文字资料。
学术界评价刘氏以上两篇文章,“虽仍不脱传统史志的体例,但已开启具备近代意义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端倪”[1]。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社会史论战发生后,中国古代社会问题开始逐步引起中国古史学界的重视。
社会史论战加速了中国社会史的成长,但实事求是地说,社会史论战期间,“郭陶两派以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人数更多,但有贡献的却甚少,他们不但少有贡献,有的人甚至于反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走入了歧途”[2]99。
此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领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然而,由于该重大理论性问题涉及专题繁多,性质复杂,在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学术界对该理论性难题的探索和争鸣一直未停止过。自20世纪30年代起,徐中舒先生即高度关注这一理论性难题的学术进展,并就此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辛勤探索,逐步建立起独到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理论体系。
一、关于氏族组织
中国早期社会中氏族的材料屡见于《左传》《尚书》《国语》《史记》等古代文献及甲骨文资料,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唯班固《白虎通·姓名》、王符《潜夫论·志氏姓》、郑樵《通志·氏族略》及顾炎武《日知录·氏族》等著作或多或少地揭示出先秦社会的部分历史实际外,总体而论,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之前,由于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念,学术界关于氏族组织与氏族社会的研究,大多尚不具有学术价值。
诸如《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近代以来的史学家已较为清晰地意识到,这里的“国”与“诸侯”皆非事实,“夫古国能如是之多者,大抵一族即一国,一国之君,殆一族之长耳”[3]40。又如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殷本纪》中均提到禹、契之后,“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并分别列举了不少的氏。
金景芳先生指出:“这些血族团体如氏族、胞族、部落等等都是‘自然长成的结构’,并不是如后世的诸侯国,是经过分封才出现的。”[4]唐嘉弘先生亦指出:“司马迁忽略了古代氏族、部落增殖裂变的事实,误以周、汉政体去理解夏商政体,不合历史实际。
……这纯粹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现象,夏、商诸氏的出现正是如此,并非出于分封。这在原始社会末期,带有普遍性。
”[5]凡此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初期的社会结构和氏族组织缺乏科学的观念,因而他们对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与特征的不少研究很难准确揭示中国早期社会的历史实际。
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学者对人类社会早期氏族的组织结构与特征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对于阶级社会以前的状态和那时的社会组织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直到1877年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较早以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发现了氏族的组织结构与本质特征,“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基础”[6]113,“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6]114,“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7]433。
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现代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传播至中国,新时代、新史观、新史料、新方法、新的文化氛围,助推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繁荣局面。
1930年,由联合书局出版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较早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概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并结合古代文献和新出甲骨文资料,对商代及其以前的社会生产、氏族组织和婚姻形态等重要理论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索。
事实上,自《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2]96-97。自20世纪30年代起,徐氏逐步自觉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民族学资料,对上古社会氏族组织与婚姻、继嗣、亲属称谓等问题作较为接近历史实际的考察。
也就在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的同一年,徐氏发表了著名的《耒耜考》一文,文中较早谈到氏族组织问题:
社会学家说原始的人们,不能有个人财产的观念。他们生活在氏族共产之中,氏族内部,一切属于全体,共同消费,非洲波希曼人若是捕获一条野牛,则分割为许多块数以送于其余的人。旱荒的时候,佛爱奇的少年便沿河而跑,若是运气好,遇着一条死在浅滩上的鲸鱼,他们无论饿得要死也不动手,只是迅速地跑回去告知他们的氏族,于是氏族人员立刻跑来,由极年长的人将死鲸平均分割于全体。即是农业发明以后,种族或氏族的共有土地,仍是共同耕作,共同消费的。[8]
徐氏还举证“纪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王时代,尼雅格大将在印度某几处地方,还目击各种族对于共有土地的共有劳动,及收获物之按照户口分配”[8],“一个爱斯基摩人自己只能具两个独木舟,若制造了第三个,便归氏族处置,因为凡自己不使用的物件,便是共同财产”[8]。综上可知,徐氏通过民族学材料较早地了解了氏族组织的概貌和氏族社会的若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