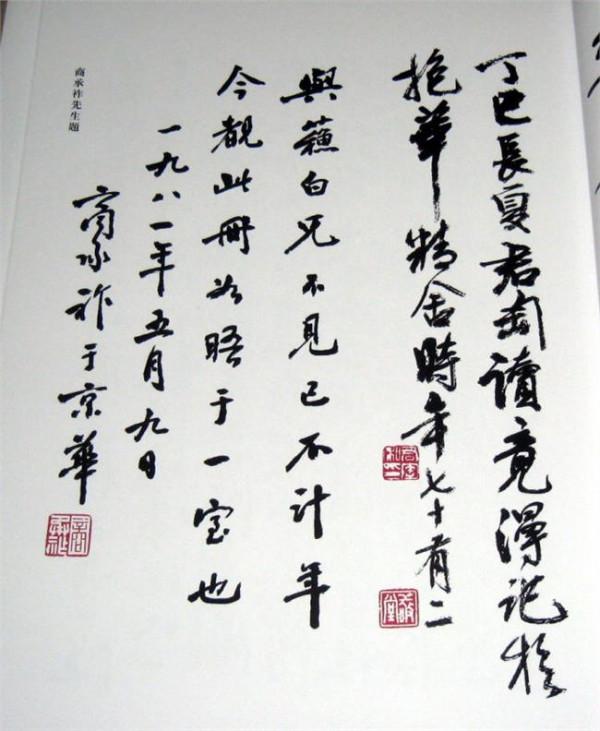徐中舒之子 天下怀宁人:怀宁六院士之徐中舒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史学涉及的方面广泛:哲学、文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工艺学、建筑学还有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等学科都可以囊括其中。在当时就成为显学,而它的治学过程却是漫漫寂寞艰辛的。 1929年徐中舒32岁起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直干了九个年头。
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同仁一道埋头整理八千余袋子重达十五万斤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是一个巨量,整理地点在故宫午门楼上。徐中舒是从苦寒中过来的,生性不好游乐,不贪图享受而专心致志于钻故纸堆的工作。
《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再述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以及参与刊行《明清档案》甲编、乙编十数册,为传承中华文化燃烧奉献着自己青春年华。 徐中舒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两大部分:一是史学,二是古文字学。
也就是在史语所的岁月,徐中舒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史学论文,让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之击掌叫好,称赞他是:“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才高气傲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在与蔡元培的信中云:“徐中舒先生之著作近有极重之大发见,其所撰狞猎图考一文,论及古代文化之迁流,多人所未道。
……尤使人欣慰者,为同人之精勤不息,奋力迈进。……此正目下所中之风气,最可珍贵者此也。”褒誉之情溢于纸面。
今天重新奉读徐中舒为探索古代北方气候的《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由象的逐步南移,证明我国大陆古今气候,实际上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从事实的指证过程可以看出徐中舒的学术视野之宽广,古今贯通而不囿于一隅。
他在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一节中谈到:河南古称豫。“〈禹贡〉豫州之豫,取象、邑二字之合文。”又在周代象之南迁中指证:巴浦即汉益州地。《山海经内经》云:“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他以古文字学及多学科的深厚功力在论证过程可谓左右逢源,将古史与古文字以及考古材料数者结合而相互印证。
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由汉语“想象”一词产生于四川,以及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中发现堆积如山的象牙,也可以佐证徐中舒在1930年的洞烛幽明。
他在该文的最后结束语是:“于是三千年来由北向南辗转迁徒之象,除我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尚有遗存外,就中国全域说实已趋于绝灭。”这一结论现在看来也是富有科学性的。另外他行文的逻辑性与艺术性让人在今天读起来也是津津有味的。
同年发表的《耒耜考》也是受到国内外学术界赞誉影响深远的一篇重要论着。“耒耜”古代指耕地用的农具,形似古钱“布币”。后来日本学者关野雄因其启发,写出了《新耒耜考》;国内的《农业考古》在1982年还重新刊载。
在该文中徐中舒是站在社会经济的高度加以认识与生发开去的,可谓高屋建瓴。 徐中舒还一篇遗作《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先后刊载在1999年的台湾《古今论衡》与大陆2000年的《中华文化论坛》上。
其中有论:“至于铜器与两轮大车非我国所固有,在笃爱我国文化之人士言之,宁非憾事。但吾人由此知中国文化在远古并非孤立,此亦非无益之事。
吾观殷墟文物之盛,即能撷取他人之长而迅即融会己有,且发扬而光大之。吾人今日之耻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发明与日俱增,而我即追摹仿效,犹不能仿佛其什一也。”海峡两岸的学者们读到这篇写于1948年的遗作都不得不赞叹史学家徐中舒的开阔的眼界与开阔的胸襟。
徐中舒在研究学术的同时亦注重交游。1933年7月他的同乡好友朱光潜自欧洲学成归来,在喜相逢欢谈之后,朱光潜不久便接到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聘书,一切顺利得让朱光潜有些纳闷。
原来这桩好事是徐中舒携好友的《诗论》(初稿)向胡适举荐促成的。这一年徐中舒正好在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殷周史料考”。 在北京最美丽季节十月的金秋里,徐中舒还在著名的全聚德烤鸭店里宴请另一位来京的好友朱自清先生。
三天之后,对方又回请。大家晤谈甚欢,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杨振声、梁宗岱、郑振铎、朱光潜、李健吾、朱物华、叶石荪、韦季斌等在那个时代小半个北京城的新生代精英都聚在席间了。
直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徐中舒一共在史语所工作九个年头,这是他一生中流金岁月,也是现代工业文明曙光初照神州昙花一现的年景,那时候的中国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目睹世界列强的横行霸道与劳苦大众的苦难之后,都在努力为国家和民族的重新崛起而尽忠尽孝,以慰藉衣食无忧后的魂灵的时时不安。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外来的侵略阻断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梦想。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央研究院开始南迁,徐中舒一家也开始颠沛流离,因家累过重,终于在长沙时离开了史语所,后经傅斯年推荐,接受了中英庚款委员会和四川大学的聘书,成为四川大学历史系中英庚款教授。
徐中舒携一家老小八口由长沙过洞庭湖转武汉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溯长江西上入蜀,先至重庆后将家眷租住于江津县西门黄金街84号。
1938年徐中舒只身赴成都就任,是时朱光潜任川大文学院院长,流亡乱离之中老友重逢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也于上年受聘川大,徐、冯二人也是一见如故,后在川大共事长达近40年而结成终生莫逆之交。
在回返江津时,徐中舒还专门对已经江津避居陈独秀作礼节性拜望,因为他们是同乡。1939年5月陈独秀病逝江津时,徐中舒的母亲太夫人尚在江津,她还曾率长孙、次孙亲往陈家吊唁。
1944年好友朱自清从昆明来成都探亲,这时朱太陈隐竹在川大图书馆工作。徐中舒和一帮成都的朋友们都想让朱自清留在成都,但朱后终不忍离开清华,在暑假仍飞回昆明西南联大。 徐、朱两家关系一直亲密,1945年徐中舒老母过世,朱自清夫人陈隐竹女士在自己家里设香案祭奠。 慈母过世,徐中舒心恸大悲,自印祭文《先妣事略》以记哀思,后为成都《新中国日报》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