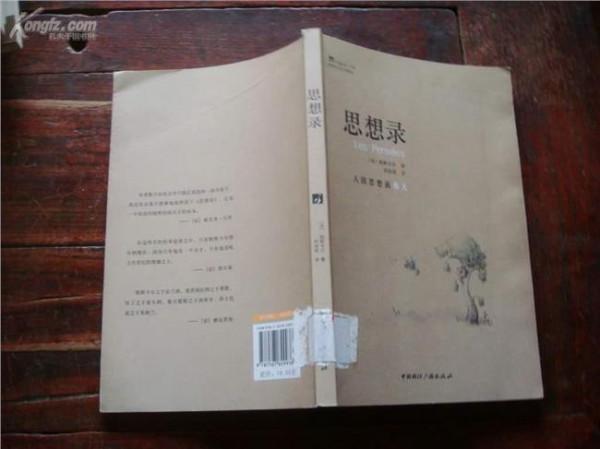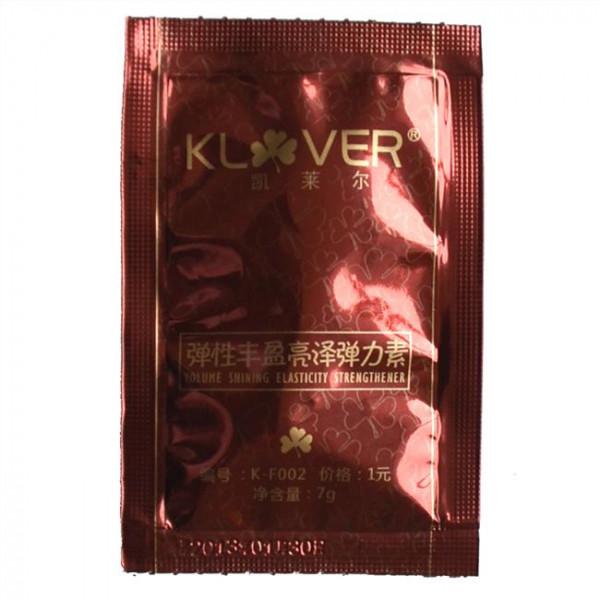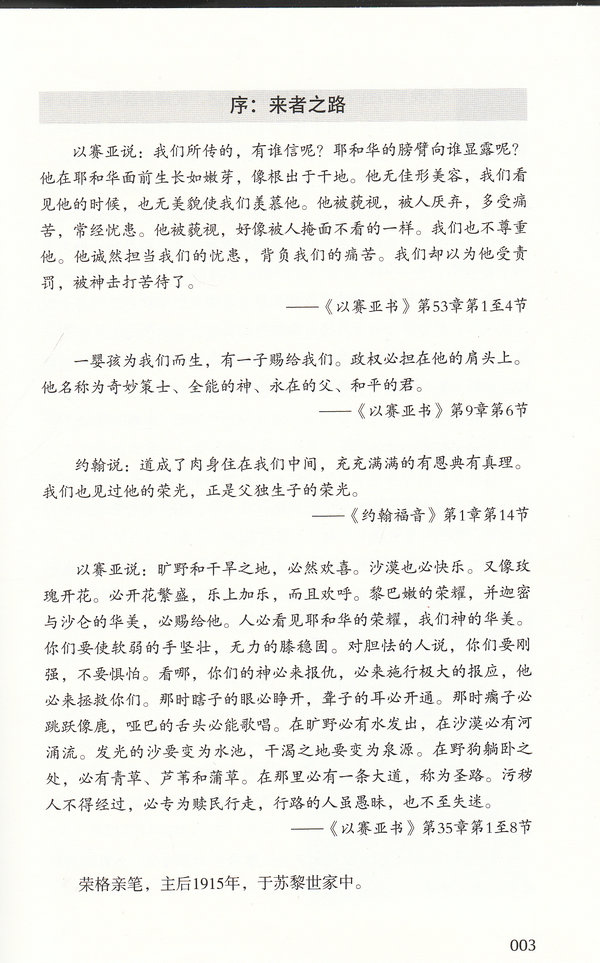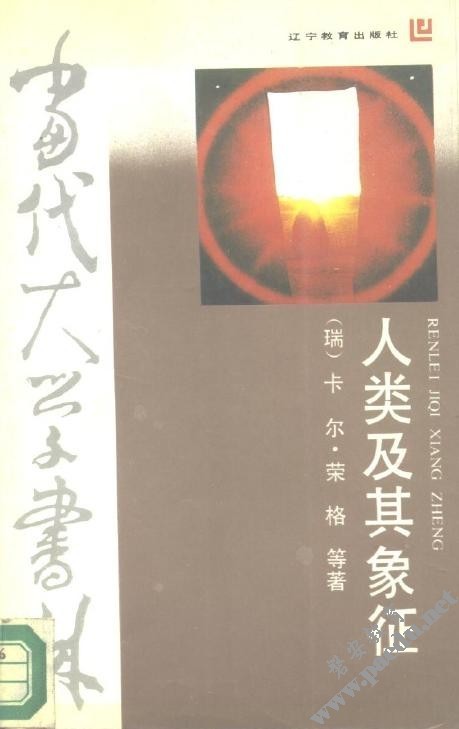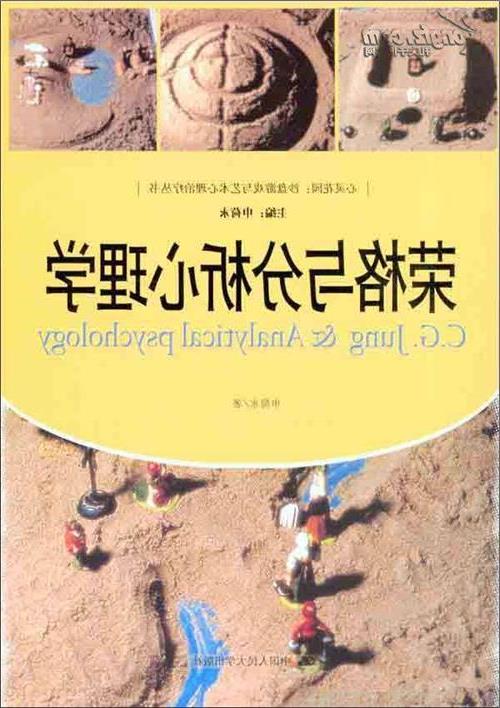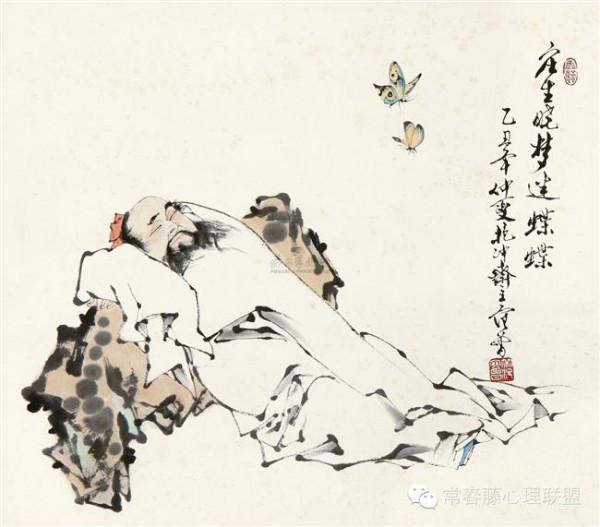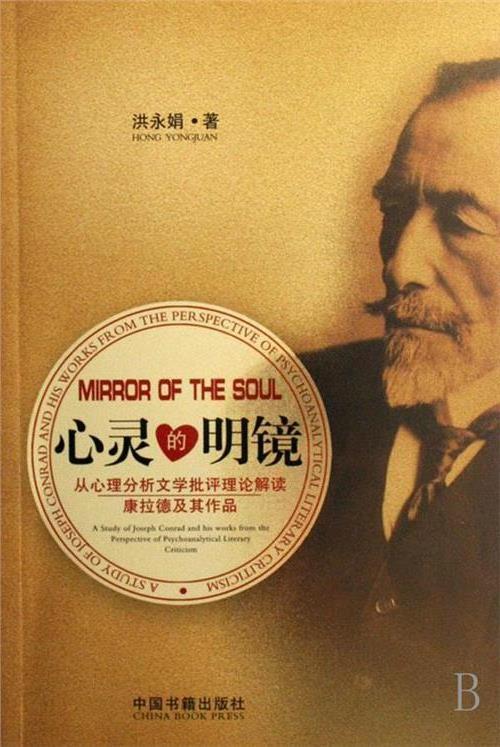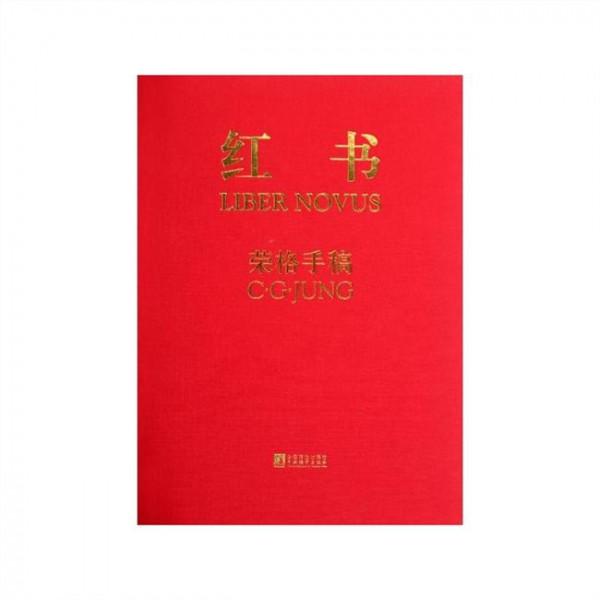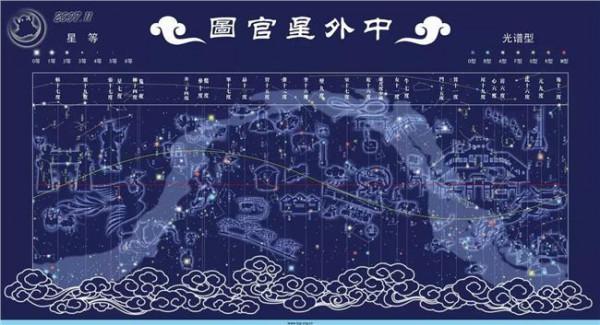孤独中之自我完成—从荣格到荣格心理学
孤独中之自我完成—从荣格到荣格心理学 郭怀慈 杨明磊 台北淡江大学教育心理与谘商研究所,台湾台北 【摘要】 荣格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个人心理学拓展到集体心理学的范畴,其中最具原创性的概念大都来自他对于自身体验的深刻剖析,并将之与各文化或是不同学门之间引申和对话。
研究者发现,作为一个「孤单的小孩」,荣格锻炼出一个特别的能力:观察自己的感受、与之对话,并从古典书籍中寻找智能;这个过程由孤独开始,往内反刍、思索、对话,到与外界建立沟通桥梁的过程,显示荣格一方面锻炼出与孤单共处的能力,同时也从最深的孤独中,试图建立与他人的沟通,当他透过长年的研究终于完成这个了解与被了解的心愿时,也同时创立了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贡献的荣格心理学。
【关键词】 荣格、荣格心理学、孤独 孤独感是古今中外不可避免、富含丰厚讯息的感受,到今天则演变成为观察精神疾病的重要征兆,显见对其深入了解之愈益重要。而荣格,这位心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如何将自身成长经验中的孤独转化成创造和自由,乃至发展出博大精深的荣格心理学,正是对当今社会提供一个不同的看待孤独的角度。
本文即从荣格的生命脉络中,试图分析其个人的孤独经验如何转化为其独特理论。
1 孤独 E. S. Buchholz(傅振焜译,1999)在她《孤独的呼唤》一书中提到:「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向来将孤独看作是精神疾病的前兆。…。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p.
36)她认为:「得到别人认同与追求真实自我,这两种需要只有在被当事人认为是对立冲突的两面,必须二择一时,才不能并存。人要取得这两者平衡才圆满。」(p.38)所以人们要呼应内在孤独的呼唤,Buchholz 并将这段时间比拟为回溯到子宫的生活,认为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身心需要;认可了这份人的基本需要之后,才有空间讨论避免「过度自我」,或是避免「过度融合」,如何在其中找到人际互动的平衡点。
P. Koch(梁永安译,1997)则在《孤独》一书中进一步说明:「孤独并不等同于寂寞、隔绝、隐私、疏离。
」这几个字可能发生于孤独状态下之感受,但自有不同之意涵,依此,Koch 将寂寞、隔绝、隐私、疏离视为孤独的家族,但是不等同于孤独。
Koch 并且用了许多字词形容当孤独被正向的完成之后,其隐含之徳之彰显:自由、回归自我、契入自然、反省态度、创造性;而「孤独因人际之交会而得以圆满」,这里他并引用老子道德经来说明其意涵(要补充一下道德经怎么说……)。
另一位专研「隐士」之孤独的学者 P. France(梁永安译,1994),在他的书《隐士:透视孤独》,对于孤独与人交会之说,则进一步阐释:「与其生活在孤独中而怀有一颗人群的心灵,倒不如生活在人群中而怀有一颗孤独的心灵。
」(p.60)并且认为孤独的完成在于「这种孤独的生活往往不是一种对社会的永远脱离,而只是为了重返社会有所积极作为的一个预备阶段。」(p.
115) 由此,我们看到「孤独」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概念,它会和不同的社会现象连结,也会涉及不同层次的孤独感;个人际遇不同则有不同的感受;最后孤独还会和人际互动共同讨论。这些丰富的意象,我们都可以在卡尔荣格这个人身上看到例证。
2 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 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 年7 月26日生,狮子座,卒于 1961 年6 月6 日,只差几个月的时间,就满 86岁,是分析心理学派(Analytical Psychology )创始人。
分析心理学派后世多称之为荣格心理学(Jungian Psychology ),显见荣格其人与其学术研究之间密不可分之关系。
前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副会长 Murray Stein 试图了解和描述荣格这种研究特质,并称之为:研究他自己的过程(朱侃如译,2006)。 Stein 认为荣格研究心灵有其非常个人的因素,他不只探索病人的无意识心灵,也透过分析自己,将自己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来扩展他的理论思想,将佛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推展到集体潜意识,也由此发展出诸如「积极想象」等实际的工作方法。
荣格一生都在瑞士学习、研究和执业,晚年自称成了瑞士的「伯尔尼熊」(李亦雄译,1998),也就是戏称自己成了瑞士观光旅游的景点之ㄧ。
他于自传中(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称呼自己的童年是一个「拥有秘密的孤单的小孩」,到了80 岁时,则以下列文字表明心迹:「我是个孤儿,举目无亲;我浪迹天涯,我是一个人,与自己对立,我是个年轻人,也是老人。
…对每一个人来说,我是必死的,我不在时光的轮回中。」(p.207) 依此看来,荣格对自己的定义由孤儿开始,但是通过了 J.
Campbell(朱侃如译,2003)所称的英雄之旅的历程后,从中得到解放和自由:「不在时光的轮回之中」;所以研究者在这篇论文中,试图贴近荣格从童年期的孤独感,并观察他如何经历孤独并转化孤独。
荣格晚年自况:「我的一生只是让我的潜意识充份发挥。」(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当荣格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一生定位的时候,他的心中想必十分欣慰,因为和潜意识相遇的过程必然充满挑战,也会遭遇满是荆棘的黑暗面,但是他已经尽力面对,并让其充分发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荣格的理论就是肯定每个人都有机会踏上整合潜意识的旅程,而当他宣称自己做到了,等于是告诉后人这是一张有用的、可行的地图,而有为者,亦若是,大家都有可能作得到!
所以这句话中,应该也满是对后人的期勉。 3 从荣格看孤独之德 3.1 孤单的小孩:隐私和孤独之关系 直到九岁时,妈妈又生了妹妹之前,荣格没有其它的兄弟姐妹。
这个孤单内向的孩子,花了最多的时间自己游戏和思考(蔡昌雄译,2004),许多影响荣格一生,甚至贯串其终生思想的早期记忆,包含了梦境、自创的仪式、游戏…等,都在荣格的童年时间发生(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
比如说他常常坐在石头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思考着:「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我呢?还是上面坐着他的石头?」(蔡昌雄译,2004) 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如此认真的思考这样的抽象问题,的确不是常见的事。
这样的提问法,和中国道家思想家庄子,梦后醒来问的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是庄周梦到了蝴蝶?还是在蝴蝶的梦中成为庄周?」 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大都会创造一些属于自己或是同伴的仪式,这些扮演游戏可以帮助孩子适应当时的环境,或是学习社会化,但是小荣格将这些点点滴滴都藏在心中,并认为自己童年岁月的本质就是「心中藏有秘密」的小孩。
他从来不对人说对于耶稣会士的恐惧,或是对于石头和小人之间的对话,或是三岁时关于阳具的梦…。
这样努力藏住秘密,对他的生命「造成一种几乎难以忍住的孤独」 (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 一个三岁的孩子,没有将令他恐惧的梦告诉任何人,而选择将秘密藏在心中,这是和一般孩子很不一样的决定,他的本能似乎已经告诉他,他必须一个人孤独的探索这些秘密。
可能正由于自身深刻了解保守秘密的痛苦,和经由遗忘秘密可能对人造成的心理和行为伤害,他在后来和病人的工作中,致力了解他人心中的秘密,透过让隐藏的秘密曝光,避免沉重的秘密(如被人格面具压抑而深潜在无意识的阴影)影响个人正常的思考和生活。
为了探索人心中的秘密,他并且实际发展出不同的工作法,如:「字词联想」、「梦的分析」,来了解潜意识底下未被意识知晓的秘密…(蔡昌雄译,2004)。
在这里我们看到「秘密」对于孤独造成影响的两种面貌,一是因为要保有秘密,而努力培养自问自答、独立思考的特质;二是因为秘密压抑在心中,而造成内心的疏离甚至扭曲,当扭曲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要隐藏的越来越费力的时候,则成为精神疾病,这方面已经由佛洛伊德对于无意识研究的发现,而逐渐为世人了解,荣格则在瑞士以字词联想来对这方面做研究。
所以 Koch(梁永安译,1997)认为隐私并不等同于孤独,却是孤独的重要家族。
当有秘密藏在心中,不能对人诉说,以荣格的语言就成为:对生命「造成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孤独」(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心中藏有许多秘密的人,即使在人群中也会觉得孤独,这种情形 Koch 则称之为「在互动中的孤独」 (梁永安译,1997)。
我们从荣格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种形式的疏离。 3.2 在孤独中回归自我 作为 12 岁的小学生,荣格有一次特殊的体验,他认为自己被迫产生了一些恶毒的想法,他极度害怕自己会因此犯下最恶毒的罪:反对圣灵的罪愆。
但是他越是反抗思考,力量越是强大,终于,当他抱着进入地狱的决心,让思想直接冒出来而不加以抑制的时候,他看到了坐在天上宝座的上帝,拉下屎来打坏地面上庞大精美而辉煌的教堂(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
这样的画面对一个努力跟随上帝的孩子来说,真是沉重。他觉得自己是得不到恩宠者,同时又是上帝的选民;既被诅咒,又被祝福(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
荣格用了强烈的字眼来形容这个情境,而这又成了另一个要被保守的天大秘密,让他更清楚自己的孤独,同时,也和父亲和家人(许多长辈都是牧师) (蔡昌雄译,2004)的距离越见遥远。
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是因为服从上帝、不再对抗,于是上帝才向他显示祂的智能和仁慈,给予了小荣格重要的讯息:祂召唤人们,分享自由,「强迫人们放弃自己的观点和确信的事物,好毫无保留执行上帝的命令。
」上帝反对遵守传统,不论何等神圣(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 在荣格的回忆中,这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从此影响了他对上帝、耶稣、和教会的想法,并认为个人要从自身体会上帝的恩典,否则会陷入他父亲后期所面对的困难:没有实质体会的干枯信仰(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
从完全孤独中,直接从内在体会上帝恩典,Koch(梁永安译,1997)形容为「回归自我」的完成。
France(梁永安译,1994)对隐士之研究,提到一八三三年诞生在孟加拉国地区的拉玛克里希纳,有相似的形容:「他试图透过孤独和苦修,跟迦梨女神有直接的会遇。…一个人住在森林里隐修,历时十二年。
…有些人说,他祈祷和静坐的时候,会有小鸟在他头上啄食脏东西,而蛇则盘缠在他身体上。不管是蛇、小鸟或是拉玛克里希纳,都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p.228-229)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荣格只有十二岁,并且与家人同住。
但是感受到的孤独感却是相似的,他以自己的形式,奋力完成内心中与上帝的直接会遇。荣格似乎为我们指出一个可能性,从孤独中完成「回归自我」的旅程,不一定是在遥远的地方,或是远离市集的山林,甚至与年龄无涉,而可能更与坚持和勇气有关。
3.3 孤独中之外在涉入 1913 年和佛洛伊德决裂之后,荣格陷入崩溃,和自己精神上的父亲—佛洛伊德决裂,严重打击荣格,使他陷入后来将近十年的黑暗期。
这种陷落的严重程度,似乎是另一种形式的丧亲历程,必须透过长时间的疗伤、自省…才得以走过。但是当他走出这段黑暗时期后,他以自身经验提出中年危机亦即转机的看法,丰厚了自体化历程的理论。
这段时间,他与同事朋友们疏离,停止大学的教职,接案量减到最少,几乎完全从俗世退出(蔡昌雄译,2004)。 在他的回忆录中(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提到这段时间他多在湖边散步,观察水中生物、玩沙、玩石…;在和自己相处的过程中,他看到内在心象、也听到声音,从看到的景象,他甚至预测到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这些种种奇特的经历,有人将之描述为荣格的精神分裂过程(蔡昌雄译,2004)。 在此时期,他也遇见了自己的心灵导师——菲利门,菲利门是一个有翅膀的智慧长者,他在荣格接下来的生命中,一直扮演指导者的角色(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
有人认为这是荣格内在智慧老人原型心像的投射(蔡昌雄译,2004)。
在荣格的描述中,菲利门则是只有荣格才能看到的个人心灵指导者(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 以 Koch(梁永安译,1997)的说法是:在孤独中,仍有外在存在的涉入,「这一类的涉入林林种种,有出之以间接的方式的,有出之以拟人化的方式的,也有出之以『底景』的方式的。
」(p.112) 以荣格的处境来说,他的孤独中有家人(妻子、孩子们…)环绕作为底景,有拟人的菲利门代表智慧的对话者,有整个大自然作为间接的思索对话对象,…。
使他虽在精神上退居个人的孤独世界,生活上仍有家庭支持,内在则有智者和大自然与之对话。 在这片交织的立体网中,我们看到退避孤独状态中的荣格,仍有外在世界的存在,他曾经特别提过:家庭是支持他不崩解的重要因素(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
以Koch(梁永安译,1997)的语言来说,孤独中仍有各种对话在发生,即使只是和自己想象中的内在对话。这种形式的对话,从荣格的经验来看,是意义深远而且深具启发性的。
3.4 孤独之完成:人际交会 荣格形容自己是孤独者,但是从他的回忆录(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 中,我们看到他在布勒霍尔兹利精神病院工作期间,有能力聚集众人组织研究机构;与佛洛伊得相识之后,担任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一任会长;隐居湖边的同时,则在附近与友人共组联谊性的俱乐部;…一直到后来分析心理学发展起来之后,他组织或是支持参予了各种大小不同的活动,互动的人群涵盖心理研究人员、物理学家、艺术家、政商贵贾、新兴媒体到一般大众。
这样的人际互动其实是非常全面而广泛的立体网络,网络中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为分析心理学提供贡献,也在其中找到各自完成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研究者认为,荣格除了有他自己较为熟悉并认同的内倾人格,同时也具备有和人沟通互动的外倾人格特质。后者让他在往内以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同样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希望找到适宜的沟通和对话方式,透过这样的沟通努力,他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以免被当作是疯子(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如他自己所说:「在埃菲尔士峰是不可能有个性的。
」他决定回到人群,从前人或是既有的知识中了解自己,找到语言和人们沟通,这个社会则因此多了一门横跨广度和深度的心理科学,引导危机中的人们,把握机会成为生命的转机。
Koch(梁永安译,1997)以易经中的太极图来说明这种孤独的特质:「如果把阴比做孤独、把阳比做交会的话,…在阴的中央位置上,有一个代表阳的白点,而在阳的中央位置上,有一个代表阴的黑点。
…在交会的极致中,人有可能会突然体会到最深沉的孤独,而在孤独的极致中,人又可能会突然体会到最深沉的交会。」(p.131-132) 3.
5 孤独与创造力 从孤独的极致中,从单一个体即含有所有存在状态的概念中,荣格似乎发现这个单一个体可以同时含容外在世界,依此,他将个人意识中之无意识,扩展到集体无意识;将外在伴侣关系往内在世界收摄,内化成为内在男人或是内在女人与自己的关系。
以荣格提出的 Anima 与Animus 的理论概念为例,他认为:一、如果我们没有将外在伴侣,作为自己内在状态的镜子,则失去自体化整合的契机。
二、对于没有外在伴侣的人来说,要了解内在 Anima或是 Animus 并且做整合,是一件挑战度更高的工作(Jung,1931)。亦即荣格将外在伴侣视为内在状态的往外投射,学习者应将这样的投射收摄回自身,变成对自身的了解和整合,因为我们对外在伴侣的所有认识,其实都属于我们内在已知或是未知的自我概念。
这是关于男女关系中「我即是他,他即是我」的概念,从孤独的我出发,映照到他人,再回到一个意象更丰厚的我的身上。
又如荣格(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提到,从 1902 年一直盖到 1956 年的石造塔楼,代表他发现自我本来面目的过程。一开始是遗世独立,探索「我」的各种意涵和形式,到了 80 岁的晚年,荣格与塔楼的关系,已经拓展到和祖先、妻子、以及后代的连结。
这时候,屋子代表的不只是他本人,也是他与外界关系的界定,同时,透过其中呈现的精神样貌,使得作为屋子这个别具深意的容器,可以涵纳祖先的精神以及孩子的未来。
他在自传中提到:「当我在石板上刻字时,我意识到了命中注定要与我的祖先产生种种联系。」(p.303)(刘国彬、杨德友译,1997) 所以这个塔楼一开始代表荣格本人自我探索的过程,经过数十年的演化,塔楼──我──中已经有了上自祖先,下自子孙的整体意涵。
所以研究者推论,荣格在自我感到孤独的过程中,渴望了解与被了解,他以此为动力和养分,探讨如何将个体我中感受到的一切,用他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从中发展出理论、概念…,最终成为理路绵密又同时保持变动弹性的分析心理学。
他在孤独的我中,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 4 结语:孤独与交会──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我们观察到,从小备感孤独的荣格(刘国宾、杨德友译,1997),从大自然为起始点,开始内在整合,感受到自己与他人并存的一体、与上下世代连结的开阔、与在时光中悠游的自由:「把人生看成来来去去、循环不息的现象。
」(p.308)荣格完成了此生自我提炼的过程,将孤独之徳发挥到极致之美。
同时,以孤我为基石,又与外界保持相互涉入关系时,反而创造了一个意象丰富的大我意涵,每一个个体的「他人」,都成为了「我」的一部分;亦即:「在孤独的极致中,…体会到最深沉的交会。
」(梁永安译,1997) 对应到易经的智慧而言,古人并没有将阴与阳当做线性的两极,而是以圆形中彼此涵扩来形容极致之阴和极致之阳间变动之可能性。当个体之孤独发展到极致,终而将所有他人涵扩进入此个体我,使得「我即是他,他即是我」,即是来到另一极:所有存在物之间有着隐密的秩序与统一性(朱侃如译,2006),这是荣格之另一发现,原型可以从心灵的母体内部,也可以从外在世界,甚至同时从两方面进入意识;由此,他提出了同时性的概念,也来到另一个境界:孤独(个体)是阴的一极,交会(外界)是阳的一极,当发现两者其实是同时存在而且相互影响的,就成为一个整合的太极图形。
作为临床工作者,当看到孤独不同的面貌,和其发展出来的可能性,在面对求诊者的孤独感时, 我们会更容易帮助求诊者发现孤独后面潜藏的交会的潜能和丰富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