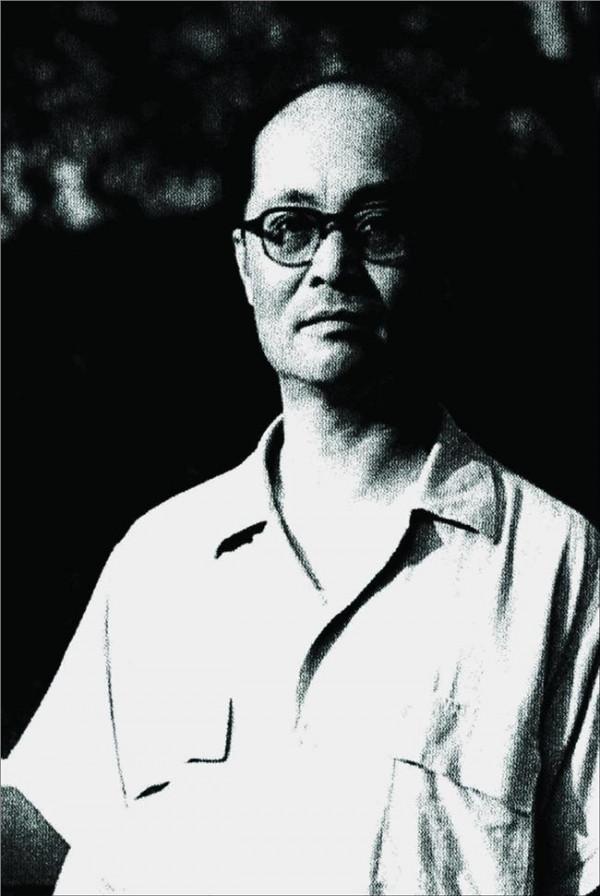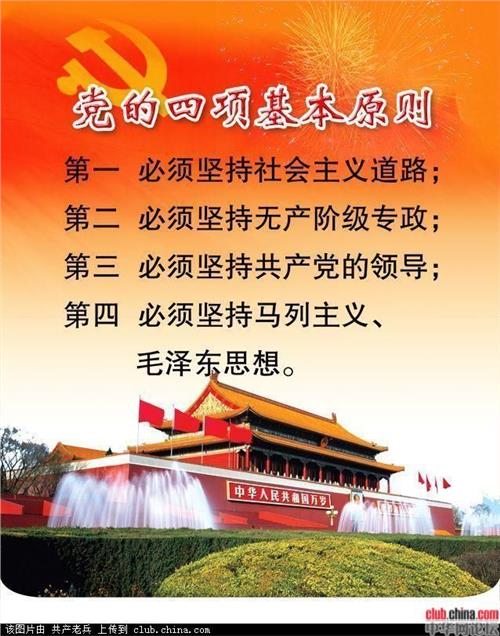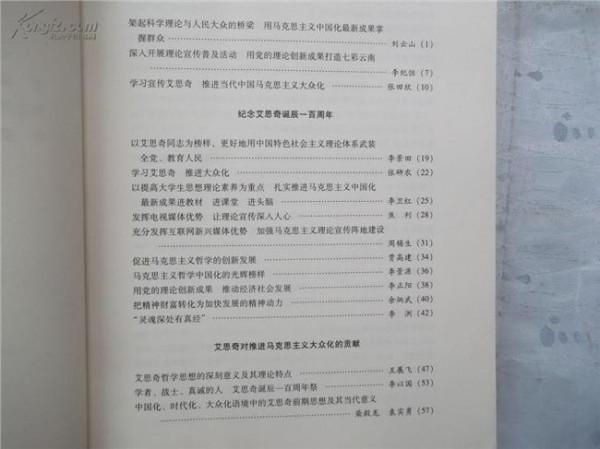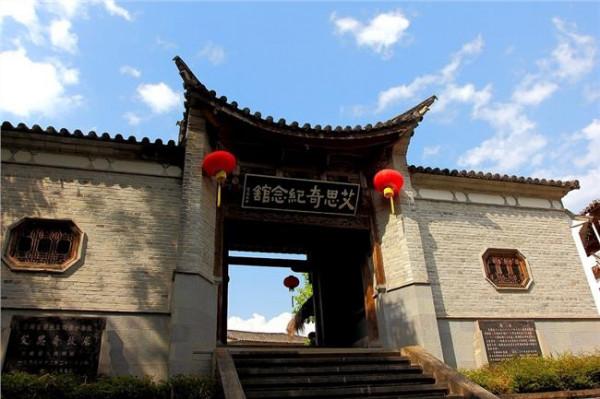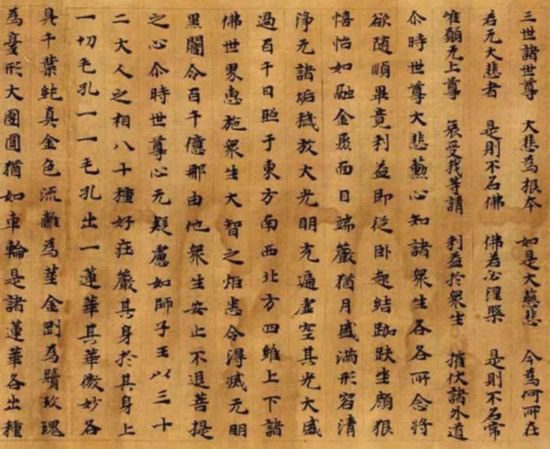艾思奇毛泽东 艾思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的发展历史上,艾思奇、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非常突出的,是这段历史的研究者谁也绕不过去的重点研究对象。中国学术界通常把他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奠基人、开拓者。
然而,以往对他们的研究一般都是分别进行的,至于他们之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理论关系,则较少有人展开细致深入的探讨。本文打算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艾思奇、毛泽东当年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路、见解和方法,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新形态,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国家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和阐述
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实践需要,使艾思奇、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在理论上予以论述。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是适应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实际需要而传入中国的。它和中国历史上一切外来思想文化一样,从传入中国的那时起,实际上就开始了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中国化”的过程。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在经历了1927年的严重挫折之后,就初步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并在实践中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历史发展发生重大转折,中国社会矛盾发生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他们对中国化问题的探索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艾思奇、毛泽东作为这个时代的先觉者,最早感知时代发展、社会实践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理论需求,并且自觉地将这种理论需求具体化为一种理论呼唤,同时展开理论论证。
1938年4月,艾思奇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在这里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在这里初步阐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概念提出并初步阐述的历史根据有二:一是抗战的实践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上了议事日程。艾思奇在文章中说,在“抗战之伟大的事实”面前,中国人究竟如何面对这场战争,是彻底坚决抗战还是妥协乞求和平?这就涉及到人们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而这些正是哲学的内容。
因此,“正确的哲学运动如果做得好,它可以从思想方面的基础上帮助我们的团结,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们抗敌的力量迅速地坚强起来。
这是一个推动的作用,并非没有意义的”。艾思奇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哲学运动,就是“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二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必须向中国化发展,不能止步于通俗化。为此,艾思奇在文章中专门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历史发展的角度做了说明。
他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按:指在这之前的以《大众哲学》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如果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够获得相当成果的。
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
”[1](PP490-491)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之后,艾思奇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了初步阐述。他明确指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
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而不是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做支配一切的死公式”。
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艾思奇在文章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概念,而是用了“哲学研究的中国化”
这个比较中性的概念,但在文章的最后,艾思奇还是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有一个中心,“这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并且说明这个中心的确立是因为“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的争论”。[1](P491)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步学界所说的“新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在艾思奇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发表半年后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了最为经典的论述。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解决的问题。
”[1](P492)①毛泽东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马克思主6义哲学在内。因此,同样应该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区别只在于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而中国化的基本思路和深刻内涵则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段论述,是中国革命发展实践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它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认识,已经摆脱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和束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直至今天的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表述,可以说都是这一经典论述的展开和发挥。
艾思奇和毛泽东都是在1938年明确提出中国化问题并展开理论阐述的,这似乎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然而在这种貌似巧合的偶然性的背后,是时代必然性在发挥作用。而这样的必然性则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根植于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
当社会实践发展的某种客观需要被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观意识所感知、所把握,也就或迟或早会形成一种主观意志和主观要求,并以一定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成为指导社会实践、主体实践行为的指南。这就是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来自实践;而从理论本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由通俗化向中国化发展,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
就像艾思奇说的,只有真正做到了中国化,才能够充分的通俗化。通俗化和中国化既相互渗透、不可分割,又有层次上的差异和超越的必要。正因为如此,艾思奇、毛泽东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根据共同的实践需要,在同一年中先后意识到中国化的必要性并展开理论阐述,也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然而,由于艾思奇、毛泽东两人身份和立场的差异以及理论视野的不同,这就使得他们关于中国化的理解和表述各具个性特色。可以这样说,艾思奇主要是从理论研究和传播的角度,毛泽东则侧重于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革命道路的角度来阐述中国化问题的。
艾思奇基本上是个学者、哲学家,他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特点出发,阐述从通俗化向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必然性,以及通俗化和中国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什么是中国化的问题上,艾思奇强调从中国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再把这种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导我们的思想行动”,指出“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
由此可见,他的基本立足点是在理论本身,即理论本身的发展。他虽然也讲到了应用,讲到了理论指导行动,但并不具体。
毛泽东是个革命家,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他的使命和视野决定了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出发,将思考的着眼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特别是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尤其突出的是他作为中国革命发展实践的具体参与者、领导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有更独特的体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危害有更深刻的认识。正是这方面的独特体会和经验教训,使他对什么是中国化比作为学者的艾思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阐述。
因此,像“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抽象地应用它”这样的话,只有亲身经历过抽象应用(教条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痛苦的毛泽东才说得出来,而没有这方面经历的艾思奇则不大可能,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亲身体会和经验教训。
这就如同毛泽东也不可能从通俗化与中国化辩证关系的角度来阐述中国化问题一样,因为他同样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教训。
艾思奇、毛泽东关于中国化的理解和阐述虽然各有特色,但基本思路和主要着眼点则是比较接近的、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都强调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吸收哲学的养料,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用它们来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在这里,具体应用、丰富发展、7指导行动是他们两人共同强调的重点,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