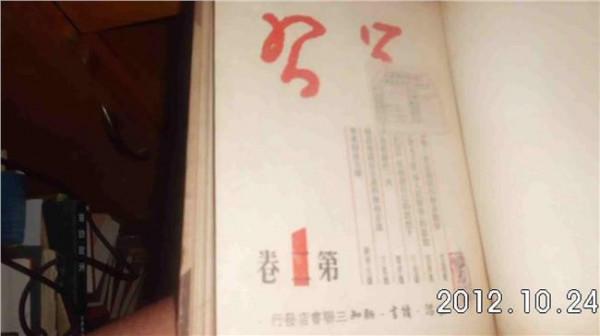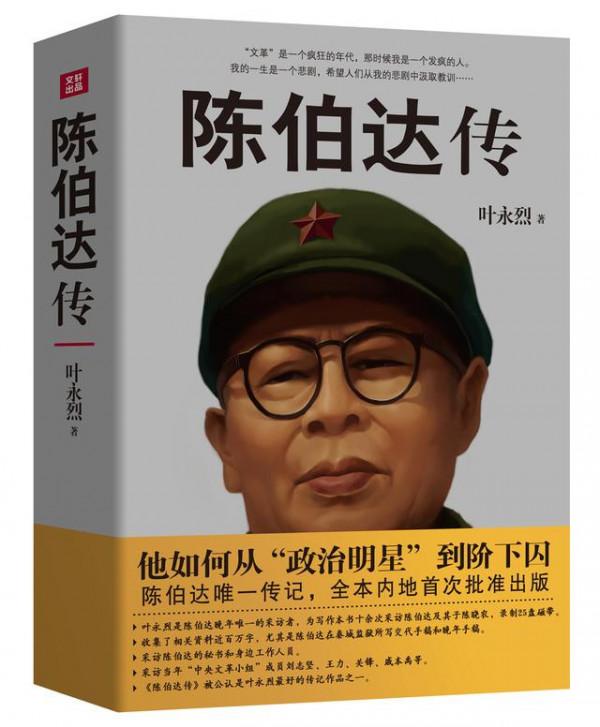陈布雷和田家英 萧象:陈伯达和田家英恩怨探微
陈伯达和田家英为上世纪40——60年代中共党内两大秀才,陈长田18岁。抗战时期两人相继到达延安,并分别于1939年和1948年入幕为僚,成为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成为毛泽东秘书之前,陈伯达与其有过一段师生之情与上下级之关系。
在此之后,两人在上下级之间,多了一层同僚之谊。满腹经纶的陈伯达和青年英才的田家英都深得毛的厚爱与信赖,从延安窑洞到京城中南海一直伴随毛泽东身边而不离左右,在陈、田的政治人生,这自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然而,不幸的是,两人之间的关系没能因同为领袖秘书而增进,反而因此出现纠结,产生矛盾。这种纠结矛盾发生在最讲矛盾的领袖身边,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荣辱进退,而渐次扩大升级,最终演变成一种让人无法释怀的怨恨。
以至于今天,人们论及陈、田,还以此作为抑扬褒贬的是非判断。这种发生在两位秀才之间多少沾有文人相轻式的纠结恩怨,在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中并不罕见,但由于两人“南书房行走”的特殊身份,和先后坠入政治深渊的命运结局,其恩怨纠结不能不包涵着某种历史的悲剧因素,折射出一定的历史经验教训,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考察价值。
据知情人披露,陈伯达与田家英的矛盾在建国之初就露出了端倪。1953年陈伯达与胡乔木、田家英一道受命起草宪法,“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田家英同陈伯达之间,常常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陈伯达霸气十足。由于胡乔木在毛泽东召集的起草小组会议上对陈伯达提出的初稿提出批评修改意见,陈曾经在会后大发雷霆。
胡、田为顾全大局,以后凡有意见都事先向陈提出,而胡、田二人意见常常一致或者比较接近。陈伯达驳不倒他们,十分恼火,就消极怠工,多次发牢骚,说要回家当小学教师。”(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而矛盾的因子,则伏生于1940年代后期的延安。“当时有一个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是副主任,田家英为该室经济组后为政治组的研究员。陈写了几本书,田曾帮助他搜集了很多材料。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搜集资料的工作十分困难。书写出来以后,陈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却问田家英:你做了什么工作?这件事使田很寒心”。(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另有一种说法,谓八大之后,陈伯达在八大决议上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表述,为毛泽东所否弃,陈因而受到毛的批评,一度苦闷,“有天之骄子之感”的田家英“因陈伯达的失势而十分得意。陈伯达觉得自己处于困难时期,田家英不但不帮忙,反而喜怒于形色,心中渐对田家英产生隔膜”。(张希贤:《陈布雷与陈伯达——踏在中国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位秘书》395页)
从上述知情人与研究者两种角度各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相同的印象,这就是,陈伯达与田家英这一时期存在的矛盾缘起于性格冲突,大抵是文字之争大于观点之别,意气之斗盖过思想之歧,荣辱之竞多于是非之辩,相当程度上带有文人相轻的意味。
以此做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虽然存在这种相轻的纠结,乃至争论,他们正常的工作关系与人际交往似乎也并未因此受到大的影响和妨碍。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是,在接下来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陈、田两人留给历史的记录,毋宁说是同舟共济的“兄弟”。
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7月23日指责右倾的讲话“一日之间,庐山会议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纠‘左’变成反‘右’了。”“这有若晴天霹雳,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愕然、茫然。会后乔木独自径回住处,家英、我和陈伯达等一起沿河东路西行,走过仙人洞,一路上默默无语。” “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四人被揭发,中央在立案审查。”(吴冷西:“与家英共事的日子”,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这就是说在标志党内政治重大分歧的庐山会议上,陈、田立场一致,观点无二,知识人的良知使他们都是站在了正确的一方。他们一并成了同一条船上的“难民”。
陈、田关系出现变化,双方矛盾明显于外,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60年代。对此,当事人之一陈伯达有一个说法:
“《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在广州会议上通过以后,没有几天,田家英跑来找我,本来他也参加了文件的讨论,可是这时却忽然对我说,六十条搞得不好,应该重新另起草一个文件。我一听就批评他:你这个人才糟糕呢,中央刚讨论通过了文件,你怎么就这么说话?我的批评很严厉,他听了很窘迫。
这就是他跟我发生矛盾的原因。他当时想转移话题,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我们要是去香港看看多好呀!我听了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想去香港,他说他有个哥大概现在在香港。
我于是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说他有个哥哥过去曾在中央社工作过。我没有再说话,因为田家英是我推荐给毛主席的,我应该对他的政治情况负责。他有这么重要的社会关系,过去却没有告诉我,我当然有意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广州会议是在1961年3月。到了1962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期间,双方关系骤然间发展到一种严重的僵化地步。吴冷西在“与家英共事的日子”中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种情景:“家英告诉我,陈伯达现在主持起草决定,神气得很,碰到家英不说话,不打招呼,装作没看见。”
“不说话,不打招呼,装作没看见”,足见关系之僵,矛盾之大。但吴文没有说明何以出现这一情形的具体原因。从庐山风云到北戴河会议,时间不过两年,落难同志形如陌路,变化之速与巨,未免让人难以理喻。即使有广州对田家英的严厉批评和不满,陈伯达似亦不应至于如此对待自己的同僚与下属。其中是否另有他因?
果不其然,从《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我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请看陈伯达接续广州的叙述:“这次谈话虽不愉快,但觉得事情既然过去,也就算了,后来也没跟毛主席谈起过。回北京后,我有时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还是约上他一起去。
直到有一次在北戴河,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田家英说你什么吗?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毛主席叫来江青,对江青说:你把田家英说陈伯达的话跟陈伯达说说。他有意见不跟我当面讲,要去跟江青讲,想通过江青影响毛主席,这就使关系难恢复了。”
原来如此。是来自第三方的因素,也就是毛泽东因素的掺与和催化,陈、田关系才发生如此急速的戏剧性的变化。我们无法确定陈伯达当时听了毛泽东的这一番传话,心里是怎样的反应,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前引吴冷西叙述中田家英遇到的戏剧性场景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通陈伯达对待田家英的那份态度。《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涉及与田家英矛盾关系的唯此一处,就是这惜墨如金的一处文字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珍贵的历史信息,为我们释读陈、田关系提供了一把解密的钥匙。
无论从上下的关系,还是从年序的人伦,田家英都会主动向陈伯达打招呼,但这一次陈竟然不予理睬,“装作没看见”,刚直耿介的田当然会气愤不过,也轻易不会消解这一气愤。但是,他哪里知道这是自己不久前的一次投诉,却被主公又将投诉内容原本传给了投诉的对象的直接结果。当然,陈伯达也不会想到主公此番传话于己背后所隐藏的玄机。
田家英告诉吴冷西,陈伯达对自己“不说话,不打招呼,装作没看见”,陈伯达则认为,从此“关系难恢复了。”据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做出这样一个判断: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传话于陈,是陈、田关系发展的关节点与转捩点,它于无形之中激化了两者之间潜在的矛盾,将心存芥蒂的陈伯达与田家英推向关系恶化的前行轨迹。
如果说,在此之前两人存在的矛盾尚可调适,也无大碍,那么在此之后,陈、田之间则成见越来越深,积怨越来越大,以至终身不解。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要传话于陈?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传话于陈?我们可以认为田家英挨了批评,心中感到冤与怨,碰巧有机会诉苦于江青与毛泽东,毛一时气下,就机转告了陈伯达。这诚然是一种解读,一种基于普通人的简单的常理解读。不过,鉴于毛泽东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当时党内斗争激烈复杂的历史背景,笔者愿从事情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考察的角度,进行另一种解读。
如所周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凭着自己的强权和威望打倒了彭德怀,取得了表面上的一时胜利,但接下来的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大饥荒使党内外不满情绪急剧上升。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和随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向来关于形势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比喻判断已不适合当前的严峻形势,而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
刘的这一看法获得党内普遍共鸣,却又一次触动毛深藏于内的那根敏感神经。就在此时,田家英衔命下乡调查,返京汇报,其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在刘少奇处获得支持,而在毛泽东处情形却大不相同: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这种情况,同刘少奇性急地打断田家英的汇报,滔滔不绝、毫无保留他讲出自己的意见,完全不同。最后,毛突然向田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他问住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他毫无准备。毛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答:‘是我个人的意见。’当时,毛没有表示意见。”(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没有表示意见就是最大的意见。庐山会议上,田家英、陈伯达作为毛泽东身边的秀才抱成一团,站在了彭德怀一边,田家英私下更说出“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的针对毛的三条意见,被泄露于众,毛泽东已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虽然隐忍不发,宽宏大量地把手下秀才保护过关,却并不等于秀才们已与过去一笔勾销,从此毫无牵挂,可以高枕无忧。这仅是毛泽东留用教育,以观后效的一种政治与用人策略。在党和国家两位主席相互较劲、党内政治斗争呈现激烈的重要时刻,田家英的此番汇报,让毛泽东又一次看到身边的田与自己相左,且“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毛对田的评语),毛不仅大失所望,更有一种隐忧,甚至怨怒。
毛不能不要有所表示。毛自然清楚田家英与陈伯达之间的微妙关系,然而他两在庐山上的抱团表现却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分而治之的妙用,毛了然于心,他要证明,他既能治天下也能治左右。于是,在随即召开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不仅有了毛传话于陈、陈对田视若不见的奇怪一幕,也有了毛重新突出阶级斗争、批评田家英、反击刘少奇右倾单干风的重要一节。
如果这种释读不无道理,能够成立,那么可以说毛泽东的传话于陈是施展其政治权术的一回经意安排,是为增加赢得党内斗争胜利筹码而打拉结合的一次牛刀小试。这也就意味着陈、田关系走向僵化乃至破裂与当时党内激烈复杂的斗争之间有着某种令人心悸的幽暗联系。田家英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在当时的年代,对任何共产党人来说,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何况秘书的田家英。田曾一度“引用唐代韩愈《进学解》中说的‘投闲置散,乃分之宜’,其心情可以想见。”(吴冷西语)但田家英直言无忌的秉性并未因此而改变,当罗瑞卿针对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一说征询田的意见时,田家英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并说出“‘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站不住脚的”这一反对的理由。
(陆石:“我心匪石”,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无疑是敏锐的,也是正确的,可也是犯忌的。随着文革风暴的来临,党内斗争的白热化,罗瑞卿与杨尚昆先后被打倒,田同罗、杨的关系就变得可疑,田反对“顶峰”之说被揭露,也就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更何况1965年12月田删掉 “海瑞罢官要害”的纪要事件,田家英这位毛泽东视为“右倾的秘书”在其看来已完全走向了反面,没有了使用价值。
于是,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一道,1966年5月田家英被中央立案审查。田家英因此而绝望自杀。
田家英因绝望而自杀。陈伯达一时风光,晋升为党内第四号人物。然而昙花一现,好景不常。陈伯达从政治秘书成为政治局常委、由幕僚进入决策,不久便与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文革主张出现分歧而受到毛的冷落,并于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毛清除出局,其政治结局比田家英更惨,也更具悲剧性。田家英在毛身后即获得平反,而陈伯达至今仍背着反党的黑锅与骂名。
自古文人多相轻,从来幕府生是非。田家英耿介而率性,陈伯达敦厚而拘谨,两人因性格冲突而出现纠葛,由工作摩擦而发生矛盾。在党内斗争异常激烈复杂的1960年代,在雄才大略又精擅权术的毛泽东身边,这种个人之间的纠葛矛盾极为不幸地被主公巧加点拨与利用,演成无解的怨恨,两人也在政治的漩涡中心起伏挣扎,最终无一幸免地先后成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殉葬品”。
此中所折射出的沉重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足以让后人哀叹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