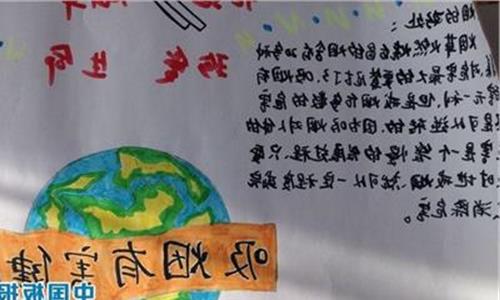曾山曾生 广东省军区教导大队政委曾山执着的追梦人生
记不清哪位诗人曾经吟颂:“梦想是玉,敲出星星之火;梦想是灯,照亮夜行之路;梦想是火,点燃熄灭之灯;梦想是路,引你走向黎明。”
我是个多梦的汉子。年幼时尤其是中学时代我美美地做着作家梦、诗人梦。这源于祖父对我的影响。祖父对我寄予厚望,在我还不懂什么叫“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时候,就要我“跟着学”,尽管似是“对牛弹琴”,但他的目的是让我从小受到熏陶。可喜的是,祖父的心血没有白废,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开始模仿着别人的作品“吟诗作对”了,尽管大部分的所谓“诗文”都是“顺口溜”和“白话诗”,甚至是带“病”的文字,但毕竟在他孙子辈中,我最早从“诗文”找到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对文学写作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且常常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男儿立志从文事,语不惊人誓不休”,以致自己把文学比作是自己的恋人,时常达到“此处果有所乐,我即别无所思”的境界。我的作家梦、诗人梦也就起始于此。许多年后,每每回想起祖父的良苦用心,才发现这对我的人生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虽然祖父早已作古,但祖父的教诲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爱是一种诱惑,奔向爱如同奔向自缚。著名作家欧阳山说过:“文学是一项粉身碎骨的事业。”对欧阳老先生的说法,我不敢妄作评论。但我至少有这样的感受:文学之路,是血与汗交替的路。为了圆梦,在中学时代的数年时光里,我把太多的精力倾注到了这项“粉身碎骨的事业中”,虽然我的作品频频在各种作文赛中获奖,但因为痴迷于文学而分散了我的精力,我没有成为理想大学中的“天之骄子”,还因为执著于文学,我曾两次在暑假与几位同学瞒着家人远走他乡,说去“体验”生活,说去 “考察”社会,说去寻找灵感,过着“流浪的日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不辞而别”,使得善良的母亲多次到神前佛后磕拜,祈祷上帝保佑我平安。整个中学年代,因为痴迷于文学梦,我吃尽了人生不该吃的苦。
为了体验生活,我与我的同学曾尝试着住过工棚,露宿过火车站,甚至坐过“霸王车”。我的人生之路一直顺畅,不论是年小时在乡下,还是稍长时迁到繁华的都市过着幸福愉快的日子,及后来为了寻梦来到军营,我都从来未受欺凌,未遭白眼。
尽管也有些许不如意,但鲜花、笑声、喝彩声、掌声始终是我人生的主旋律。但为了追梦而外出“流浪”的日子,使我体会到了 “流浪者”的疾苦,应该说,“流浪”使我读懂了人生。
火热的军营,男子汉的图腾。我景仰猎猎飘扬的军旗,我崇尚身着军装时无限荣光,我羡慕威风凛凛的将军,我向往硝烟滚滚的疆场,我梦想有一天率千军万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卫戌边疆!为了圆梦,1990年冬天,我从“象牙塔”里出来,携笔奔赴火热的军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与许许多多的军人一样添了一个新的梦想——将军梦。
“君欲采拮,必先鞠耕。”事业和征程,从来少有康庄大道;蟾宫折桂,需要不懈努力。于是,我用勤劳与智慧、信念与执著编织和打造军营梦想。40多度的高温下,我与亲如兄弟的战友一起摸爬滚打;接近摄氏零度的荒野里,我与亲如兄弟的战友在一起,接受风雨的洗礼;风雨飘摇的洪魔肆虐中,我与可亲可敬的战友兄弟在一起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夜深人静的孤寂中,我在一盏30W的台灯下,攀登知识的高峰……
岁月不居,似水流年。从1990年冬天入伍,22年光阴在跌岩起伏中滑过我的眼前。记不清多少次在训练场你追我赶,记不清多少个夜晚在孤灯下奋笔疾书,记不清多少个日日夜夜风在办公室里追星赶月,记不清磨破了多少双解放鞋,记不清穿破了多少套绿军装。汗水与收获是成正比的。我的胸前挂过15枚闪闪的军功章,其中荣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12次,成为广州战区同龄军人中立功受奖最多的军人之一。恰如著名作家冰心所说:“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荣幸的是,我已经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党员领导干部,在平凡而又重要的岗位上为国防事业奉献着聪明与才智。
多梦的汉子,不懈的追求。梦给了我成功,梦也给我留下了遗憾。我要说的是,在祖父仙逝的时候,因为我是一名军人,恰巧任务在身,家人怕我经受不了打击,没敢告诉我这一不幸的消息。没有为至尊的祖父送别,成了我终生的愧疚。或许,祖父会感到欣慰,在为他送别的日子里,许多人自发地来为他送行,这些人中,有政府官员,有社会、村寨名流,有普通百姓。虽然他悉心栽培多年的孙子在数千里外的军营未能为他送别,但祖父当会含笑远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孙子正在军营里追求人生另一个梦,正用双倍的努力雕刻美丽辉煌的人生,为祖国、为军队、为家族描绘更为壮丽的风景!
梦是永远的诱惑。就众多的文学作品而言,我对诗歌情有独钟。对于诗,杜甫的胸怀“不薄今人爱古人”,郭沫若的见解是“好的旧诗万岁,好的新诗也万岁”,我更为欣赏诗人向明的观点:“喜欢旧诗爱新诗”。我曾经向著名作家高玉宝请教,问他什么样的诗才是最好的诗,高老说,这要看个人选择!但他强调“文学是写给人民看的”,“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是的,诗人应当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与现实,关注人类的命运,为时代的英雄而歌,为人类的命运而忧,为社会的进步而呐喊,为人类的成功而欢呼。著名诗评家吕进说过:“诗是歌唱生活的艺术。”我想,每一个具有良心的责任感的诗人,都应该对生活抱着正确的态度,在创作时注意社会效果。对于好诗标准,著名诗评家杨光治认为要达到“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这一境界。光治先生解释说,能写出“人人心中所有”,说明诗人是广大群众的代言人,“人人笔下所无”,表明诗人有艺术的独创性。
我酷爱诗歌。这是因为我为缪斯的艺术神功所折服。读诗,我要读质朴隽、情真一意切得诗,我不喜欢装腔作势、故作高深或言浮于情、华而不实的诗,更不喜欢那种读后“令人气闷”的“古怪又朦胧”、“读它百遍也不懂”的诗。当然反对隐晦,并不是赞成大白话或“机械的模拟生活”的诗。
至今,我还常常做着未了的“诗人梦”。
诗,是时代的音符;诗;是情感的喧哗;
诗,是奋进的号角;诗;是前进的动力!
生命不息,追梦不止。写出更好的“意象纷繁、内蕴深沉、质朴隽永的人生体验之作”将是我毕生的梦想。我力求让自己、让别人从我的诗中读出深刻,读出隽永,读出真实,读出生动,读出自然,读出激情,读出斗志,读出刚强,读出成功!我才疏学浅,缺乏恒心,深知自己成不了气候,但“天空中没有留下痕迹,而我已飞过”、“以笔为旗,旗帜的本质是飘扬着,不管飘扬得高不高,人们看没看见——旗帜的追求是激烈地抖着风,猎猎飘扬!”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因为我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因为我十年如一日在广州军区机关从事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几乎每一个春夏秋冬都被没完没了的“文字游戏”折腾得精疲力竭,对诗倾注的热情少了许多。与诗“暂别”多年,今又说诗、写诗,我不禁要问:缪斯,你可会恨我无情如斯?不过,我相信,人生四十正年轻,我将会执著地追逐人生的追逐,“少小敢立为文志,终生不改幼少心。”过去的仅仅是序幕,在永恒的诱惑面前,任何的遗憾必将被未来大写的成功所补偿。
只要有志常自奋,终有一日梦成真。(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