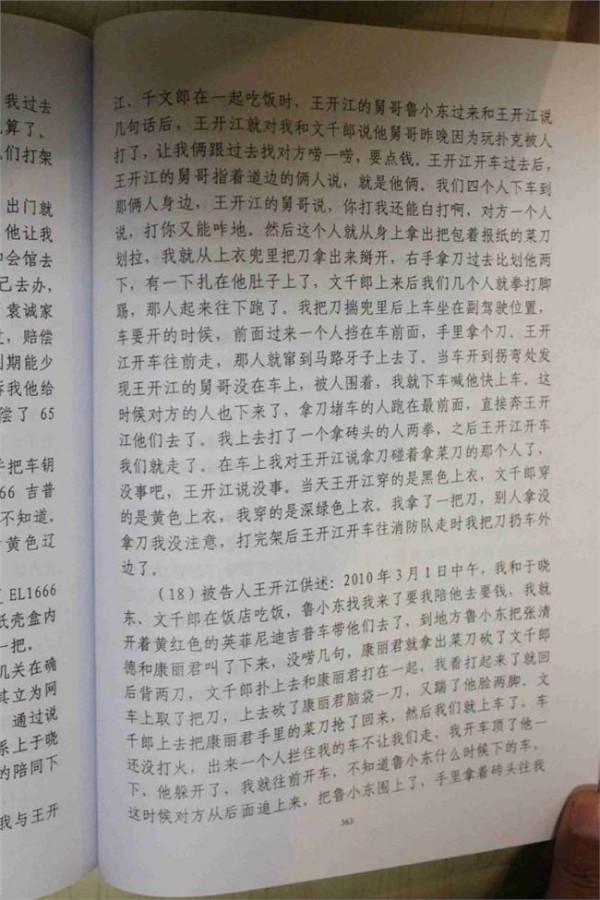《余罪》余罪 一个没有标签的人物形象更有感染力
归功于故事?可能是靠谱的思路。虽然原著书写者不满,但以追逐人的立场,引人入胜的剧情,合理铺陈的故事,以及鲜活的人物形象等,才是废寝忘食的原因。
也许各方面的原因都有,而令人满意的答案却不会有。
撇开源于剧作自身的因素,有一个现象无疑值得关注:一部以卧底警察为素材、正面形象塑造有悖常规思路的作品,何以引致大量网民(年轻人)的共鸣?
余罪:标签无法定义
余罪是《余罪》的主角,这个被称为“贱人余”的家伙有着非人的名字不说,在小说里,在“粗制简编”的剧里,看起来也没有“好东西”该有的样儿。实际上他也确实不像好人,反倒是满世界播散“坏人”事迹:
念大学挂科,还不是一次,临毕业还因为打架差点被开除。也许就是这些流溢出来的痞子习性,很不优秀的余同学被发现为优秀的卧底人才。
作为水果贩的后代,原初他只是为了卖水果的老爸不被欺负,想着片警余罪威风胡同的样子才决定去当警察的。这突然被绳索套住要去做卧底,焉能轻易就范?
面对无名无姓、黑白天都危险、分分钟会丧命的“机会”,余罪很清楚,如果牺牲,底层的老爸未来堪忧,于是他想方设法逃离。然而,在慧眼伯乐的“诬陷、胁迫、威逼”下,更重要的是这个内心充满矛盾冲突的小人物,除了痞子形态,灵魂深处内疚、感动、责任、正义交织,在目睹卧底之死的情境染色下,一激动?一冲动?就把死活的事儿忘了,上道了。
当卧底还真不是被逼的。可是身份的确认并没有改变余罪的“做派”。贪生怕死、不务正业的“贱人余”依旧放纵、享乐,一副本性难移的样子,在表面上“都是为了任务,不能让人怀疑”的荒唐中,演绎着“乐在其中”的性情——卧底角色使然的后面,无疑散发着醉生梦死的余味。正派?反派?真的很难定义。
第一季的最后,心里想着、嘴上念着保命要紧的余罪心生退意,想结束卧底旅程。置身林宇靖男友的葬礼,又被正义、责任意识把持,他决定再次踏上征程,将卧底的任务完成。
关于余罪,多次命悬一线却坚持道义担当,无疑是正面的,甚至是伟大的,是英雄。然而在组合起来的画面中,人们却很难给出标签化的定义,尽管现实生活中本来没有标签。
但是,在我们的符号系统中,在内心深处,标签的刻痕难以抹去。
范本:尚未去除面具
关于英雄人物,或者说正面形象,国人意识里的范本是容不得沙粒的。
不光是晚近以来高大全的宣传和书写,类型化的叙事古已有之。从传统文化留下的仓库中,很容易获得精雕细琢的样品:几乎每一个“模本”个体,不是与生俱来,就是教条化的道统文字堆砌,人们很难找到时间蚀刻、生活浸润下善恶交错的成长、成型之路。这当然无关性本善之说,人们倾向于简单地判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比如岳飞及其母亲的刺字。
当然,少年儿童的教育成长方式和未来有关,问题是,当人们希望各色各样光辉形象伟岸的时候,很可能忘记了作为一个吃喝拉撒活体人物的存在,过分地渲染、刻意地拔高,末了生活中的事迹碎片被无限放大,活生生的人物被演化为门神,像关羽、包黑子所属的队伍。这种正面的形象突出积久成习,渐渐地,碎片被一些人当作了整体,再也不去考虑美好图画中留白的意义,甚至拒绝留白。
在特定的年纪,又或者特定的文化、意识境遇里,模式化的英雄标签确实可以起到鼓舞人的短期作用。遗憾的是,一旦系统开放,一旦人们从圣人的阴影中走出来,曾经的标签就只会是标签,而不再是现实生活的参照。特别是在当下多元化的丛林里,人们不再迷恋单向(单一)的人性解读,粉饰的英雄沦为了童话故事,就如英雄联盟中那些画师笔下的超人。也许有人认为精神可学,不过这要面对一条鸿沟:我们讲述的是世俗社会街道上行走的人,而不是抽象出来的线条。公允地说,能触摸到的准则才有示范意义。
“英雄是鲜活的”,在这种流行说法的表层,人们看到的还是精心雕塑的“面具”。
启示:剧情外的话题
有血有肉、有普罗大众影迹的模型成就了《余罪》的感染力。
作者坦言:“我的粉丝里有无数警察,喜欢余罪,就是因为在他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不是高大全风貌。《余罪》叙述的是一个小警察的成长故事,他有满不在乎的外表,也有满腔的热血。事实上正是焦虑、矛盾,甚或还荒诞的人物性格为剧情的跌宕起伏拓展了空间,也为人物的多样性展示留下了时间。
从网友的角度看,大多数人表示人物设定真实,余罪形象受人喜爱。由此回看旧时代的武侠,往往是那些非正统的缺点(行为)构成了感染力的支点,是这些鲜活的个性,拉近了与世俗生活的距离。
正在念大学的艺潇是《余罪》粉,拍过小电影的他在组织自己的小团队讨论后结论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余罪以一介草根身份,虽困于规则但敢于挑战规则的非标准正面形象,以及口头上一切听指挥,实则自作聪明为所欲为的青春特色。
活在有阳光但也有阴云的世界里,面对世态百相,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在我们设定英雄的完美形象之时,尤其是将这种形象普遍化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杜绝绝大多数普通人趋向英雄之路,反过来,却是并不完美的余罪唤起了很多平凡人的英雄梦,故而其现象级的共鸣就不难解释了。
一个虚拟的角色因为生动的现实色彩,收获了各色年轻人的热捧,其中的缘由是明晰的,也许无需提醒神剧的制造者从中寻获启示——观众(如果有的话)仍然可以将之视为低劣的搞笑谈资,但回到现实里,回到高大上人物的书写,是不是应该把延续了不短时间的标签取下来呢?毕竟,这些人物的事迹的传播,不是为了使本身已经伟大的形象更伟大,而是出于弘扬、激励、示范的目的,要能让人学得来。在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社会环境中,尤其如此。
《余罪》现象呈现的意义不止于影视剧,它应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