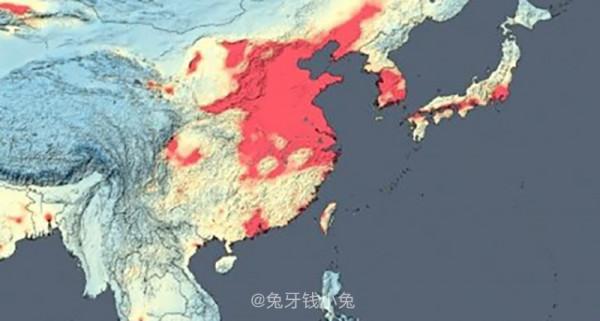瓶中人巫昂 巫昂《瓶中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无拘无束”是巫昂的长篇小说《瓶中人》最迷人的气质之一,它使得小说从头到尾洋溢着一种自在感和松弛感,率真、轻盈、任性,又带着几分暗藏悲伤的慵懒。
《瓶中人》真正虚构出了一方小小的避难之所,时间的概念在此被取消,灵魂的声响因亦真亦幻而变得更加响亮,那种孤寂又温暖的色调犹如两场暴雨之间天空中冰蓝色的隐约预感,这是我们在当下的文学阅读中久违了的深沉况味。
“每当有人问我你的小说处女作是个什么?我总是犹豫再三,回答:科幻爱情小说?”读到《瓶中人》后记里巫昂自己的这句话,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小说完成后,作者摊摊手、耸耸肩、撇撇嘴那一副既珍爱又无奈还要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在我看来,这是小说写作者一种难得的好状态:故事自身的纹理和呼吸节奏得到充分舒展、进而自然而然地生长出作品的肉身,作者没有夹带那么多宏大词汇,不操心这本小说在书店里的定位,评论家会怎样解读也暂且搁置到一边……用巫昂自己的话来说,“创作是件无拘无束的事”。“无拘无束”是这部小说最迷人的气质之一,它使得《瓶中人》从头到尾洋溢着一种自在感和松弛感,率真、轻盈、任性,又带着几分暗藏悲伤的慵懒。
“无拘无束”是想象力的保证,而想象力关乎人类进行小说虚构的遥远初心——这种能力本来是理所应当的,在今天的文学写作中,倒渐渐变成了珍稀物种。《瓶中人》里那种神思飞扬、举重若轻的想象力令人惊喜,只不过这种自由的想象的确给评论者们制造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例如,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把《瓶中人》装到哪一支“瓶子”里去。
第一眼看上去,这个故事似乎应归入科幻小说一类:一位事事不顺的女屌丝阴差阳错地掉进了一只瓶子,发现里面住着一位外星男人,原来这只瓶子是凝聚了外星人高度智慧的特殊生存空间,它类似于地球人的空间站,时间和空间在其中都能够自由缩放扭曲。
“深蓝星”在巫昂笔下有一个大致轮廓的“前史”,玻璃瓶的功能构造也堪称神奇有趣,但这个故事从根子上讲,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幻作品不同。
百万光年外的战争与毁灭似乎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由头,它仅仅负责解释瓶中外星男为何会出现在地球,至于它的细节乃至真假,小说没有也不必过多牵绊。
而作为充满象征意味的关键道具——那只瓶子,只是一小方隔绝于世的空间,像一本书,或一门私人创造的秘密宗教。无论乌托邦、恶托邦、虫洞穿越还是星际帝国,大多数科幻作品对幻想空间的构筑,背后都暗藏着对现世的总体性的观照,《瓶中人》却对这些不怎么感兴趣,人类命运、宇宙玄机、善恶对垒、政权组织形式、世界与人的存在合法性等并不是巫昂书写的重点。
与一般科幻小说往“大”里写不同,巫昂的功夫在于“小”:小说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往往在于那些细微的(而非宏阔的)、身体的(而非思想的)、本能的(而非技术的)、无关痛痒的(而非生死存亡的)部分,比如主人公那隐形的泪腺、水龙头关闭角度错误引发的困扰、被抛出瓶子时那一身脏兮兮有些不好意思的睡衣、那试图借助剧烈的麻辣来镇压心灵之痛的胃……这些细微的笔触常常打动我,让我在悲悯之余生出一丝莫名的亲近与认同。外星人以千计赠给女主人公的那面镜子,微缩着一条凌驾时空的能量通道;整部小说则是另一种镜子,它的光芒探向内部,日夜映照着女主人公那小小的心绪波澜。这一切无关乎宇宙运转、也不涉及人类命运,它只跟一个落魄女孩的日常和内心有关——她是如此平凡,平凡到我们不愿意在街上赐给她第二眼注视;但又有谁能说,宇宙的烦恼就一定比她的烦恼更令我们动心、也更同我们自己的生活相关联呢?
《瓶中人》又像是一部充满幻想色彩的爱情小说。事实上,爱情构成了小说的主线,我们甚至可以套用一个类型文学的公式来简单明了地勾勒出小说在大致上的情节走向:灰姑娘式的女主与具有超能力的男主相爱了,男主的超能力救了女主,女主放弃一切救回了因过度使用超能力而奄奄一息的男主,最后两人顺路私奔,离开了烦恼之地。但《瓶中人》显然不是一部类型化的小说,一个典型的表现是,真正意义上大起大伏的情节在小说行至一半时才出现——由于私情被发现,同居男友杨少康在盛怒中痛打女主,眼看女主面临严重受伤甚至被活活打死的危险,瓶中人终于启动了超能力,通过镜子把女主瞬间转移到了自己这边。这是瓶中人第一次真正以自己的存在介入现实世界,它像一针催化剂,迅速加快了小说的前进速度。而在此之前,瓶中人始终是一个秘密的存在,如同悬崖高处一座不问世事的寺庙,只负责为女主疲惫的心灵提供偶尔的安抚。
整本书的前半段围绕女主的日常生活展开:平庸乏味的过往、莫名其妙的同居、有心无力的吐槽、并无刺激可言的艳遇、糟心又看不到盼望的工作。巫昂把这些无趣味、不好写的东西写得轻快好看,这是好作家的本事。进一步讲,一般意义上的爱情故事,也并非是巫昂的重点。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不少,却都谈不上精彩。爱情于她,更像是一道鼓点催行的程式,而不是心神战栗的仪式;借爱情之名展开的,也更像是一场自己寻找自己、自己安置自己的漫长旅途。那么以千计呢?女主人公同以千计的爱情似乎也隐隐少了一些什么,不仅是撕心裂肺生离死别的虐恋成分,更是那种自私偏执、狭隘敏感却总是能被原谅的疯狂本能。“那你喜欢他,还是爱?”闺蜜问她。她的回答是,“我觉得是爱。”
令她记挂的是爱本身,而不是哪个具体的人,即便那个人本身其实已相当非凡。因此在我看来,这部小说不是爱情小说,而是关于爱的小说——对所谓“世界之外的世界”的想象和感知,说到底,也还是跟广义的爱有关。爱情关乎两个人,爱则是一个人与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事。
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只有女主没有男主,因为那个稳坐瓶中的外星人,从一开始就可以被看作是女主人公的另一个自我。因此我们可以将《瓶中人》看作一部兼糅弗洛伊德色彩、爱伦·坡情调甚至哥特气息的心理悬疑小说,巫昂一度再明显不过地在故事的层面上直接暗示了这层充满分裂感和病患气息的小说真相,这就是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确凿地使用过女主人公姓名的原因:我们曾经以为她叫莫莉,后来慢慢发觉,那位从性格命运到罩杯型号都颇为不同的闺蜜余怀春,跟莫莉好像是同一个人。
至于那只小小的瓶子,也有过那么一瞬,我们意识到它可能真的只是女主人公的“怀春一梦”。“没见过,你记错了肯定……你不信我说的,找别人问去,我还要回家做饭去。
”积水潭桥下的大妈这样回答,手里提着永世不朽的购物塑料袋。眼前是自己跟以千计相会的地方,此刻忽然已变得景物全非,那只玻璃瓶自然不知所踪;我们似乎有理由这样理解,女主挨了同居男友一顿暴揍,终于从分裂的幻梦中清醒过来,至于后面重逢私奔的段落,只不过是一场既温暖又悲凉的回笼觉而已。
但是这些重要吗?无论女主是叫莫莉还是余怀春,无论瓶中人是默默旁观人类的外星生物还是平凡女孩内心投射的幻影,它们都不是这部小说的精髓所在。小说本来不就是一场从真实手底逃逸出来的幻梦吗?在一场梦中再做一场,又有何妨。
重要的是,《瓶中人》真正虚构出了一方小小的避难之所,时间的概念在此被取消,灵魂的声响因亦真亦幻而变得更加响亮,那种孤寂又温暖的色调犹如两场暴雨之间天空中冰蓝色的隐约预感,这是我们在当下的文学阅读中久违了的深沉况味。至于它究竟是精神分裂的产物还是来自更大意味上的混元合一,反而成了次要问题。
这便是巫昂和她的《瓶中人》。我至今不确定该如何称呼小说的女主,就像我至今无法笃定地将这本书归类到任何一种已知的小说类型之中,也不会用那些老生常谈式的庸俗价值来框定它。它貌似科幻,却紧贴肌肤;讲述“爱情”,却归隐回“爱”;真假恍惚,同时又能超脱于真假。它无拘无束的天真中透着熟练的洞察,在轻松睿智的文字间讲述着深沉,用新奇的想象力撞击着我们,唤醒的却是内心深处那些古老的常识和本能。我很难说它究竟“是什么”,这由它无拘无束的气质和内在的文本丰富性所决定;但通过以上那些“不是什么”,我想,我已经说出了《瓶中人》带给我最强烈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