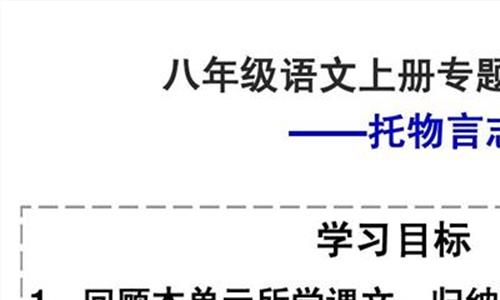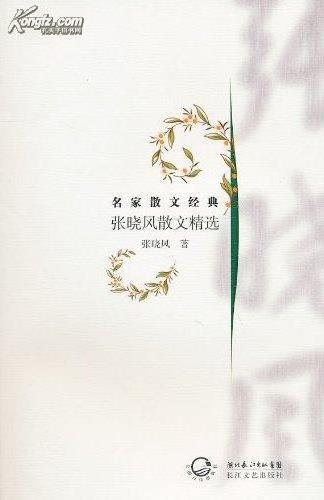张承志名句 名家散文赏析:重逢关川 张承志
大约是四月的下旬,我独自一人离开兰州,搭上了从小西湖走关川的班车。
那是在激动的八九年。这趟长途车上,满满挤着晃着的,都是农民。那是最胆大或最绝望的农民,咬咬牙走出家门、刚刚尝试走出去的八十年代末。后来我才明白,与我同挤一车的,都是西海固最初的打工者。我刚从他们的腹地出来,与一场凶恶的械斗交臂而过。
车里响着粗浊的陇东口音,不时有人一声胡大一声主地长吁短叹。我捉摸着农民,他们永远叫人费神难猜。我觉察自己触碰着了他们的一个规律:利益多了就闹些是非,逢灾遇难就远走他乡。他们不识地理,只认方向,循着五八年的老路向西,先青海,再向西,走新疆。
被陇海京包几条干线甩开的甘沟道,是一条弃儿般的老路。
在那条我惯走的路上,天荒地旷,沥青剥落,车影稀疏,不见树阴。只有眼巴巴的农民等在路旁,等着兰州放下来一天两趟轿子车。上了车再坐上座儿不容易,我有时就坐在车门的铁台阶上;而农民傻,常一路站到甘沟驿或马莲湾。
窗外的革命如火如荼,贫瘠的窝里却在斗殴。想着天下的兴亡,听着愚昧的械斗,我欲哭无泪,心里一团乱麻。我几乎是逃跑般到了兰州,打算从那个码头穿越黄土迷蒙的陇东。
憧憬的关川,以前只来过两次。
在马家堡的桥头下了车。我寻着依稀印象,朝土崖上走。鞋子也咀嚼般踏着,走上斜斜的漫坡。那一年,红脸银须的老者已经卸任,换了我还没谋面的一个新人。从远近空旷无人的苦旱风景,从苦水河那望着难受的辽阔河滩,升起扶摇蛰气。我踏着没踝的软土,登着土坡,走向迎面的关川窑洞。
那个缓漫的上坡,冷冷寂寂。没有为我出现谁。我敲门进窑,一个沉默的老者,对我欠起身来。
他脸颊瘦削,不苟言笑,颜色铁黑。是西海固山里那种硬脖子不易通融的类型。问答间知道,我在《金牧场》里怀念过的银须老者已经退位,他是接替了银胡子的新任,姓高。时刻已进了迪格勒,我忙着洗;往下一连串的功课,晚间睡前能谈些什么,那时我顾不上想。
沙姆、胡夫坦、塔巴莱,穆罕麦斯―――住进拱北,流水的功课终于都结束了。我站在土崖顶上,四顾漆黑。大川平滩都不见了,混沌天穹把它的浓黑重蓝,直接罩在我的脸上。它浩莽且孤独,低垂着四合。
进了窑,一盏茶沏上。我喝了一口,茶水甜甜的。该是炕头上细声漫话的时候,但高阿訇不善话语,不接人的话头,我也就早早躺下了。
在漆黑的关川窑洞里,我散漫想着些心事,闭上眼准备入睡。
―――“那个事,你也听说了么?”黑影里,老汉突然问。声音硬硬的。他问的是家乡的械斗。一句话,挑起了我心头的怒气和烦乱!